来源于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官方账号 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
《古诗十九首》的笔墨是非常大略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随意马虎引人产生遐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什么叫“天衣无缝”?便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
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因此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个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殊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高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王安石的“东风又绿江南岸”,便是个中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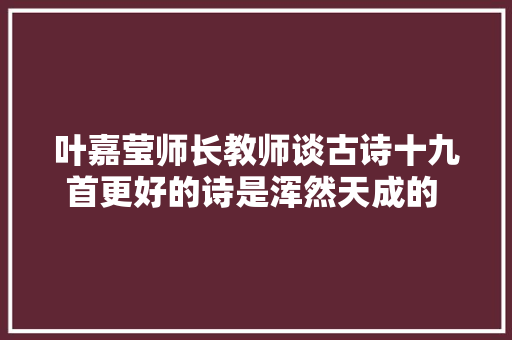
其余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墨客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字,自己又拿不定主张,坐在马背上想得着迷,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军队,被众人拿下送到韩愈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墨客,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推敲了半天,末了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由于墨客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拍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高下功夫,费尽了“考虑”。
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主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实在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个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秦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落》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
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落,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险些去世在道路上,而在这段韶光里,羌村落一带也被叛军盘踞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落落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墨客得到机会回羌村落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那种战前常见的安然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觉得!
如果你不读他全体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墨客,都不是用笔墨写诗,而是用自己全体的生命去写诗的。
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评论辩论比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冲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全体生平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剖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墨客?就由于没有这个结合。墨客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十全十美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节制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剖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遐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冲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贯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真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楚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若何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遐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
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平生来做印证,多数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弗成,我们只能觉得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缘故原由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气,总是要费尽心机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对有些诗来说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如杜甫诗便是如此,他有不少诗反响了唐代某些历史事宜,写诗的时候确有所指。对这一类诗当然该当尽可能确定作者的原意。但十九首之以是妙就妙在不知作者——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若何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遐想。
正由于《古诗十九首》有这样的特色,以是它特殊适宜于当代西方“接管美学”的理论。西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曾盛行一种叫作“新批评”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见文学批评该当以作品为主。他们认为,作品里的形象、声音、韵律,都关系到作品的好坏,惟独作者却是不主要的。而后来盛行的“接管美学”的理论,则是一种更新的文学理论,它进一步把重点转移到读者身上来了。接管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故意义,也没有代价;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工具,才有了意义和代价。
然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经历和阅读背景,因此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好?便是由于它能够使千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读者读过之后都有所冲动,有所创造,有所共鸣。
但《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涉及它所写感情的主题了。《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去的感情、失落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我以为,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由于,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生平中都会有生离或去世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因物质或精神上的不知足而感到失落意;每一个人都对人生的无常怀有恐怖和忧虑之心。而《古诗十九首》就正是环绕着这三种基本的感情转圈子,有的时候单写一种,有的时候把两种结合起来写,而且它写这些感情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含意幽微,委婉多姿。
例如,《今日良宴会》里有这样两句:“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你为什么不鞭策你的快马,抢先去盘踞那个主要的路口?实在,所谓“要路津”所代表的乃是一个主要的官职,说得普通些,这是对争名夺利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还有一首《青青河边草》,它写了一个孤独而又不甘寂寞的女子,最末两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这几句“可谓淫鄙之尤”,然而它们之以是不被人们视为“淫词”或“鄙词”,那便是由于其感情的朴拙了。
实在,我说这两首诗真正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感情的朴拙,它们真正的好处在于提出了人生中一个严明的问题:当你处于某种人生的困惑中时,你该怎么办?每个人都难免会有懦弱的时候或绝望的时候,每个人在这种时候内心都会产生很多困惑和挣扎。而《古诗十九首》就提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直接写出来的,而是用很委婉的姿态、很幽微的笔法来引起你的冲动和遐想。晚清有一位诗学批评家叫陈祚明,在他的《采菽堂古诗选》里有一段话对《古诗十九首》评论得非常好。现在我把这段话抄下来: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敷,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生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生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大家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脾气之物,而同有之情,大家各具,则大家本自有诗也。但大家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蕴藉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切切不然之想。今若断交,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之矣,必曰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断交之念,以是有思,以是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古诗十九首》说出了我们人类感情的一些“基型”和“共相”。比如,每个人都希望知足自己的统统空想和欲望,但真正能够知足的又有几个人?就算他在物质生活上知足了,在精神生活上也都能知足吗?有的人已经得到高官厚禄,但仍旧有不知足的地方,何况那些贫贱之人呢?如果你拥有充足的韶光去追求,大概终极会有知足的那一天,然而人的生命又有多么短暂,韶光并不等待任何人,你的生平很快就会过去!
又比如,谁不愿意和自己所爱的人永久相守在一起?但天下又有谁没经历过生离或去世别?当你们相聚的时候,并不能体会到离去的悲哀,因而也就不睬解这聚会的难得和名贵,可是当你失落去的时候,你懂得了它的宝贵,却又不得不承受失落去它的悲哀!
人都是有感情的。以是自然界的四季变革、人间间的死活离去,所有这些物象和事象就会摇荡人的心灵和脾气,从而产生诗的感发。可是,既然每个人都能产生诗的感发,为什么还有墨客和一样平常人的差异呢?那是由于,一样平常人只是“能感之”,只有墨客不但“能感之”而且“能写之”。也便是说,写诗不仅须要有感想熏染的能力,还须要有表达的能力。
我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常常为我的一些学生而感慨:他们有很敏锐的感想熏染能力和很深厚的感情,但却因写作的能力差而不能够把自己感想熏染到的东西写出来。特殊是我们中国血统的同学,他们在台湾或喷鼻香港念了小学,中文的根本还没有打好就来到了加拿大,但他们英文的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由于他们毕竟是从小念的中文。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美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天分,他见告我,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出来呢?他说:“老师,我写不出来。我的中文不成,英文也不成!
”
这真是人生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每个人生活在这个天下上,都该当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可是有的人却把它失落落了!
陆机在《文赋》的序里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谓“意不称物”便是说,你内心的感情与要写的工具并不相合。还有一个可忧虑的问题是“文不逮意”——你用来表达的言辞赶不上你的意思和感情,你无法把你内心产生的那种美好的情意完备表达出来。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但什么是“完备表达出来”?你说你现在内心之中有十二万分的悲哀或一百二十万分的悲哀,这就叫完备表达出来了吗?弗成。由于你虽然把话说到极点,可是人家看了并不冲动。就以爱情而言吧,每一个人爱情的品质和用情的态度都是不同的。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后来那女子不跟他好了,他一怒之下杀了这个女子和她的百口。这或许便是当代人的感情。
而中国古人用情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所追求的标准乃是“温顺敦厚”。《古诗十九首》的感情便是如此,它是温厚缠绵而且蕴藉不尽的。我们常说,某人的感情是“百转柔肠”,这种人他不能够把感情一下子割断。由于有的时候,他的理性明明知道这件事不会成功,该当放弃了,他的感情却没有办法放弃。一个人被他所爱的人抛弃了,如果干脆从此断绝关系,那么就不会再有相思怀念了,但他偏偏不肯,心里总是在猜想:对方一定不会如此绝情吧?我们终极还是要相见的吧?因此才会产生相思怀念,才不由自主地要用诗歌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古诗十九首》用情的态度是如此温厚缠绵,以是它表现的姿态也十分委婉弯曲。它的措辞表面上蕴藉不尽,实际上却把人的内心之中这些繁芜的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
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实在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不雅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在美国西部转印的喷鼻香港《大公报》上曾刊载一篇文章,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阐明为文学文体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构造。“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
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文体的构造和对文辞的利用,我们就会创造,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便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创造: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光鲜的印象和冲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以为,《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平凡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以为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想熏染;等你年纪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想熏染。
《古诗十九首集释》
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二心坎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便是婉转附物。在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我们看详细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先容。
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落、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墨客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由于,凡是真正的墨客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付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习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每每能很好地表现出墨客的这种感情。“切”是相符,便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便是由于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如果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足,那当然是失落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浮夸了,超出了实际情形,那也不是好诗。把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属于“赋”的方法。以是,《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中国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意见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大略,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繁芜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便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冲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冲动。
其余,前文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个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触目惊心,可谓险些一字千金”。“温”,温顺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撼,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末了,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样平常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每每只选个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想熏染,只读几首是不足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由于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同等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理解旧诗措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由于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遐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便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全体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本文节选自《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标题为编者所拟)
《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迦陵说诗)
叶嘉莹 著
简体横排
本书是诗词大家叶嘉莹师长西席对汉魏六朝期间代表性墨客及其作品的鉴赏、评点。叶师长西席从详细的个体墨客入手,通过对其代表作品的讲解评析,阐述了历史时期、社会现状和墨客个体的身份地位、品性才情对其作品的深刻影响,展示了全体汉魏六朝期间文学的整体风貌以及这一期间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其承前启后的过渡浸染。
《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隋树森 集释
32开 平装
繁体竖排
9787101126006
20.00元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主要的作品之一,历代传诵,被誉为“五言之冠冕”;致力于十九首的研究者代不乏人,撰述层出;而总其大成之作,当推隋树森师长西席之《古诗十九首集释》。是书分考释、笺注、汇解、评论四卷,全方位地揭示了古诗十九首的文献与文学代价,为之后的研究者供应了可靠的文本依据。
《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
叶嘉莹 著
32开 平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27089
36.00元
她是学生眼中要眇宜修的湘水女神,也是无数人通向古典诗词海洋的摆渡人,她使古老的诗词得到再生。她是才情纵横四海的大家,在颠沛流离中写下摄民气魄的诗篇。她是深具弱德之美的大家闺秀,坚忍支撑一个家庭。94岁的叶嘉莹师长西席用诗词来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北平的生离去世别、台湾的白色胆怯、外洋的丧女之痛……在多舛的命运中,以诗词创作、研究蜚声国际;在国难家愁面前,独占一份“士”的情怀与担当。在与诗为伴的沧桑岁月中,历练成俏丽的星光。叶嘉莹的笔墨诚挚、深隐、文雅!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