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秦访古,游历吟咏留名篇
兴安在湘漓之源,山水清幽,灵渠、乳洞、严关、秦城遗址、湘桂古道等古迹历历如画,吸引着文人士子们前去寻秦吊古。不管是初来广西上任进入兴安,或是在任期间专程来游,亦或是奉使公干途经兴安的仕宦文人,都会为兴安的美景古迹所倾倒。游历者每每情不自禁吟诗咏赋,留下一首首随处颂扬的名篇。
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朝奉郎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方信孺游乳洞岩,将其间美景喻为玄门十大洞天之罗浮山,《乳洞》诗句 “分得灵河一派流,铁桥仍复借罗浮。”范成大在《兴安乳洞》的诗中“山水敦夙好,烟霞痼奇怀。”写出了他对兴安山水云霞的赞颂,不再是他刚来时觉得中的“瘴乡”。王正功《乳洞》诗则描述了洞外的村落落是一幅悠然自适的世外桃园:“湘南悬想碧云横,桂岭遥瞻烟霭暮。招提钟磬出幽深,村落疃牛羊自来去。”
兴安县最著名的古迹,当属灵渠,而灵渠两岸的美景,自是明洪武年间工部尚书严震直感触最深。当时严震直奉命至兴安修缮灵渠,竣工拜别时作《筑兴安堤》,“匆匆装归去去朝天”, 自是喜不自胜,行于灵渠岸,“桃花满路落红雨,杨柳夹堤生翠烟。”将六百多年前的灵渠美景如一幅幽美画卷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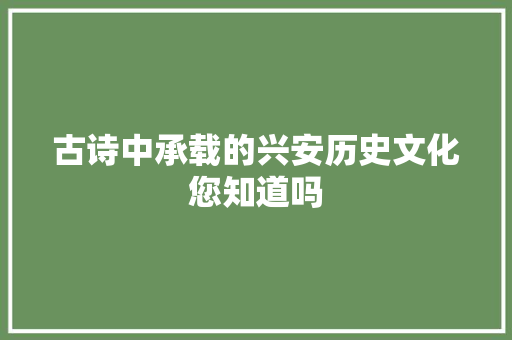
山净水秀的兴安古城,引来多少文人雅士游历并为之倾倒,乾隆年间,著名墨客袁枚自桂林漓江坐船到兴安,见两岸奇峰倒影如成长于水中,船行江上如行走于山顶,有感于兴安绝美山水,写下了与元代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佳作《兴安》:“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瞥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与袁枚相交甚好的李松圃,途经兴安时在灵渠边停车小憩,见野外里荞麦着花若满地白云,芦荻飞花,农舍炊烟袅袅,有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作诗《晓行》二首:“朦胧曙色噪归鸦,风撼疏林一径斜。满地白云吹不起,野田荞麦乱着花。”“芦荻飞花白满汀,停车小憩水边亭。前林一线炊烟起,画断遥山半角青。”
乾隆八年至十三年间任兴怎知县的杨仲兴,在兴安五历重阳,分别“驱马游三洞”、“奉使出永福”、“登高点灯山”、“北祭海阳庙”、“西向雷神殿”,游历了兴安的各处名胜古迹,“樵歌雁落与离骚,风吟泉滴声相偶。”写下了情景交融的《重阳纪游诗》。
庆远府同知查礼于乾隆十九年协修灵渠,并稽核湘漓之源,沉醉于灵渠美景,更是将分水塘边的景致刻画得出神入化,他的《分水亭晚眺》诗中,“粼粼亭下”“苍茫夕曛”等描述,动与静意境完美的交融在一起,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卷展现在面前,末句“看山看水看飞云”让人从诗句中能读到自然美景目不暇接。
广西玉林举人苏宗经道光年间经由兴安,见灵渠内舟从桥底过,水街边篷窗买酒便,一派热闹景象,已远非明末徐霞客经由时那般“城墙环堵,县治寂若空门”,一首《出陡河过兴安县》,将清代兴安水街的繁华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径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易,篷窗买酒便。水程今转顺,翘首望前川。”灵渠上的桥多,水路便是穿过一座座古石桥。沿水街两岸是集市商铺,打开舟中的篷窗,伸手出去便可向酒家买酒。
还有清代王国梁在《秦堤不雅观澜》 写道“三十六矶一望遥,江干风雨正潇潇”,赞飞来石“此石飞从何处来,参天拔阵势崔嵬”。陆纶《陡河口号》“陡门湾湾三十六,二水湘漓一派分”生动描述了灵渠三十六陡及湘漓分派的情景。
清末,兴安县末了的古诗名作,当属废除科举考试前兴安末了一位举人彭榕。彭榕走遍了兴安所有的名胜古迹,用他独特的目光,感想熏染、诠释了家乡的山、水、草、木,引发了用画笔把这些壮丽景致表现出来的创作激情亲切。于是,他创作了气势磅礴、技艺博识、清逸俊秀、飞彩流韵的《兴安八景图说》这一组八幅国画,并在每幅画上题相应的诗一首,成为了兴安古诗终极的名篇。
其一 铧嘴不雅观澜
澎湃汹汹激上矶,横流倒泻震阵容。惊异蛰起龙分水,舞爪掀鳞势欲飞。
其二 秦堤拜石
障地如砥拳多大,国计民生歌永赖。 不但棱皱品质奇,襄阳一见爱慕拜。
其三 渡头唱晚
渡头风景晚来佳,夕影炊烟画不差。犹有鱼排三五起,一歌一答唱还家。
其四 越岭歌风
越城岭上草婆娑,碧血殷殷迹未磨。北望边尘旋地起,登临合唱大风歌。
其五 北廓耕云
时雨时晴布谷鸣,春来廓外带云耕。省耕亭上凭栏望,一幅幽风谁画成。
其六 金峰待月
纵横眼界如披画,开拓心胸胜读书。有酒不妨人去后,无诗且待月来初。
其七 乳洞餐霞
巉岩三洞乳晶莹,模糊霞光映上清。到此飘然尘浊净,无须云母一身轻。
其八 严关玩雪
一夜雪飞不过关,满山都是玉为颜。重楼十二城一座,白玉京原在此间。
文人士子们游历兴安,哦诗题名,留下不少千古名篇,而终极饱含深情以诗入画并因画题诗的兴安人彭榕,作《兴安八景图说》以空前的高度总结了兴安的各处名胜古迹,成为兴安历史上古诗文化的千古绝唱。
二、 途经感怀,古今共是一长叹
唐宋以来,大量官吏文士或任职或游历来桂,多自水路进入广西。由于广西地处穷山恶水,阔别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央,那些离家的游子抵桂之后,难免各有感叹。开元十八年夏天,张九龄来桂州上任途中作有《自湘水南行》“落日催行舫,逶迟洲渚间”。元和年间,参与永贞改造失落败后被贬的柳宗元从永州履新柳州刺史,亦是溯湘江过灵渠去柳州,在兴安时留下了名篇《全义县复北门记》。宋之问、李商隐、元晦、范成大、张孝祥、刘克庄、秦不雅观等绅士,入广西上任者,或在任者途经兴安,各自都会有一番感慨,身处岭外,空有报国之志,无法很好地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华。卸任之时,大抵还是因得已重返中原而感到喜不自胜。广西刑狱摄帅事李师中在离开广西的前夕作《菩萨蛮·子规啼破城楼月》一首,个中有 “佳人相对泣,泪下罗衣湿。从此信音稀,岭南无雁飞。”将要离任了,佳人也无法挽留,相对而泣,热泪纵横,湿透罗衣。从此音信也会稀少,由于岭南没有传书的鸿雁。可见其拜别的希望是任何情绪也无法阻挡的。而调任北返,意谓着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报国的抱负更随意马虎实现。李师中离开广西过严关时,感慨四年岭外生涯现终得已北返中原,作《过严关有感》,深深感触途经严关宛如彷佛玉门关 “大抵孤忠报国难,古今共是一长叹。玉关还路春无绿,定远归来鬓已斑。四年岭外得生还,自顾无功但愧颜。欲识君恩至深处,严关便是玉门关。”
每当来任广西的仕宦进入严关时,由于想到岭外的瘴疠,荒蛮,总会有一种踏入鬼门关的觉得。清代墨客蒋肇《严关》诗句 “旧传此地鬼门关,逐客由来去不还”,故而可从宋代邕州知州陶弼《题兴安县石灰铺壁》“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中可体会到得以活着走出严关返回中原大喜过望的心情,想到自己的仕途,已两知邕州,今又终得北返,坎坷弯曲,看湘水宛然,借景抒怀“江势一两曲,梅梢三四花”。
相对付严关,古秦城也是仕子们途经吟咏抒怀之处。南宋隆兴年间知静江府张孝祥道经兴安古秦城,作《古秦城》感怀帝王“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岂不知在兴安居住的平民百姓“桂海冰天尘不动,岂知陇上两耕夫。”如处于桃花源中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悠然自适的生活,
南宋绍圣间广西提点刑狱曹辅过秦城,作诗《古秦城》抒发了另一番感慨,当年秦国发兵征南越,岭外已是海穷山尽之地了,仍要南征使之统一,一场又一场的恶战,只不过是“髀肉消残只自惊”而已,回顾都城八千里,这里又哪有什么秦城。
官宦儒士们道经兴安时总会有万分的感慨,吟诗寄怀,而个中还有曾权倾皇室有时道经岭南的明代宰相严嵩,经由万里桥,风雪日暮,远峰层阴,破屋老松,回忆自己已是行将就木,人生与仕途都已走到尽头,悲从心起,写下了《兴安县》两首:
其一
兴安城郭枕高丘,湘漓水分南北流。
万里桥头风雪暮,不知何地望神州。
其二
破屋古松喧夕籁,远峰寒雾起层阴。
梅花两岸湘漓水,岁晚相随到桂林。
一番感慨,一声长叹,历代文人儒士们的情怀,寄寓严关,寄寓秦城,从一首首古诗中流露出,让我们本日读来,仍能深切体会到他们当时或喜或悲的繁芜心境。
三、 古道西风,饯别相送在兴安
兴安地处粤西之首,湖湘之尾,是历代文人仕子自中原来上任或贬谪流放来广西的必经之地,也是任满回中原离开广西的必经之途。解缙《素位轩记》说“兴安当道于交广,湘漓众水之所发源,山林沮洳。”又在《赠周兴安朝京师序》写道“兴安在广右水陆之冲,湘漓渠水之所发源,送往迎来者日相续也”。湘水逶迤,古道悠悠,同寅或石友间饯行送别,多在兴安同游乳洞岩吟诗题刻,或严关口纵马北返,或从灵渠发舟,从此一别,如湘江北去,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载 “兴安石乳洞最胜。余罢郡时过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与栖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罢郡之时,也便是他离开广西北返之时,从桂林出发,同寅二十一人为他送行饯别,“华裾绣高原,故人纷后陪。”过兴安,经灵渠,与同寅们沿湘桂古道一起前行,至乳洞岩同游,心情十分愉悦而又有几分不舍,“向闻乳洞胜,出岭更徘徊。”想着即将阔别广西这蛮夷之地,而又因出任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
经略安抚使四年之久,对此地以及众同寅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但朝廷调任,不由自主,只能用文人们最儒雅的办法“题名”来话别,“祝元将、王仲显、游子明、魏景道、马奉先、李静翁、杨懋之、周直夫、郑梦授、陈仲思、魏舜徒、陈席珍、刘庆长、施进之、赵伯山、诸葛叔时、谭明卿、范至能,右十八人同游。至能之侄若、男萃侍行,岁月及道号在上洞。”并作五言古诗《兴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岩妙绝南州率同寅饯别者二十一人游之》,“南游冠平生,已去首犹回。”再次感想熏染到了四年前来桂林时在余杭与亲友作别那种“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去世别”的觉得。与同寅们乳洞话别后,范成大沿古道路经严关“裹饭长歌关外去,车如飞电马如流。”车轮马蹄留下的,是霎那间滚滚风尘,而其诗文中留下的,却是千年的文化余韵。
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正月初八日,广南西路提点刑狱王正功携家还里东归,幕僚送行至兴安,同游乳洞,王正功想到自己二十余岁便步入官场,为官几十年,也颇有政绩,始终未能青云直上,感慨“绝知官里少夷途,始信闲中无窘步”,“共醉生前有限杯,浇我胸中今与古。”相对而言,王正功更多的是对仕途的感慨,对人生的无奈,“早知富贵如浮云,三叹归田不能赋。”
宋淳祐甲辰(1244年)三月,静江知府谢逵奉诏经由,同客张景东、冯云从,男公阐、公阊,同游乳洞岩,夸奖兴安“灵钟秀异,美哉景致”,留诗《淳佑甲辰三月中浣奉诏经略同客张景东冯云从》于乳洞:“寻幽景象得晴酣,小小篮舆胜绣鞍。洞以乳名云液涌,泉迂石出水晶寒。山容染翠开油幕,竹韵鸣竽立玉竿。孰谓地灵钟秀异,美哉景致见兴安。”
乳洞岩自古为离去广西北归中原的士大夫们饯别探幽同游的最佳场所,每每在此留诗题名吟咏。隆兴年间静江知府张孝祥离开桂林时,“(蒋允济)与邦人送余于兴安,置酒于鲜乳洞之下。”“石间题名赋诗,火尽乃出。”
送别于兴安,除乳洞吟诗题刻,还有湘桂古道上的严关、石灰铺。
宋代官员邹浩,累迁兵部侍郎,两谪岭表。其在广西时与兴安当地绅士唐叟有旧,关系非常好,在兴安为唐叟写了《止止堂记》与《华严阁碑》,而唐叟的朋友也大都是当时绅士——苏东坡、黄庭坚等,可见其才华教化之高雅。邹浩出严关,想起十九年前从此经由,今日终于得已重返,听泉水声响潺潺仍似往昔,岁月悠悠,古迹依旧,作诗《滑石泉》感念“惟有流泉声似旧,凭防重听响潺潺。”邹浩北归时,念念不忘好友唐叟,文人重情,离去时,千般不舍,在石灰铺匆匆膝对饮,依依惜别,作《留别兴安唐叟元老推官》“天绘亭边三载梦,石灰铺里一时情。个中不是同参得,胸次峥嵘何日平。”而元代任广州路学教授的傅若金,一首《和智礼部早发兴安》,则是与好友相别于灵渠,并描写过灵渠时的悠然自适“解缆眠看竹,哦诗坐煮茶。”元代灵渠岸边别有致趣的一番景象,雨来、云去、解缆看竹,哦诗煮茶,发兴安、过灵渠,“归程足幽意,莫向市朝哗。”描述出一幅清幽的即景画卷。
对付那些从中原来广西,而任满后又将离开广西的文人仕宦们而言,从心中原认为的“蛮夷之地”,到入广西时所见张安国题诗“烦君净洗南来眼,从此山川胜北州。”进一步理解该地的山水胜景,徜徉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置身于“胜绝南州”的“湘南第一洞”乳洞岩,道经悠悠的湘桂古道,行舟于千年历史的灵渠,潜意识里从“蛮夷瘴疠之乡”转变为“地灵人杰之地”。而一旦拜别,自是感慨万千,更多的是对同寅朋友的不舍,如范成大与众同寅、张孝祥与蒋允济、邹浩与唐叟间的深厚交情,一旦阔别,南北两茫茫,不知异日能否再相逢,难免千般不舍,依依惜别,吟诗题名,在兴安留下一段段饯别同游的千古佳话。
兴安县自古以来是湘桂走廊,为楚越文化交汇之区,历代以来文人仕宦们或上任途经此地,或是游历古迹美景沿途吟咏,或离任时同寅朋友送别,留下了一篇篇传世诗作,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文化,让我们现在读来仍能感想熏染到千百年前兴安的“灵钟秀异,美哉景致”, 体会到文仕们当时离去“出岭更徘徊”的心境。而今,灵渠与古道都已失落去原有的交通运输代价,而千百年前的历代古诗文仍能让我们得见灵渠深厚历史文化秘闻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