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诗文作成往后,读者如何理解,又是其余一回事 。是不是有其他含义,实在并不是作者说了算。
下面,老街列举几个有名的关于杏花的诗句,比较一下。看看各种杏花有什么不同,咱们再判断”一枝不安于室来“有没有其他意思?
也可以从创作的角度来思虑,自己作诗的时候,该当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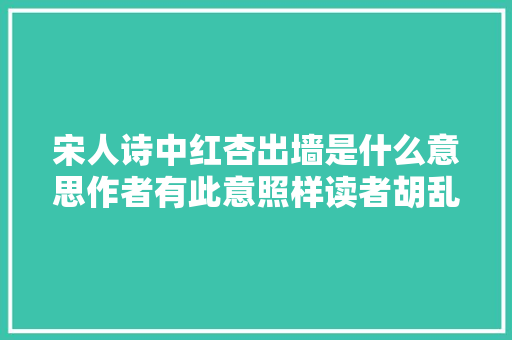
在浩瀚的杏花诗中,南宋墨客陈与义的这两句我最欣赏,每次读到的时候,仿佛空气都清新了许多,患有鼻炎的我彷佛呼吸都通畅了: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雨声中。
这两句来自于《怀天经智老因访之》:
今年仲春冻初融,睡起苕溪绿向东。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雨声中。西庵禅伯还多病,北栅儒先只固穷。忽忆轻舟寻二子,纶巾鹤氅试东风。
陈与义是我很喜好的一位墨客,不过这首七律,我只喜好这两句,不知道读者是否有同感。
陆游的这两句诗也很有名: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附全诗《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陆游还有一首直接写“不安于室”的七绝:
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不安于室头。《立时作》
仔细品味一下这三首诗中的杏花,便是春天的杏花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二、拟人的杏花 张先犹解嫁东风
上面说陆游和陈与义的诗中,杏花便是杏花,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北宋张先的词就不同了: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张先笔下的杏花,用拟人手腕,有了人类的个性。这三句出自张先《一丛花令·》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沼泽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薄暮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和陆游、陈与义的诗不同,张先的这首词很明显,把杏花授予了人类的性情特点,不是纯挚把杏花当作一个植物来写了。
三、以血书写杏花
说到杏花词,不能不提赵佶的《宴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喷鼻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悲惨,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斟酌,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个作者赵佶大家都很熟习,即著名的宋徽宗。上阕以杏花托物兴感,又把杏花比作一位“新样靓妆,艳溢喷鼻香融”的美女,却在无情风雨中凋零愁苦。
这首词的题目为“北行见杏花”,作于被俘北上的途中。于是下阕写出了宋徽宗见到杏花后,有感而生的痛楚。这首词被王国维拿来和李煜的作品比拟:直笔
尼采谓统统笔墨,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天子《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出生之感...........《人间词话》
这里也授予了杏花以人类的情绪特色。
说到宋徽宗这首词,顺便提一下唐朝吴融的一首《途中见杏花》,题目和宋徽宗的挺像,这首诗有一个版本是最早提到“不安于室”的:
一枝红杏(或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长得看来犹有恨,可堪逢处更难留。
林空色暝莺先到,春浅喷鼻香寒蝶未游。更忆帝乡千万树,澹烟笼日暗神州。
这首诗和宋徽宗的词,都特意写了“见”这个字。喜好诗词的朋友可以品一品宋徽宗与吴荣异同之处。
四、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的杨花与叶绍翁的杏花
1、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有一首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开头有六个字:
似花还似非花。
我们用这六个字,来剖析一下叶绍翁《游园不值》的杏花。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不安于室来。
可以看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整首诗毫无疑问是写景。但是后两句杏花时,明显与陈与义和陆游笔下的杏花不同。由于这只”出墙“的杏花,更随意马虎引起遐想。
叶绍翁的杏花有没有其他含义呢?
用苏轼的话来说,真得很恰当:似花还似非花。
2、 不同于张先、苏轼、赵佶的花
但是叶绍翁的杏花,又和张先”犹解嫁东风“的桃杏不同,也和”随风万里,寻郎去处“的杨花不同,后两种有明显的拟人手腕。
我们看看苏轼这首“似花还似非花”的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斟酌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词中的杨花,和张先的”犹解嫁东风“、赵佶的“新样靓妆”一样,也是把花当作人来写。
我们会创造,叶绍翁并没有特殊明显给杏花以人的特色和感情。
3、类似于柳宗元《江雪》
我们不清楚,从主不雅观来说,叶绍翁的杏花是不是和柳宗元的《江雪》那样,背后一定有深意: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和陆游陈与义一样,肯定便是写一个植物而已。
之以是说类似《江雪》,是由于我们理解柳宗元的创作背景。大多数人认为《江雪》不仅仅是写景, 柳宗元在主不雅观上用景语反响其情绪,表达自己遭遇贬谪仕途运蹇的孤寂。
但是叶绍翁是不是主不雅观上就如此呢?不好说。大概是、大概不是,似花还似非花。
五、作者未必是,读者何必不是
一个作品写成往后,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由读者完成。清朝学者谭献也有”作者未必是,读者何必不是“的说法。我们引用西方的说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便是说,叶绍翁写完这首诗往后,无论他主不雅观上是不是纯挚写景不主要,主要的是读者怎么看。
雍正期间,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结果被认为讽刺朝廷丢了性命,便是一个例子。
苏轼的”乌台诗案”也由于其诗文被解读出多重含义,以是被敌人捉住,差一点丢了性命。
也便是说,无论墨客是否有此意,但是作品中却可以让读者遐想到此意。
用黄晓明的话说: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结束语
王国维说,统统景语即情语也。但是在创作时,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不一定“统统”景语都是情语。
这种不动声色,却把景语写成情语的,有时是墨客是故意为之,有时是无意为之。不管叶绍翁是不是故意为之,他并没有写出后来“不安于室”的含义。
在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似骑不安于室”之语,把不安于室比作一种不检点的行为 ,这该当是别人的发挥了。
至于作诗的时候,实在很多墨客是喜好利用多重含义这一手腕的,似花还似非花?让读者猜去吧。
@老街味道
黄庭坚说杜甫作诗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王维的《鸟鸣涧》与我们常见的绝句 在构造上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