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样的问题,解释你或许还不是很理解诗词哟!
用本日已经被当成梗的一句话来说:“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
”
下面,我就举一些例子来讲一讲古代诗词中的化用、借用的情形,以及它们同抄袭的差异。
借句:另类的拿来主义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都会创造这样有趣的征象,即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墨客诗词中看到,为此,我们常常惊异不定。同时,当我们被问及某句的出处时,也时常由于这个缘故原由而闹笑话。
古诗词中常常会涌现照搬古人句子,或者进行略微加工便挪用的情形,我们可以将这称为借句。这每每是由于情景共通,或者对作者推崇备至,到了写诗的时候便脑筋里自然浮现,信手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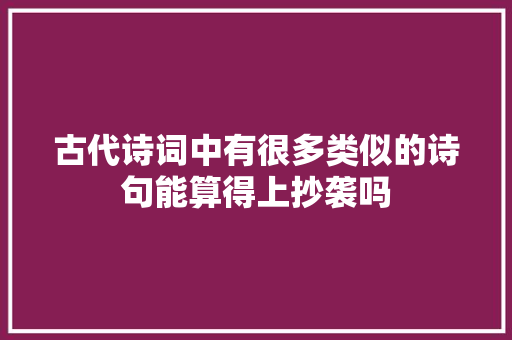
比如其他回答里提到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最开始出自于唐朝墨客李贺的《金铜神仙辞汉歌》: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节选)
这句诗寄寓了非常深奥深厚的古今兴亡之感,读来给人以痛切感,在当时十分出名,也被许多文人雅士推崇利用。
宋代一个叫石延年(曼卿)的人在赠友联中,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上联,对出下句“月如无恨月长圆”,也是震荡四座。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对此就评价说:
“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对‘月如无恨月长圆’,人以为劲敌。”
但这还不算完,宋朝词人贺铸在其《行路难·缚虎手》当中直接将李贺的一整句全部引用,词云: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节选)
相似的,宋朝欧阳修在其《减字木兰花》、明代陈继儒在其《集情篇·七》、清代程颂万在其《玉楼春·再集十阙》中同样有引用,当然不止如此。而我们最熟习的则是毛主席《七律·公民解放军盘踞南京》中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句。
毛主席对付李贺诗句的化用,完备改变了原诗悲哀感慨的基调,转而授予诗句积极昂扬的革命乐不雅观主义精神,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
通过上面的这个例子,你或许会创造,古人的借用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拿来主义”,而是一种更如“旧瓶装新酒”的创新之举,或者称“另类的拿来主义”,其通过详细的诗境、情境进行翻新再创造。恰如一个马克杯,放在办公桌上便是办公室的一份子,放在寝室书架上便是学习生活的一份子,放在阳台藤椅旁玻璃桌上便是闲应时光的一份子。
这样的情形绝非个例。
宋代诗词当中引用唐人诗句的例子就很多,但他们实际上不仅仅是引用诗句,连更早时候的一些古谚语和古诗也会引用。当然,这也绝非是宋人开的先河,我们所熟知的曹操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一句便是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当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句子。
化用:读书人的事
化用在古诗词当中也非常常见,或是直接化用句子、或是化用诗词的内蕴、或是化用诗句的写作方法。这类做法每每不将诗句直接引用,而是会变动一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创作。
这样一听,彷佛还和本日的“洗稿”有一点相似。但同样的,化用诗句有化用的好的,乃至远超原句,当然也有化用的差的,落了下成。
例如初唐墨客沈佺期在《钓竿篇》中曾有一个体致的譬喻,即“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这句诗再后来便被许多墨客化用,我们最熟习的有李白的《江上赠窦长史》中“人疑天上坐楼船,水净霞明两重绮”,杜甫的《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等。
对此,《优古堂诗话》中还有记载评价到:
《潘子真诗话》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杜子美诗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盖触类而长之。」予以云卿之诗,盖原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诗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
明明是自己的诗句,被化用之后反而被说不如后人——看到这里你可能要为沈佺期鸣不平了,但别急,由于这句诗、这么奇特的譬喻本身也就不是他的创始。
沈佺期的这两句诗实际上也是化用了古人的诗句,即东晋王羲之的“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与南朝陈释慧标的“舟如空中泛,人似镜中行”两句。
这种情形在古诗词当中同样多见。当一个人读得多了,肚子里有货的时候就很随意马虎随口成诵,化用古人的诗句,并且翻出新意,化为己用。
对付这种行为,古人的容忍度是很高的,大家也对此颇为认可,彷佛正印证了那句话“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
但是,化用的好不好,自然全凭本事了。
举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即上文提到的宋代贺铸的《行路难·缚虎手》: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匆匆。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
这首词中化用之处极多:
“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化用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仰天算夜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直接借用李贺《金铜神仙辞汉歌》原句。“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似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当垆秦女”化用辛延年《羽林郎》诗:“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语如弦”化用韦庄词《菩萨蛮》:“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以上列出的这几处是化用较为明显的,其化用不明显的同样很多,席卷了《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世说新语·赏誉》、《后汉书·陈蕃传》、曹植《名都篇》、《离骚》、《史记》和李益、韩琮诗里的词句等多处。
但难得的是,这首词作化用奥妙,能够将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且变得独具一格。因此 叶梦得也评价这首词说:
掇拾人所摈弃,少加櫽括,皆为新奇。
贺铸自己在谈及作诗的时候也说:
“吾笔端使令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厨密《浩然斋雅读》引贺语)
这解释化用他人的诗句和诗意是贺铸惯用的手段,但他的声名鹊起也反响出时人对此的认可。
抄袭:过度的拿来
百科里对抄袭的释义为:
抄袭,指盗取或修正他人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在相同的利用办法下,完备或者部分完备(设定.念白.观点.台词.场景.图片.等...)照抄他人作品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形式或内容的行为。
但实际上,抄袭的界定十分困难,并且抄一句和抄十句的差距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却很少。人们近年来对付版权、抄袭等关注很多,但有时候难免矫枉过正。
抄袭的行为我们自然该当是抵制的,纵然是诗词中的借用拿来也该当有一定的限度,有自己的创新。并且,抄袭者的主不雅观目的多是恶劣的,比如为自己扬名等等,纵然在中国古代也同样存在抄袭的征象。
但由于古代传播媒介的限定,人们能够打仗到的文献很少,大多数时候只能够凭借影象,因此想要纠察抄袭也是困难的事情。但在本日,在网络传媒等助力下,抄袭行为很随意马虎便会被曝光。
总而言之,借用化用他人的诗句是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独特征象,是墨客们在深受古人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模拟和引用,不宜过分指摘。
但对付主不雅观恶意的抄袭行为,我们应该严厉抵制,争取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
如果想要理解更多汉语和文学知识,请关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