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叶永烈与本文作者1979年在天津日报大楼前合影
我与叶永烈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时,我采写了《名家与新秀——访高士其和叶永烈》。我们从此结缘。他性情敦厚、谦和,彼此视若同学兄弟。他喜好新闻,原想报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后来考了化学系。我们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我长他几岁,1957年同年考入大学。他上北大化学系,我入复旦读新闻。更有趣的是,1951年,他11岁时,在温州小学上五年级,《浙南日报》揭橥了一首小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投稿。也是1951年,我在郑州读初中一年级,第一次投稿《郑州日报》,在报屁股登了个小豆腐块。中学期间,他写诗数百首;我为报社写稿百余篇。“事情狂”是我们相同的雅号,哪怕累得吐血也无怨无悔。直到古稀之年,他仍满负荷运转,昼夜兼程写新作。2014年,他将手稿、书信、照片、档案资料、采访条记、采访录音带,装满一卡车,捐赠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他建立了“叶永烈专藏”。2017年,我把积存的数百本采访本,分别捐给母校复旦大学和公民日报社社史办公室,并做了展出与收藏。
我们曾经互助编辑出版过一本《科学家诗词选》,他卖力采集京沪科学家诗词,我采集天津科学家诗词。今春,我编辑出版了《一个老的镜头缘——王学孝影集》,特意给叶永烈一个专页,孰料这竟成了对朋侪的永久纪念(叶永烈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
叶永烈出身是理工男,走的却是文学创作路,成为高产作家,生平出版180部作品,3500余万字。他写作速率极快,文思泉涌,挥洒自如,日作5000字。从前用圆珠笔,手指磨砺成皮开肉绽的老茧。后来用电脑写作,如行云流水,逐日10000字。他从不打草稿,打好腹稿,一气呵成。1979年一年多,他出版14本书,130万字。《高士其爷爷》是20万字的传记,开40个夜车,即完成初稿。那时,他还在上海科教制片厂事情,没有创作假,全靠业余采访写作。其间,他还为报刊撰写各种文章近200篇,有人戏称他为写稿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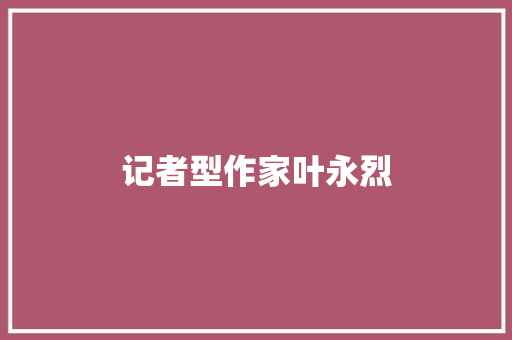
叶永烈早期作品,紧张是科普类和科幻小说。他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紧张撰稿人。个中化学分册175篇,他撰写了163篇。当时他还在大四读书。天文气候、生理卫生、农业平分册,很多篇也由他撰写。初版5个分册中的《十万个为什么》,三分之一是他写的,发行上亿册。我家祖孙三代爱读他的作品。2014年,增订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印行,我特意为小孙女购得一套。他21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也是脱销书,成为广大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精良读物。前些年,将一款手机命名为“小灵通”,用户不下一亿人,这意味着至少有两亿人在“消费”叶永烈。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科普科幻写作,转向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传记文学创作,相继推出赤色系列、玄色系列、名人系列。创作此类作品,须要作大量采访,用他的话说,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他的书是“跑”出来的,一部书每每要采访数十,乃至上百人。跑路、采访,是做的基本功,叶永烈是名副实在的型作家。他说,采访是很辛劳的活儿,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这一行实际是干的活儿。他通过大量采访,用文艺笔法写党史、写人物,在撰写《赤色的出发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时,他从党的出身地上海和嘉兴南湖,沿着赤色革命路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不辞费力,奔波万里,实地踏勘采访。而采访重大事宜、主要人物,光能跑路还弗成,还得有过人的本领,方能有所获。一样平常人与一些传主,根本连一壁之缘都没有,他却有通天之力,靠着广泛的人脉轻松拿下。他很早就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熟习,通过于夫人采访陈云,挖出许多宝贵口述史料。陈伯达刑满开释后,没有接管过任何人采访,唯有叶永烈得以进行独家专访,写出《陈伯达传》。
叶永烈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讲究史实的完备准确,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准确。他说,文章有百分之一虚假,读者就会疑惑全体作品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纪实文学亦然,这与对采写新闻的哀求毫无二致。他外出采访时,总是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旅行袋,里面放着“三机一本”:录音机、摄影机、小型摄像机和条记本。他捐给上海图书馆的采访录音带,有好几铁皮箱。他每采访一个人,都要与之留有合影。他的纪实文学作品,采写的人物都是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他的作品富有当代史文献代价,为后世供应丰富的历史素材。将来如有人回顾当代历史,一定会去看叶永烈的《1978:中国命运大迁移转变》《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这些书。
追逐社会热点问题,是的本能,哪里涌现热点,叶永烈就奔向哪里。2001年,“9·11”胆怯打击事宜发生越日,他就同妻子杨惠芬乘机从上海飞往纽约。当时他已不是年轻小伙子,已届花甲之年。临行时,他们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便匆忙上路了。那天,机场安检极为严格,可乘几百人的飞机,仅有十几位搭客。他们就在世贸大厦废墟附近的旅社住下,旅社里连窗户也不能开,由于空气里弥漫着呛鼻的焦味。《受伤的美国》一书,便是由于他抢先进入采访而抢先写成的——这一点,我们做的自感汗颜。
“作家要关注社会、关注生活,这点与你们是一样的。但作家还得要深刻地认识,深刻地思考。”叶永烈如是说。(王学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