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长安城夜景剧照
那么我们如何来概括唐朝呢?我想用下面五个词来描述:
第一个词是“天下主义”。“天下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最常用来描述唐朝的观点。比如《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早在1973年出版的《唐代概不雅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中就用“天下主义”来概括唐代的中国文明,而日本著名的唐代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也以“残酷的天下帝国”来描述唐朝。这种天下主义的特质是憨实、原谅,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再造了中国文明,进而带来了宗教、文化、制度、知识的残酷和辉煌。唐代尤其是盛唐之前,华夷之辨并不霸占主流。唐太宗认为四海之内不论华夷,都是自己的子民。彼时盛行的佛教强调众平生等,部分化解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构造以及华夷之间的壁垒。更为范例的例子便是粟特人(Sogdian)。这些被称为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的族群,“利所在无不至”,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他们不但连通了中国和域外的商业网络,还充当了大唐的使节、将士、音乐人、画家等,给大唐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比如随着龟兹等地的中亚音乐的传入,宫、商、角、徵、羽中土五音音律的固有缺陷被不断寻衅,“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以琴瑟、钟磬为乐器的时期过去了,音乐进入了新的期间。又如武则天期间,一个叫安金藏的粟特人,本是太常乐人,为了保护当时的皇储李旦,剖腹以证皇储未曾谋反,被称为“义士”。安史之乱后中国文明逐渐走向民族主义,而粟特人却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这或许是中国人长于做生意的部分基因来源。
第二个词是“佛教帝国”。如果我们把隋唐和其他朝代比较较,就会创造那是一个佛教繁荣的时期,唐朝可谓是一个“佛教帝国”。上至政治宣扬、意识形态,下到日常生活、节日习俗,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响。大唐的长安和洛阳的天涯线被佛塔所装点,人们的心灵被笼罩在佛光下。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带来了宗教崇奉的传入与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领悟,也带来了险些全面的知识和不雅观念的改造:地理知识、宇宙不雅观、生命循环、措辞系统、新的艺术形式、风尚习气、城市景不雅观等。这种文化领悟和再造,不但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更是高度发达的知识和崇奉体系之间的磨合。仅仅从政治史的层面讲,佛教对未来美好天下的描述,以及对空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数百年中,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改造、建筑空间等方面。武则天正是在佛教繁荣的背景下,才能以佛教转轮王的身份登上皇位。又比如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佛教兴起之前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分为“官”“民”两种空间,像用于国家敬拜的礼仪空间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的涌现,在官—民的构造之外,供应了双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间的场域;城市空间在世俗空间之外,也涌现了宗教(神圣)空间。从《两京新记》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读出这种变革带来的城市活力。如果我们比拟汉朝的长安和唐朝的长安,就会创造,这是两个完备不同的城市——唐朝的长安是一座佛教都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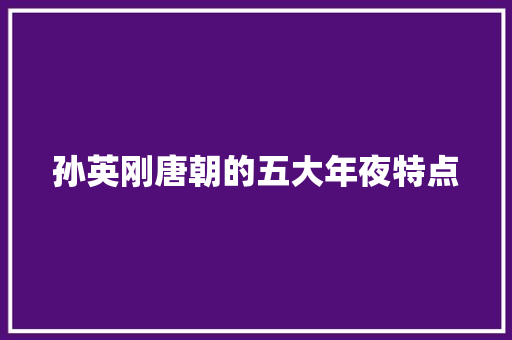
《妖猫传》中的日本僧人
唐代的中国,在宗教崇送上处于文化上风地位,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思想天下最为繁芜繁密的一部分,唐朝也已经成为当时全体佛教天下的中央。正如近代以来欧洲传教士到东方传教,唐代时中国佛教强势对外传教,比如日本把佛教引入本国,各大宗派都视长安的某个寺院为自己的祖庭。佛教对日本文明的再造起到非常大的浸染,直到现在仍旧这天本人主要的心灵家园。佛教的传入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主题,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贝。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景教也便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摩尼教、祆教或者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中国,让大唐文明呈现出憨实残酷的景象。
第三个词是“贵族政治”。你如果穿越回唐朝,可能会创造出身很主要。以是我们在隋朝和唐代前期,看到了大量权势熏天的皇子政治集团:隋朝的晋王杨广攫取了太子杨勇的储位;唐朝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去世了自己的兄长和弟弟,攫取了皇位;唐太宗的几个儿子也跃跃欲试,觊觎着最高权力。各大家族各自下注,乃至两边下注,希望能延续自己的政治地位。乃至外姓的武则天攫取了李唐皇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天子。唐前期,险些没有一个太子能够顺利继续皇位,终极真正继续大统的每每是残酷宫廷斗争的胜利者。初唐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催生了一大批个性光鲜的政治人物,中晚唐的政治史同样很精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皇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皇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比如,中晚唐时宦官的崛起,他们的权力来自天子,是皇权的延伸;又如僧侣,中世纪欧洲的教士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恪守独身的原则,割断了跟大家族的联系,而在中国,佛教僧侣在特定情形下也成为皇权的主要支持者。
第四个词是“律令制社会”。唐朝是一个律令社会,非常讲究律法和制度。从制度创新上说,它进一步发展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对周边文明都有影响。我们以前对科举制度有非常多的批评,乃至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当代化,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很不公正的。如果放在全体人类文明史上看,科举制度可以说是非常主要的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非常大的贡献。说到底,科举制度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近代英国开始进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时候,考试的内容还不如我们的科举制度—英国考《圣经》。以是问题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其详细的社会功用以及政治功用。考试的内容是大家诟病的地方,但制度本身是非常主要的发明。唐代的科举制度在最初并没有改变贵族社会的实质,比较寒门子弟,士族子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上风准备考试,让科举变成有利于自己的新的游戏。但是随着韶光的推移,科举在唐朝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崛起,取代了以前依赖家族出身决定政治出息的贵族阶层。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的四百余年中,法制领域涌现了一个连绵不绝且逐浪飞腾地强调法典浸染和地位的历史运动。法典浸染和地位的持续上升,至唐永徽二年(651)及开元二十五年(737)臻于顶点。安史之乱往后制订法运动迅速跌落:法典修订长期结束,《律》《令》成为具文,形形色色的敕例反而成为法律过程中最为主要的依据。历晚唐五代及于宋初而再度向近乎秦汉旧式《律》《令》系统编制发展的轨道复归。大略地说,初唐的律法具有一定威信,乃至能平衡皇权,唐太宗非常强调法律的严明性,抑制“朕即法律”的冲动,这是大唐盛世法律根本;但是之后天子的“王言”又压倒了律法,成为最威信的法律来源。
第五个词是“神文时期”。从汉代到隋唐,虽然学术与思想几经变革,但是就政治论述而言,总归不脱神文主义的总体架构。纬学为经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其他知识体系,比如天文、气候、音律、历法、祥瑞灾异、阴阳五行,乃至许多崇奉体系如佛教、玄门,无不与其紧密干系。这些知识和崇奉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天下和崇奉天下。在中古时期弥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中,人类天下是定命秩序的反响,晚至唐代,这种宇宙不雅观依然在学术和思想上霸占显著的位置。我们会看到唐代政治操作中频繁涌现天象、祥瑞、灾异等谈论,一点都没有自欺欺人的意思。包装皇权、打击政敌,每每会引入天文星占和祥瑞灾异。唐代的这些知识传入日本,结合日本本土崇奉,发展成安然时期的阴阳道传统。
唐代禁谶不禁纬,纬书仍被视为六经的主要补充,而且谶纬之书并非神文思想唯一的载体,中古时期大多数的知识体系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例如《五经正义》中就屡引纬书,因而遭到清儒皮锡瑞等激烈批评。更不要说庾季才、吕才、李淳风等节制“术数”知识的群体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真正对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定命说提出寻衅的,紧张发生在中唐往后。宋代新的儒学潮流兴起,将佛、道、谶纬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力乱神都排挤出正统学术体系。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谶纬才终极衰绝。反响到其他知识领域,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取消自汉朝以来诸史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而不载事应;《新唐书》虽有《五行志》也仅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从政治思想方面说,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往后,在北宋中期往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从神文到人文,从定命说到王者仁政说,这是唐宋之际思想变革的一大面相。
以上是我总结的大唐的五大特点。不过,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可能还是大唐的国力壮大。唐高宗期间,经由八十多年的战役,唐朝破灭了地区强国高句丽,奠定了东亚长期的政治格局。在这场战役当中,朝鲜半岛在新罗的旗帜下统一,日本干预大陆事务的企图遭到了挫败,之后的将近一千年,日本都没有入侵大陆的操持。唐朝在对内亚的游牧民族战役中也取得了打破性进展,先后攻灭东、西突厥,把中国的影响力拓展到中亚腹地,这是前所未有的主要造诣。
中国历史的主要迁移转变点也发生在唐朝。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从中亚退出。从思想上说,安史之乱引起了唐朝思想界的转向。唐中期往后,哀求回到中国古典文明的呼声日高,佛教也被视为外来文明成分,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带有文艺复兴性子的文学、思想运动,以及唐武宗以行政暴力伤害佛教,将佛教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系中打消出去。唐朝在走向民族主义的同时,自动放弃成为佛教天下领导者的角色。思想天下的变迁,改变了唐朝士人的代价不雅观,连带文学格调、社会不雅观念也发生主要变革。
总体而言,隋唐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期间。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帝国是秦汉,经由三百年的分裂、战乱以及种族和崇奉的冲击领悟,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明,中华文明又实现了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明之以是能够耐久不衰,生生不息,最主要的缘故原由在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就开放性而言,中国文明展开双臂拥抱外来文化元素,将其变成自身传统的一部分,比如佛教;就创造性而言,隋唐时期呈现得非常明显,三省六部权力制衡的政治系统编制、文官考试制度等,均为周边民族和国家效仿;中国博大开放的文明更吸引了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高僧、士人、贵族子弟。
(本文系孙英刚精讲隋唐史系列的“导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