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词牌名,别号“踏雪行” “踏云行” “柳长春” “惜余春” “转调踏莎行” “喜朝天” 等。以晏殊《踏莎行·细草愁烟》为正体,双调五十八字,前后段各五句、三仄。另有双调六十六字,前后段各六句、四仄韵;双调六十四字,前后段各六句、四仄韵变体。代表作品有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等。
《踏莎行·细草愁烟》——宋代· 晏殊
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阑总是销魂处。日博识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带缓罗衣,喷鼻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东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这首诗见于晏殊《全宋词》,北宋期间,天圣五年(1027年),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在此期间,他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又称“睢阳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首创大办教诲之先河。庆历三年在宰相任上时,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传授教化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形成一种广兴文学的浪潮,这便是有名的“庆历兴学”。晏殊临春之季不禁有感而发,以物抒怀,感叹光阴的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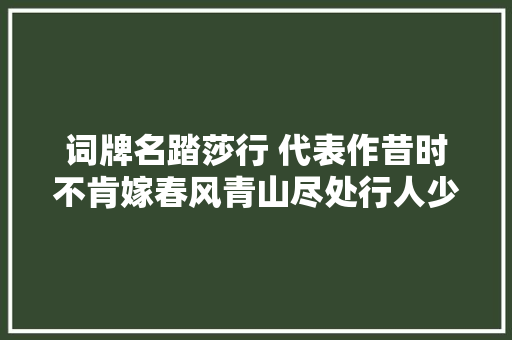
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光阴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李调元说:“晏殊《踏莎行·细草愁烟》极流丽,而以翻用针言见长。如垂杨只解惹东风,何曾系得行人住?又东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等句是也。反复用之,各尽其致。”这段话,恰切地点出了此词的艺术特色所在,全词通过写景抒写离愁、思念和慨叹,充满了悲惨悲哀的感情色彩。”
《踏莎行·候馆梅残》——宋代· 欧阳修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考证,欧阳修这首词当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3)暮春,是作者从前行役江南时的作品。
此词紧张抒写早春南方行旅的离愁。上阕写行人客旅的思念。以时空的转换,写人在旅途,流落无际,且无止期,从而展示了游子剪不断的离愁。下阕写居者对高楼的企盼和悬想,写了望之人的内心活动。春山本无内外之别,词人将其界定,写出居者念远的迷茫心境。全词寓情于景,蕴藉深奥深厚,是为人所称道的名篇。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高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构造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这种透过一层从对面写来的手腕,带来了强烈的美感效果。
整首词只有五十八个字,但由于奥妙地利用了以乐写愁、实中寓虚、化虚为实、更进一层等艺术手腕,便把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以是成了人们乐于传诵的名篇。
当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首,上片写行人忆家,下片写闺人忆外。起三句,写郊景如画,于梅残柳细、草薰风暖之时,信马缓步,一何清闲。“离愁”两句,因见春水之不断,遂忆及离愁之无穷。下片,言闺人之怅望。“楼高”一句唤起,“平芜”两句拍合。平芜己远,春山则更远矣,而行人又在春山之外,则人去之远,不能目睹,惟存想象而已。写来极柔极厚。
《踏莎行·郴州旅舍》——宋代· 秦不雅观
雾失落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词大约作于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作者初抵郴州(今属湖南)之时。词人因党争遭贬,远徙郴州,精神上倍感痛楚,故作词抒写客次旅舍的感慨:上片写谪居中寂寞凄冷的环境;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朋侪殷勤存问、安慰。全词以委婉弯曲的笔法,抒写了失落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此词为作者绍圣四年(1097)作者因坐党籍连遭贬谪于郴州旅店所写。当时作者因新旧党争先贬杭州通判,再贬监州酒税,后又被罗织罪名贬谪郴州,削去所有官爵和俸禄,又贬横州。此词作于离郴前。
元祐六年(1091)七月,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秦不雅观从苏轼处得知自己亦附带被劾,便急速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秦不雅观的失落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讦,而苏轼与秦不雅观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奇妙的变革。有人认为,这首《踏莎行》的下阕,很可能是秦不雅观在流放岁月中,通过同为苏门朋侪的黄庭坚,向苏轼所作的弯曲表白。
清·王国维《人间词话》: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此淡语之有情者也。
《踏莎行·杨柳回塘》——宋代· 贺铸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清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宋史·文苑传》载贺铸“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他出身崇高却长期屈居下僚,其心中的苦楚是一样平常人难以体会的,于是作此词以咏心志。
这首词是咏荷花,寄寓了作者的出生之感。词的上阕描绘了一个详和而宁静的池塘。而荷花却成长在池塘僻静处,只能寂寞地凋落。就象一位美女,无人欣赏,无人爱慕,饱含零落的凄苦。词人通过美人的自嗟自叹,也暗露了自己年华的虚度。下阕仍借美人之口言志:纵然凄风冷雨,我仍旧不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开放,甘心盛开在炎炎的夏日。荷花、美人、君子,形成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南唐中主《浣溪沙》云:“菡萏喷鼻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均《离骚》句。)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是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偏安小国的君主为自己不可知的出息而发出的嗟叹的。晏几道的《蝶恋花》咏荷花一首,可能是为小莲而作。其上、下片结句“照影弄妆娇欲语,西风岂是繁华主”和“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与这首词“无端却被秋风误”和“红衣脱尽芳心苦”的用笔用意,大致附近,可以参照。
由于古代墨客习气于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出处之节,以美女之不肯轻易嫁人比贤士之不肯随便出仕,以是也每每以美女之因择夫过严而迟迟不能结婚甚至延误了青春年少的悲哀,比贤士之因择主、择官过严而迟迟不能任职甚至延误了建立功业的机会的痛楚。曹植《美女篇》:“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杜甫《秦州见敕目薛、毕迁官》:“唤人看腰袅,不嫁惜娉婷。”陈师道《放歌行》:“东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虽立意措词有所不同,但都因此婚媾之事,比出处之节。这首词则通体以荷花为比,更为蕴藉。
作者在词中隐然将荷花比作一位幽洁贞静、出生飘零的女子,借以抒发才士沉沦腐化不遇的感慨。《宋史》“虽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这些记载,对付理解此词的深意颇有帮助。
《踏莎行·春暮》——宋代· 寇准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喷鼻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这是一首即景写闺情的小令,情致缠绵,属伤时惜别之作。此词上片重在写景,暮春时令,微雨濛濛,自然界的春天呈现一派寂寥无人的景象;下片紧张抒写离情,写两人别后没有音讯,引起思念之情。全词风格清新,措辞明白晓畅,以细腻而幽美的笔触刻画暮色景物的衰残、画堂风光的孤寂,进而透露人物内心的惆怅和迷惘,外在与内在交汇,情怀与物象相通,激荡回旋,错综交织,谱写成一首伤春念远的闺怨心曲,委婉有致,真切动人,活画出这位独守空闺的女性对付羁旅天涯、久客不归的心上人的无限思念和一片深情,显示出婉约派高度的艺术技巧。
全词由描写景物起,又由景渲染情,将暮春时节一位闺中思妇怀念久别爱人的孤寂情怀抒写得委婉动人。上片写景,来由景生,景中有情;下片写情,寄情于景,以景结情。情景交融,意境浑然,于是情经景纬,织整天机云锦。
《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宋代· 姜夔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作者二十多岁时在合肥(宋时属淮南路)结识了某位女郎,后来分离了,但他对她一贯眷念不已。淳熙十四年(1187年)元旦,姜夔从第二故乡汉阳(宋时沔州)东去湖州途中抵金陵时,梦见了远别的恋人,写下此词。
前三句纪梦,借用苏轼诗句以“燕燕”形容梦中人体态的轻盈,“夜长”以下皆以背面敖粉,设想伊人对自己的相思之深,声吻毕肖,实则为作者自抒怀怀。“离魂”句经幽奇之语写出伊人梦绕魂索、将全部生命投诸爱河的深情,动人心魄。末二句为传世警策,描写伊人的梦魂深夜里独自归去,千山中唯映照一轮冷月的清寂情景,显示了作者无限的爱怜与谅解,意境极凄黯,而感情极深厚。这首词以清绮幽峭之笔,抒写一种永不能忘的深情,朴拙动听。
这首词紧扣感梦之主题,以梦见情人开端,又以情人梦魂归去扫尾,意境极浑成。词的后半部分,尤见幽绝奇绝。在构思上借鉴了唐传奇《离魂记》,记中倩娘居然能以出窍之灵魂追逐所爱者远游,着想奇妙。在意境与措语上,则又领悟了杜诗《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咏怀古迹》“画图省识东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句意。妙在自然浑融,不著痕迹。
《踏莎行·小径红稀》——宋代· 晏殊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东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蒙 通:濛)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喷鼻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此词写暮春闲愁,上阕写郊野暮东风景,蕴含淡淡的闲愁,将大自然春之气息表现的淋漓尽致,下阕写身边的春景,进一步对愁怨作铺垫,表达了词人面对光阴匆匆逝去的无奈和哀伤。全词以写景为主,以意象的清晰、主旨的朦胧而显示其深美而蕴藉的魅力。
初读起来,结尾两句彷佛和前面的景物描写有些脱节,主人公的愁绪来得有些溘然。实际上前面的描写中固然流露出对春暮夏初的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的欣赏,另一方面又隐含有对已逝春光的惋惜。由于这两种抵牾的感情都不那么强烈,就有条件的共处着。当深院闲居之时,惋惜之情转而繁殖。结尾两句便是后一种感情增长的结果,由于这种春愁只是一种时序流逝的惆怅,以是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淡淡的轻愁,并没有否定前者。
《踏莎行·情似游丝》——宋代· 周紫芝
情似游丝,人如飞絮。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舟住。雁过斜阳,草迷烟渚。如今已是愁无数。明朝且做莫斟酌,如何过得今宵去。
周紫芝生活在南宋,亲历宋代社会的巨大变迁,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离去成为家常便饭。作者与情人将要离去,难以表达自己心中的哀愁与不舍。故作者作此词,意为送别相思之人,用以反响出有情人的无奈。
词的上片写离去时的情景。一对恋人在绿柳垂丝、柳絮飞舞的春光中,在水边依依惜别;下片写别后的留恋与相思,愁绪无数,无法排解,仍写居者行人走后的惨恻情怀。这首词蕴藉深婉,情景交融,几入化境,愁苦之味溢于言表,通过对分别情景的描述和别后相思之苦的传达,婉转地抒发了词人的无限离愁别恨。
《踏莎行·晚景》——明代· 陈霆
流水孤村落,荒城古道。槎牙老木乌鸢噪。夕阳倒影射疏林,江边一带芙蓉老。风暝寒烟,天低衰草,登楼望极群峰小。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
这首词是通过写秋日傍晚的荒凉景致来抒发沉沦腐化天涯的凄凉心情。宋柳永《玉蝴蝶》:“晚景萧疏,堪动宋玉凄凉。”
作者在写这首词时,时在深秋,人在贬所(他因得罪当时炙手可热的宦官刘瑾而被贬安徽六安),可谓是时亦凄凉,人亦凄凉。
词的上片写秋日傍晚的景致,点出词人当时所处之地,暗含贬臣的幽怨之情;下片写登楼所见及所感,化用古人诗意而独出心裁,触发万古迁客骚人最深奥深厚、又最难以排解的思乡之情。全词凄迷哀婉,愁思无限,于羁情中寓贬愁,景悲人亦悲,写尽了离去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