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喷鼻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纵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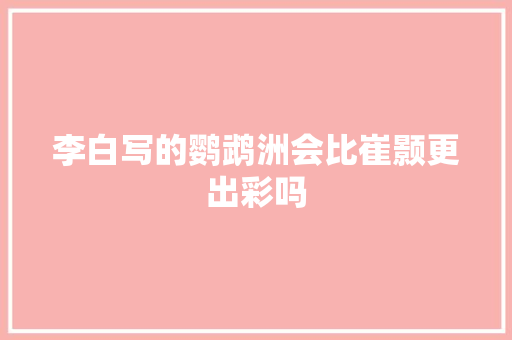
提到“鹦鹉洲”,首先浮上我们脑海的想必是崔颢的“唐人七言律诗之首”——《黄鹤楼》中的“萋萋鹦鹉洲”吧!
殊不知,其实在此之外,还有一位冠绝诗坛的大家也为鹦鹉洲进行了走笔赋诗。《鹦鹉洲》是唐代“诗仙”李白的一首拗体七律。全诗一反李白惯现的飘飘乎如羽化登仙之诗风,呈现出来的是意境浑融,情绪深奥深厚的效果,通过对鹦鹉洲的描述,实则吊古伤今,委婉地抒发了墨客慨叹祢衡才高命蹇终被杀的痛惜之情,同时抒发了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悲愤之情。本文将通过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以及“七律不工”三个方面对《鹦鹉洲》展开品鉴与剖析。
一、鹦鹉洲的渊源与《鹦鹉洲》的创作背景
鹦鹉洲,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是江夏的名胜。但是大众对它的理解普遍比较片面,所得印象大都来自崔颢的名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相传,鹦鹉洲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宗子黃射大会来宾时,即席挥笔而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言及祢衡,不得不说他是鹦鹉洲的灵魂人物。因祢衡“尚有刚傲,好矫时慢物”(《后汉书·祢衡传》),对曹操“数有恣言”,而被曹操转交给刘表欲借刀杀之。仍反面,遂再度被转送到江夏太祖黄祖处,终因托物抒怀搪突了黄祖,黄祖怒气冲天,杀之。下笔千言却一气呵成、文不加点的《鹦鹉赋》也从此成了大才子祢衡的绝笔之作。尔后黄祖悔憾不已,将祢衡葬于洲上。
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刚毅刚烈不阿、任性敢言使得无数文人骚客赋诗词曲文于鹦鹉洲上,或哀叹出生,或借此思念,其在墨客心中的地位绝不亚于黄鹤楼。尤其是诗仙太白,关于祢衡的诗作将近二十首,个中最著名的是前面提到的《望鹦鹉洲怀祢衡》,而本文探究的《鹦鹉洲》更是有一段有妙趣横生的背景故事。
李太白《鹦鹉洲》成诗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年(760年)。《唐才子传》有记载,因在永王叛乱中受到牵连而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的李白,次年携友登黄鹤楼,但见云天开阔,纵目千里,俯瞰长江,滔滔东去。不禁触景生情,感时伤怀,油然而发思古之幽情,不觉诗怀躁动,成作于胸。猝然见到崔颢所题《黄鹤楼》,玩味良久,自知心中之作不能赛过崔诗,叹道:“面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哲匠敛手。然末了还是写下了吊古伤今之作《鹦鹉洲》,但后人一度认为这是崔颢《黄鹤楼》之仿作且远不及其,乃至高度赞赏《黄鹤楼》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只管亦有研究认为这里的“第一”不是指造诣而是指在七律发展史上涌现的韶光,这段公案仍旧成为诗仙创作史上的白璧微瑕。
而笔者更认同下述不雅观点:“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因此文笔行之,一气迁移转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以是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故意学之而自似。”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方氏所论还是比较相符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奥深厚,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二、《鹦鹉洲》的全诗内容与思想感情
“鹦鹉来过长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更觉一泄如注、席卷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戛然收束更给人意犹未尽的淋漓之感,然而回顾蓦然发觉诗篇已过半。哪里真的是歌颂鹦鹉来过呢?“鹦鹉”看似实写,实则代指祢衡,“鹦鹉名”,紧张是指祢衡以及他的一朝即席呵成的《鹦鹉赋》千古留名却憾成绝笔,而不是专指鹦鹉雁过留痕,可谓妙极的一语双关,虚实并用。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此句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成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鹦鹉已踪迹无觅,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回溯了祢衡在此地被杀的感伤情境。又是意蕴深远的双关手腕。因此,墨客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俏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正如您,我崇敬的祢衡,羽化登仙驾鹤西去啊。情韵深邃,余味无穷,表现了墨客对祢衡的无限追忆与绵远幽思。
这四句诗一唱三叹,气势雄浑磅礴却又灵动富节奏美,读来朗朗上口又荡气回肠。它是墨客的艺术创造。个中词语的重叠涌现,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利用,设问的发人深省,同崔诗比较,实在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堪称匠心独运。
“烟开兰叶喷鼻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五六两句转向写景,诗意开始迁移转变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述了鹦鹉洲上妖冶的春光:远了望去,鹦鹉洲上,五彩缤纷,水气环抱,花之冶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东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繁,在微风中摇荡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喷鼻香,令人陶醉而感想熏染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时令,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犹如朵朵红云,相互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残酷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春景如此妖冶娇艳,为下联描写“我”的心情埋下铺垫,正所谓“乐景衬哀情”的范例利用。
“迁客此时徒纵目,长洲孤月向谁明。”纵使景致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墨客的欢畅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墨客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面前这统统活气勃勃的自然好风光跟二心坎的落寞痛楚正好形成了强烈的比拟。春光甚好花红柳绿,都只是徒有。自己生平颠沛流离,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贫乏,只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晚年壮志,但终不免付诸东流。颈联尽数描述的景致并不是他的关注点所在,他所凝望的仍是“鹦鹉”,是这位和自己遭遇相似的祢衡。“诗圣”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李白的才华。墨客对月发问:如今,祢衡就葬于这片地皮之下长眠,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三、《鹦鹉洲》\"大众七律不工\"大众及其缘故原由探究
接下来,我们剖析一下《鹦鹉洲》的平仄: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
鹦鹉西飞陇山去,方洲之树何青青。 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
烟开兰叶喷鼻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迁客此时徒纵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
仄起,首句不入韵,庾韵,第四句韵脚“青”出韵。首联出句第二个字“鹦”当平而仄。颔联出句第六字“山”当仄而平拗,第五字“陇”当平而拗救;对句第五字“何”当仄而平,不仅使得全句仅一“树”字是仄声,而且造成三平调 。全诗只有颈联对仗,而“鹦鹉”一词和“洲”字在诗中三现。综上可见,这是一首“不工”的拗体,可古可律。正如《唐诗别裁》语:“以古笔为律诗,盛唐人每有之,大历后,此调不复弹矣。”
而曾遍读李白其他七律后,我们可以创造,李白七律大多不工,存在拗句和失落粘征象。这是什么缘故原由造成的呢?
笔者认为,首先,这是由当时七律系统编制尚未完备这一文体发展现状决定的。在李白创作生动的开元、天宝年间方回说\"大众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大众;赵翼说\公众七律尚未盛行\"大众,直至安史之乱之后的乾元元年春,王维、岑参和杜甫唱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才是七律开始盛行的契机。而这时,\"大众青莲久已出都\"大众,故所作已不多矣。
其次,是太白对\"大众兴寄\公众的追求。他感叹诗歌的衰落,明确反对六朝以来那些内容空虚乏味、一味追求形式富丽的作品和浮艳淫靡的文风。同时,他又是颇具抱负并充满自傲的,他要使诗歌规复古道,推崇刚健有力的\"大众建安风骨\"大众,清真自然是他倾力追求的诗歌审美最高境界。《古风》59首及大量乐府诗或述怀言志,或刺时讽世,无不表现出墨客强烈的社会任务感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而几首七律的内容则局限于友朋赠答和登临怀古,题材相称\"大众私人化\公众。可见,太白彷佛认为那些承载了\公众兴寄\"大众的重大内容不适于用七律这种强调形式的诗体加以表现。
同时众所周知的是,太白个性张扬,作品中的情绪表现极具个性。一方面是突如其来,如彭湃的波涛般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一方面又呈跳跃式创造,倏忽变革,纵横驰骋,跌宕起伏。这种情绪,更适宜篇幅自由、句式灵动,章法多变、格律哀求宽松的歌行来表现,而七律在格调声韵方面有严格的哀求,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墨客自由抒发自己豪放不羁的情思。诚如赵冀所云:“(李白)盖才华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
究其因,盖当时七律尚未完备成熟,李白在创作上既追求\公众兴寄\"大众,又张扬个性,故七律作品数量虽少,仍有助于七律提升格调,拓展内容和深化内涵。
结语:题曰鹦鹉洲诗写鹦鹉洲,实则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墨客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此外,李白《鹦鹉洲》与崔颢“千古擅名之作”《黄鹤楼》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不落窠臼,富有匠心独运的艺术成绩,在思想高度和历史秘闻上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地,“不工”的七律丝毫不掩作品本身的意境雄浑与情绪深奥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