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忧吟西涧诗
公元七百八十三年,也便是唐德宗建中四年,韦应物接到诏谕,由尚书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刺史。这虽然不为重用,滁州刺史也不是肥缺,但对韦应物的生平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迁移转变,在他的人生史上是一件不屈常的事。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韦应物出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一个世代做官而富有艺术教化的家庭。他的曾祖父韦待价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祖父韦令仪做过宗正少卿和梁州都督等官;父亲韦銮是一位很有成绩的画家。韦应物十五岁那年,一半沾了祖上官品高的光,一半由于他仪表健美、机灵聪慧,选进了宫廷,做了唐明皇的侍卫“三卫郎”。史料记载:唐制天子的禁卫军分亲、勋、翊三卫,常日选取高等官员子孙中“年少壮”“仪容整美者”。这时的韦应物少年得志,狂放不羁,他自己说自己“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安禄山之乱后,韦应物退出三卫,折节读书,进了太学,自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年间,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尚书比部员外郎。
韦应物手捧着诏谕,心头却另有一番滋味。他认为朝中有人排挤他,使他丧失落了京官。虽然尚书比部员外郎只是个六品官,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京官要比地方官高一等,何况自己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仕途上只有末了一站了。以是,他感到不平,心绪愤懑。可他又以为有几分甜蜜、宽慰,虽然滁州户不敷二万,属于下州(唐代官制:四万户为上州,二万户为中州,不敷二万户为下州),但作为刺史,仍是个正四品官,比员外郎又升了两品。当然,更紧张的是刺史系一州之主,有着对公民同情而又想施展一番抱负的韦应物,认为这正是显露才华、造福百姓的好机会。于是,他欣然接管,择日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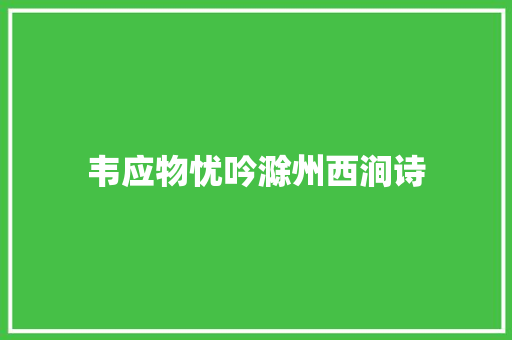
初夏,韦应物轻装独身只身离开长安,登舟南下滁州履新。风催浪推,弯曲提高,舟行数月,驶进黄河。韦应物特立船头,展望前景,即情抒怀道: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
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闪动乱流中。
孤雁几发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
为极洛桥游官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夏尽秋至,水陆并进,昼夜兼程三个月,韦应物抵达滁州。
滁州虽然不大,但它的地理形势险要,西北清流山中清流关是南来北往的要冲,西边是庐州,东边是楚州(今江苏淮安),襟山带河,为“江淮保障”。原来的滁州“山川之清峻,城廓之宏丽,风尚之敦庞,名宦人物之奇瑰雄杰”,冠于一方,堪称名郡。可是,面前的滁州,多年来由于唐皇朝和藩镇军阀的强取豪夺、搜刮剥削,加之水旱磨难,已经满目疮痍和贫乏冷落。
韦应物信步走进滁州城,只管他对困难早有思想准备,可是,还是被眼睛的景象惊呆了:城廓破墟,街面冷落,百姓干瘪,店铺倒闭。他容身巡视,这才弄明白朝中人不愿到此做官的起因,原来这里“四面尽荒山,州贫人更稀”!
看惯京城繁华场面的韦应物,不禁感叹:“景致殊京国,邑里但荒榛。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
目睹滁州的荒漠景象,韦应物心中甚难堪受,决心救民于水火。经由一番察视,他打算从蠲免百姓的赋税动手,逐步振兴滁州。当时赋税重叠,徭役繁多,百姓债务缠身,精神上压力沉重,生产难以规复。韦应物亲自撰写上疏,列举百姓困苦,治政困难,哀求减赋免税,分别呈扬州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唐朝中、后期,除中心委派官员到各地外,又在边疆和主要地方设节度使,掌管当地的军事大权。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权力扩大,在其辖区内任意扩军、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当时滁州行政上从属扬州大都督府,军事上由淮南节度使统领,因此,欲要减免赋税,必须哀求扬州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
上疏呈送多日,韦应物翘首愿望,得到冷冷两个字:不准!
年夜志勃勃的韦应物看了批复,意气消沉,烦恼愤慨,可又无能为力。晚上,他一人孤坐于书斋内,窗外秋雨沥沥,归雁声声,引起他无穷思绪。时期的乱离,公民的苦难,官场的纷争,牢牢地裹着他的心。他想摆脱,他想弃官,他想回到相隔两千多里的长安家中,可统统又是徒劳。他只有把一片心、一片情、一片思虑、一片愤懑藏的诗句中,他挥毫而就——
故宅眇何处?归思方悠哉。
淮南秋雨夜, 高斋闻雁来。
韦应物低吟着,雨声、雁声相和,浮想联翩,触绪万端,泪洒诗笺……
恶劣的环境,不顺心的公务,折磨着韦应物的意志。他常常想“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扔下乌纱帽,回家种良田;又常常“聊假一杯欢,暂忘终日迫”,借酒消愁,彷佛变得无所作为起来。实在,他并非真的冷漠统统,只是对政务不热心,对朝廷和上司胡弄搪塞,对庶民百姓却时时关念、事事掩护,一片情意。他在处理政事之余,常常寄情山水,沉醉民情,或者登山临水,或者种花种药,或者留连阡陌。
滁城西南的琅琊山,险要而奇丽,其山峰屹然而特立,其深谷窈然而深藏,林木茂密,花草各处;山中琅琊古寺,雄伟壮不雅观。韦应物常常前往,登山不雅观景,还和寺中僧人结为朋友,交谈和诗,但他并没有被山水沉溺,仍旧惦记着政务、公民。寺中方丈僧挽留他,他婉言道:“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辉崇冈。……物累诚可遣,疲甿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
秋逝冬临,景象渐寒。一天夜晚,韦应物想到新交识的百里之外的山中羽士。这位羽士正在全椒西三十里外的神山寺中艰巨修炼,韦应物想为他送去一瓢酒,为他驱寒除寂,可又转念到,这些人都是逢山住山、见水止水的人,本日还不知在哪儿呢。再说这满山落叶,脚印都难以找到,觅人更难,不如作首诗,遥寄于他。于是执笔而书:
目前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韦应物尤为喜好步入城郊,参加田舍种药植树,不雅观田舍劳动,咏诗赞颂他们,与田舍同乐。天降瑞雪,他和农人一样高兴,咏唱道:“飘散云台下,缭乱桂树姿,厕迹鸳鹭末,蹈舞丰年期。”尤难堪能名贵的是韦应物每每在诗中流露对田舍的同情和崇敬,对朝廷官吏的鞭笞和自责。一日傍晚,韦应物独自闲步到城西西涧处,见劳累一天的百姓疲倦而归,牛贪婪地饮着西涧的水,触景生情,慨然吟道: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壮年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恩惠膏泽且为喜。
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爱民、敬民、惜民之情渗透字句其间,自责、解剖、怒斥之意袒露其表,令同辈佩赞,使后人崇仰……
冬去春归,转眼间韦应物到任近一年了。春天的滁州自然界景致俏丽诱人,可是,韦应物却掩门谢客,心情忧闷。
原来,头年十月朝廷发生了叛乱,长安城被盘踞,德宗天子仓皇出逃。传到滁州,韦应物一壁忧虑皇家的安危,一壁顾虑骨肉的存亡,便派人北上长安打听。可是,一去数月,人未归,情不知,朝廷如何?家人安否?韦应物发急满腹,心绪不宁。其余,自己作为朝廷行政官员,有志改革而无力,到任一年,无所作为,也感到于国于民都有愧色。他给远方的朋侪写诗曰: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次圆。
书应物盼到五月,探者归来,叛乱平息,家中无事,悬着的心平定不来。不久,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换人,韦应物心头升起几丝希望,原来的上司搜刮抢夺,鱼肉百姓,不听下属只言片语,独行其是,新的上司大概不会如此吧?振兴滁州的大志又萌生复起。于是,异昼夜办公,撰写上疏,评叙滁州现状,设想管理方案,希望得到上司支持和重视。可是,这时有人也捉住机遇,在上司面前告他的“刁状”,说他太严刻“刚略”,滥用权益“取威于懦夫”。没等他的上疏奏报,朝廷的诏谕降到:罢韦应物滁州刺史职。时在公元七百八十四年底,德宗兴元元年。这一年,韦应物四十八岁,任滁州刺史只有一年半。
韦应物双手抖动,忿恨交加,撕碎上疏,摘下乌纱,锐气全泄,喃喃自语:“先哲庄子说得对呀,‘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餍饫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自己光忧国忧民,但无有能力,无所作为,枉做一年多剌史。”此时,眷念长安,怀思骨肉之情油然倍增,归心似箭,恨不得乘风飘到家人中间。可是,无奈他任职期短,又不忍搜刮民财,经济情状颇窘,他在诗中描述说:
昨日罢符竹,家贫遂留连。
部曲多已去,车马不复全。
做了一年多刺史,连回家路费都难以凑足,其清廉真可歌可泣!
韦应物一时没有力量返回长安,只得暂住滁州。他搬出剌史府,来到西涧旁闲居。
西涧源于滁城东南林壑幽美的琅琊山谷中,距城一里多路,溪水经年不息,自西向东,穿滁城而过,因其紧张河道在州之西而得名。当年西涧景致十分柔美,春暖时令,绿柳婆娑,芳花烂漫,百鸟啁啾,水映蓝天;一到暮春时节,桃花水发,溪涌泉喷,涧水飞涨,犹如江潮春涌。韦应物在职时,公务之暇,常常醉卧不归。
韦应物临涧而居,每天不雅观涧水,听泉声,赏花草,闻鸟鸣,以表面清闲而掩饰笼罩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忧伤。言为心声,诗为真情。他写诗叙情道:
寝扉临碧涧,晨起淡忘情。
空林小雨至,圆文遍水生。
永日无余事,山中伐木声。
知子尘喧久,暂可散烦缨。
除此以外,他在涧边栽花、种药、植树,装扮西涧,造福于后代。
当然,韦应物更多的韶光用在“聊将横吹笛,一写山水音”作诗抒怀上。这期间他写了《滁州西涧》《简寂不雅观西涧瀑布下作》《西涧种柳》《种药》《乘月过西郊渡》《再游西郊渡》《西远足瞩》等诗篇,个中《滁州西涧》为名篇,传诵最广,历代视为绝唱。诗曰: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春深时令的傍晚,韦应物独自一人立在西涧边,深情地看着茂盛可爱的小草,耳里传来不解人间之事的鹂声,久久不愿归回自己的陋居;溘然,大雨如注,涧水上涨,犹如春潮,郊野渡口,本来人少,水急舟横,更无人问津。此情此景唤起墨客的遐思,触动了墨客的灵感,千古传诵的名诗流出内心。墨客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好与不喜好的景物,说自己合意与不合意的事情,而其胸襟恬淡,情怀忧伤,自然流露渗透个中,从而把他的山水诗推到了无可复加的地位。
韦应物在西涧闲居半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出任江州刺史,依依别离了西涧绿水,告别了滁州百姓,又去施展抱负,寻求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