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研究《红楼梦》,就硬说它写的是“反清复明”;研究《西游记》,就强说它写的是“炼丹过程”;研究《水浒传》,又说它写的是张士诚农人叛逆的底细等等。
话说在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正是大唐天宝十二年“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有一个失落意落魄的文人逃难到了苏州这个地方。
某一天,这个文人独宿于江畔的一条小船上,半夜霜寒露重,愁不能寐,于是他提笔写下一首七绝。这首诗由于冲破了一些“创作规律”,被北宋欧阳修斥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
谁料欧阳修骂了它,它反却是以出了名。北宋期间,这一带的地方官为了达到“文化宣扬”的目的,专门请人为这首诗立碑作传,因此带动了附近一座寺庙一带的旅游不雅观光家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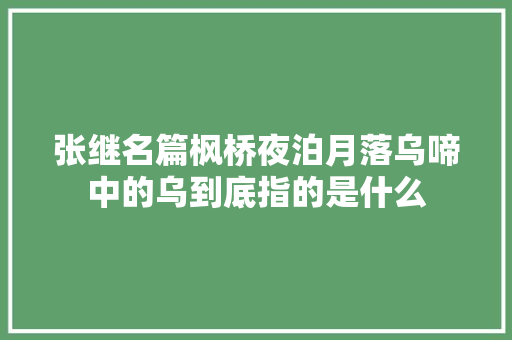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韶光不知不觉又过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间,这首诗漂洋过海,到了日本,溘然就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作。
民国期间,中国一个叫俞樾的文化贩子有时在日本创造了它“很走红”,于是就又把它带回中国,再一次刻碑撰文,大力推广。
后来,经由俞氏三代人(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的努力,这首诗就成了“唐朝在外洋影响力最大的七绝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枫桥夜泊》,写出它的文人便是张继。
原文如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枫桥夜泊》被考据出的“四大谜题”前面我们说过,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流派中,最扯淡的一派便是“考据派”。而在近代努力推广这首诗的俞氏家族的俞平伯,恰好便是“考据派”中一个主要人物。
六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红学家”便是俞平伯。在俞氏的影响下,许多“考据癖”在考据《红梦楼》之余,又开始考据《枫桥夜泊》。他们经由这首诗,开拓出了四大“谜题”,分别为:
其一、这首诗写的这天间,还是夜晚;
其二、霜明明是落在地面上的,为何墨客说“霜漫天”;
其三、一千多年前,寒山寺的和尚是否会在半夜敲钟;
其四、“乌啼”里面的“乌”,到底是哪一种鸟儿。
在这四个问题当中,一千年前辩论得最激烈的是“夜半钟声”的问题,最早提出疑问的自然是欧阳修。他的情由也很大略,由于和尚“夜半”敲钟是违反知识的。
古代没有电灯,故此古人都习气早睡早起。寺庙里有做晨课、晚课的习气,一样平常是在清晨的六、七点钟起床做“晨课”。
然后吃一顿早饭,到了下午五六、点吃完晚饭,再做一场“晚课”。到晚上九点就睡觉了,岂有“半夜”十二点爬起来“敲钟”扰民的道理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墨客和学者,忽然跳出来与欧阳修争辩,说自己从前听到过寒山寺的“夜半钟声”。
一千年以来,关于这首诗的绝大部分争议,都集中于“寒山寺夜半钟声”的悬念上,偶尔大家也会谈论一下关于降到地面上的霜,是怎么被张继弄到“漫天”飞的。
不过一贯没有什么人去研究“乌啼”的“乌”,到底是哪一种鸟?直到2013年,海内有一个“考据癖”兼“边缘动物学家”才另辟路子,开始研究“月落乌啼”中的“乌”,到底是哪一种“乌”。
这位“考据癖”提到,最初有人说诗中的“乌”,指的是乌鸦。但是乌鸦这种动物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它一样平常每天都要睡10个小时以上。
以是乌鸦只在清晨和傍晚叫一叫,然后很早就去睡觉去了,怎么会和寒山寺的和尚一样,半夜深更爬起来“搞事情”呢?
于是这位“边缘动物学家”说,诗里的“乌”是指“乌臼鸟”。古书上的确有这种鸟的记载,比如明代杨慎《丹铅录》中先容:“乌臼,五更鸣,架架格格者也。如燕,玄色长尾,有歧。”
但是这里仍旧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从杨慎的描述,我们完备看不出乌臼这种鸟和乌鸦有什么差异;第二个是这种鸟五更天叫,那便是在“清晨”时分啼叫,而不是在“半夜”。
后来又有人指出,北方的乌鸦常常在凌晨五点多就开始鸣叫。这么一看,就更搞不清张继写的是哪一个品种的“乌鸦”了。
由于这个缘故原由,于是就有人说“乌啼”中的“乌”,并不是指鸟。“乌啼”是一个名词,它指的是寒山寺附近的“乌啼山”。然而这座山的得名,恐怕还是在《枫桥夜泊》这首诗成名之后。
二、文学创作,须要想象美就这样,“考据癖”们的考据,越走越偏,让人看了直想发笑,于是网友们常常骂这些专家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你考据了那么多的“周边知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七绝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吗?文学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拿着放大镜去抠字眼儿的人,便是真正的“门外汉”。
李白写“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时候,你咋不去考证一下,哪个人类的头发可以长达三千丈呢?
王维写“人闲桂花落”,这是写秋日,然后他又写了“夜静春山空”,你咋不去研究一下,王维是怎么让时空扭曲,同时看到秋日、春天两种景象的呢?
再有,王维也写过一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你咋不去研究一下这个“月出”,又“惊”到了哪一个科目、种类的鸟呢?
“寻章摘句老雕虫”,完备不懂文学创作的灵魂便是要有想象力,便是要有“虚构”。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没有负责地读过南朝的《文心雕龙》,更不知道诗歌最讲究“意象”的丰富性。
诗歌天然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非要把诗中意象化的事物给具象化,就即是是年夜煞景致,大煞风景了。
结语欧阳修对付《枫桥夜泊》这首诗的评价,虽然略微有一些抠字眼的嫌疑,但是“夜半钟声”这种情形的确是违背常理的。
至于有人说自己的确是听到有寺庙在半夜敲钟,只能借鲁迅的话来说: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
关于有人提到张继诗文中的“乌”,到底是指一种鸟,还是一座山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千多年来都没有人辩论,只有当代才有人开始辩论呢?
那是由于,在过去只要稍有古诗创作知识的人都知道,“乌”在诗里只能是“乌鸦”,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由于写诗是要精挑细选“意象”的,“乌鸦”在古诗中便是一个成熟的意象,它有固定的内涵,比如象征去世亡、象征恐怖与不祥等等。
中国古代墨客正是靠着这些词汇丰富,同时又是“大众都知晓”的意象,以“公共之措辞”来引发读者个人的遐想,创造出“含隐”之美,即“我说了,我又什么都没说,全都是你想出来的”。
像这种致力于打通墨客与读者的“任督二脉”,共同完成诗歌创作的高等审美技巧,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接管美学”兴起时才学会。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中国的“考据癖”们,为何这么“实心眼儿”?有人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学唯物论学到走火入魔了,太重现实主义,老想着在统统文学作品中去探寻“背后的真实”。
他们分不清什么是“文学虚构”,什么是“社会现实”。于是不只《红楼梦》写的是反清复明,就连金庸写个武侠小说,当中的少林寺出了几个反派,也会有人站出来抗议“曲解了佛陀”。
小时候读《枫桥夜泊》,觉得这首诗是有“声”有“色”的。“月落乌啼”是大自然的声音,夜半钟声是来自尘世中的声音。“霜漫天”是洁白的颜色,“江枫”又是血一样的艳赤色。
鸟叫声与钟声,反衬出苏州城外夜晚的宁静之美。虽然由于当时的年纪小,不太读得懂诗的含义,但是也能感想熏染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之美。
但是后来看到“考据癖”们的考据,原来会啼鸣的“乌鸦”,彷佛也变成了一座不会开口的“哑巴山”,切实其实让人无语到凝噎。
以是“一根筋”的人,完备就不适宜搞文学研究。“考据癖”们切实其实便是文学创作的杀手,他们的存在对付文学而言,切实其实是太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