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喷鼻香袅袅,如翠云轻绕;春泉泠泠,似玉珠落盘;茶韵悠悠,若仙子轻吟。在这方寸之地,光阴仿佛一瞬间凝固,尘世的鼓噪渐行渐远。
反复吟咏中,笔者对作者的平生充满了好奇。不知是何等人物,能以寥寥数语,绘就出这般令民气驰憧憬的山居生活?
张可久(约1279——约1354),字小山,庆元(今浙江宁波)人。他是元代著名散曲家,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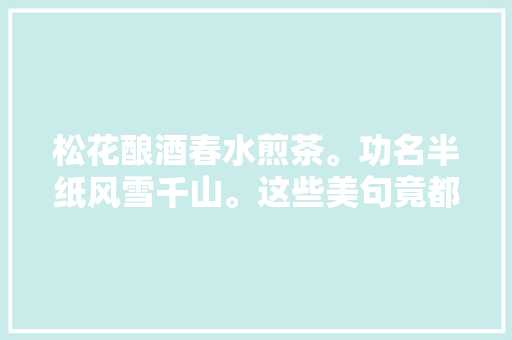
他专致于散曲创作,尤擅小令,与卢挚、贯云石等人常相唱和。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小山乐府》、《吴盐》等散曲集。
在中国散曲史上,张可久以其作品之丰、造诣之卓,独步曲坛。据《全元散曲》所辑,计有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成为元代散曲作家中著作流传最广者。
明人李开先赞誉他为“词中仙才”,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中有李杜”。
我们在品读张可久的散曲时,能够领略到凄婉之美、悠远之情、清雅之风、蕴藉之韵,感想熏染到那份超越时空的艺术传染力。
与曲坛上的显赫声名相反,张可久的平生业绩犹如隐匿于光阴深处的幽兰鲜为人知。然而,穿越光阴的迷雾,我们依稀可见那身影,从历史的长河中缓缓地走来。
他出身于书喷鼻香门第,饱读诗书。“忆淮阴年少,灭楚为帅,气昂昂汉坛三拜”,少年时的他刻苦学习,博闻广记,聪明过人,从小就承继了传统儒士建功立业的民气抱负。
青年时,他显露出过人的才华。约二十岁旁边,为延揽荣誉,求得进身之阶,张可久怀揣着对仕途的渴望,离开家门开始游历。
他投书于仕宦权贵之门,广交文士名流,以期铺开自己的青云之路。
作为一名深具传统气质的文人,张可久不知疲倦地辗转奔波,和当时许多有名的官员和学士交游唱和,游山玩水,流连于酒筵歌席。
可是,命运却未能眷顾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为求取功名,他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终极换来的是仕途的无望和经济的困窘。
待千金散尽,貂裘破敝,归来的是一个全身风尘、满怀落寞的失落意者。张可久纵有万般无奈和心伤,都只能凝于笔尖,记录下一个文人的坎坷与悲辛。
只可叹,他生逢异族统治的元朝,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占统治地位的独特朝代。
自蒙古族入主中原,不但科举被取消,法律还明文规定“人分四等”,汉人、南人居于蒙古人、色目人之下。
南人便是指末了被元朝所灭亡的南宋统治的南方汉族与其他民族。当时就指江浙、湖广、江西等省的各民族公民。他们的报酬最低,备受歧视,处于最下等。
伴随着宋元王朝的更迭,科举制度还一度陷入沉寂。在中国北方,科举的停摆更是长达七十九年。这段结束的空缺期,是饱学之士们一段漫长而无望的等待。
时期的车轮滚滚向前,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的一纸诏书重新点亮科举的灯火,为士子们燃起新的希望与机遇。
张可久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怀着满腔的豪情和热切的期待。当梦想即将照进现实,他无比激动的用笔墨抒发着内心的振奋和喜悦:“翰林风月多进才,满袖东风下玉阶,执金鞭跨马离朝外,插金花坠帽歪,气昂昂胸卷江淮。昨日在十年窗下,今日在三公位排,读书人真实高哉。”
他遇上了科举,结果显然是败了。由于元朝的科举在合格人数、考试标准等方面,带有民族歧视色彩,对待蒙古人和汉人大有差别。其余,还规定政府和各级官吏的紧张官职不能由汉人南人担当。
广大南人士子纵然满腹诗书,究竟被间接拒之于科举大门以外。张可久恰属于最受歧视的“南人”身份,在《殿前欢·客中》一曲中,他将内心深处的悲愤与不甘流泻于笔端:
望长安,出路渺渺鬓斑斑。
南来北往随征雁,行路困难。
青泥小剑关,红叶湓江岸,白草连云栈。
功名半纸,风雪千山。
岁月无情,曾经斗志昂扬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染霜。这些年,他像一只怠倦的征雁南来北往,四处迁徙。一起的困难险阻,印刻着流落的足迹,无情的风霜,催老了客子的容颜。
为求得个半纸功名,不得不奔忙于风雪千山。张可久毫无保留地表露了半生奔波的酸楚与心底的隐痛。
这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感慨,也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处境的写照。科举的复兴,让他们的“用世”之心有所萌动,现实的境遇又让他们体会到心被撕碎的悲冷。
到头来,功名不过梦一场。元代法制根本没有专供儒户的做官之路,知识分子是被边缘化的。“半纸浮名,十载功夫”,愤激不平的喟叹,道尽了他们无声的控诉与悲哀。
仕途的挫折与磨难,逐渐消退了张可久昔日的年夜志。为缓解生理的压抑与沉重的包袱,他自然地转向了一条历代失落意文人所走过的路——归隐。
像那些先哲一样,他于青山绿水间,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将空想与抱负寄托于大自然的山川湖泊之中。
从前颠沛流离的张可久,崇尚曾在杭为官的苏轼,钦羡隐居西湖的林逋。他视杭州为精神的故乡,故把杭州选为定居地,生活渐趋稳定。
他留恋杭州的湖光山色,使女塔影。杭州西湖,也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他写下很多西湖的散曲作品,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普天乐·西湖即事》是他夜游西湖时即兴的佳作:
蕊珠宫,蓬莱洞。
青松影里,红藕喷鼻香中。
千机云锦重,一片银河冻。
缥缈佳人双飞凤,紫箫寒月满长空。
阑干晚风,菱歌高下,渔火西东。
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书剑飘零,浮云无定,怎能不唤起张可久心底对归隐田园的渴望呢?他神往的生活,是放情烟霞、诗酒自娱般的恬淡欢愉。他喜好的隐居之所,是一处宁静古朴、无车马之鼓噪的宁静之地。
如今他寓居西湖边,有“万卷”书读之不尽,“松花”“春水”取之不竭,平日里饮酒作诗,读书品茶,如此雅事足以抚慰悠悠岁月。
在这片栖息之地,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得以放来世俗的负累,享受到难得的清净与清闲。就像他在《人月圆·山中书事》一曲中说的那样: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落家。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此曲浅近朴实,写得尤为风雅,感情由浓至淡,由激愤至沉着。
朝代更迭,盛衰无常,英雄荣辱,皆若梦幻泡影,须臾即逝。滚滚长江,东逝不返,历史的长河中,统统繁华终将归于尘土。
昔日孔子的儒家风范,吴王的雄图霸业,楚庙的江山社稷,如今安在哉?唯留古木参天,蔓草荒漠,寒鸦数点,诉说着世事的无常与岁月的沧桑。
一个“倦”字,凝聚了张可久多少岁月的风尘奔波之苦,暗藏了多少落拓不遇的郁郁之怨。这些年,他定是饱经了世态的炎凉,民气的无常,才终于勘破了尘世的虚妄,对这骚动的风尘生出了深深的厌倦。
在杭州这个风月之地,于俏丽的西湖之畔,得与刘致、贯云石等官宦名流相交,张可久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逍遥清闲的岁月。
这段光阴里,他的散曲创作水平日臻成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日渐攀升。醒来明月,醉后清风。于山水田园中寻觅灵感,随情自适,一韶光,张可久彷佛体验到文人诗意的栖居。
然而,正当他沉醉于创作的欢愉之时,灵魂深处对付功名未竟的遗憾和人生失落意的感伤,时时地刺痛着他的神经。
只管他的名声日益显赫,但这并未给他带来仕途上的本色性转机。安逸舒适的隐居生活背后,仍旧暗藏着难以言说的苦闷。
“小山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四十多岁以前,张可久还未走上入仕之路。直到元延祐七年(1320),已过不惑的他经文友推举,离开杭州前往绍兴,担当绍兴路吏,后又到浙西衢州任路吏。
像张可久这样的儒生,未能由科举入仕,转而充任胥使,每每是他们后半生的普遍归宿。
元统元年(1333),他离开衢州,在短暂地过了一段或隐或吏的生活后,再次回到杭州居住。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杭州,又相继担当婺州路吏、桐庐典史、新安松源监税等职,直至70岁时,还任昆山幕僚。
二十年间,他奔波于吏途,时吏时隐,对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剥削百姓的丑态早已切齿腐心。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一次次举夺由人,直至亡故异域。
儒家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纵不雅观张可久的生平,他一贯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生平怀才不遇、沉滞下僚,终不能一展怀抱。
在儒、道思想共存下,人生时常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他的生平是悲剧的,就像没有作别仪式的剧目一样平常,在无声中悄然谢幕。
在冷落苍凉的人生基调上,张可久的仕途之路毫无波澜。正如其自道“十年落魄江滨客,几度雷轰荐福碑,男儿未遇暗伤怀”。
张可久的人生经历可叹可泣,终其生平他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既不能任性洒脱地归隐田园,又无法真正融入官场,跋前疐后,旁边难堪。这种内心的冲突与彷徨,正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
元代,是文民气灵遭受重创的时期。元曲,是文人悲剧的写照。那些散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们的精神风貌和心中的苦痛挣扎。
张可久笔下那种深婉宁静、疏放幽美的意境,实则是他用以抒发郁结、排解愤懑之情的主要路子。读他的散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想熏染到他的抵牾与痛楚,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情。
然而,正是在绝望的熔炉中经受过的精神淬炼,铸造了张可久在文学上的卓越造诣。本日,当我们在低回中吟咏这些散曲时,不仅能体会到他的哀愁与思虑,更能从中汲取坚韧与聪慧的力量。
作者:溪月,喜好诗词,愿用厚重作纸,清淡作笔,书写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