嘞呃复哦哦,晚五重朝九。
才诵诗书礼,又唱易春秋。
笑言卷中味,可抵饭喷鼻香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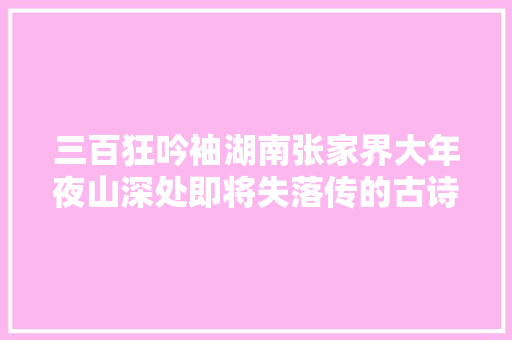
这是笔者追忆家公(土家族的“家公”即“外公”)肖先生长西席而写的五言诗,描述的正是家公诵唱古诗歌时的情景。我一贯以为家公的这种古诗歌诵唱法,可能只是老教书师长西席特有的读书习气,乃至有些老土,便没当一回事。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家公每天早晚都会坐在阶檐下诵唱诗歌,几十年如一日,直到2008年去世。说实话,家公这种诵唱古诗歌的“激情亲切”和执迷,我一贯是不理解的。
图为笔者家公(即外公)肖大明先生长西席
直到2019年笔者回到老家,当我再次回顾家公诵唱诗歌的情景,并试着用家公的古诵唱法唱诵了几首诗歌后,溘然创造这种古诵唱法实在并不大略!
尤其是笔者试着诵唱了几首屈原的《离骚》,觉得特殊顺畅,与平时用普通话读屈原的诗歌完备不一样!
普通话读屈原的诗有些拗口,用古诵唱法唱屈原的诗时,诗歌中的情、境、意、韵,便尽显无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烦闷忧伤,时而高山流水,时而春暖花开。这使笔者对中华古诗歌有了新的理解,当即写下了《诗载论》一文,并考试测验着写了一些古体诗歌,个中就包括《忆家公四首》。
用古诵唱法唱屈原的诗歌特殊流畅
如果用“古诵唱法”诵唱我自己写的诗歌《忆家公》,其唱法是这样的:
三百(~)狂吟袖(呃~),
一山(~)洒唱丘(哦~哦)。
嘞呃(~)复哦哦(呃~),
晚五(~)重朝九(哦~哦)。
……
一、笔者对"古诵唱法"的理解与思考:楚文化与蜀文化领悟的产物我的家乡在湖南张家界桑植县北部与湖北恩施鹤峰县交界的龙潭坪镇(央视“天梯上学”新闻曾宣布过的地方),龙潭坪镇是一个真正隐蔽在大山深处的山村落儒士之乡,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读书欲望。在龙潭坪镇暗藏的小山村落里,曾住着一批未被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老学堂师长西席,个中就包括我的家公肖大明先生长西席。新中国刚成立时,这里曾一度连续保留着古老的学堂教诲办法。至于本文所先容的“古诗歌诵唱法”为什么终极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留存下来,我以为有三大缘故原由:
(1)地理位置。我结合卫星舆图查看了老家的地理位置,这里正处于武陵山区腹地,四面环山,以正我的家乡为半径,正北方是长江流域巴蜀段,分别坐落着云阳、奉节、巫山、巴中、秭归、宜昌等历史文化名城。北起湖北巴东县城,南至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景区,刚好是北纬29度之31度之间,网络上火热的“北纬30度文明”之说也适用于全体大武陵山区,而实际也如此,比如长江沿岸的诗歌文化,而武陵腹地的恩施山歌、桑植民歌,都是非常有名的。这里高山重重,四季分明,这样的地理位置确实有利于诗歌艺术的产生和传承。
于是,笔者便有了这样的思考,楚辞的精确唱法,可能便是恩施山歌和桑植民歌,同属武陵山歌。而屈原的《离骚》,很可能便是武陵山歌而已。
图为笔者家乡龙潭坪镇的地理位置
(2)文化渊源。由于地处高山重重的武陵腹地,这里的劳动人民天生喜好唱山歌,也是情理之中的。山歌文化和诗歌文化本是一脉相承,楚文化和蜀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在武陵山区形成相对稳定的诗歌文化传承习俗,也是顺理成章的。比如笔者的嗲嗲(即“爷爷”),曾经便是一名“山歌大王”,常常跟十里八村落的人对山歌。我至今也依稀仍记得有一些山歌是这样唱的:“你唱的山歌嘞没我多,我唱的山歌几巴篓壳,老鼠子啃断一匹篾,去脱七八百嘞……”,“你唱的山歌嘞是我的,我唱的山歌夹船拖哦,我到河里宠瞌睡儿,你从我插口里抠去的嘞……”,这个“巴篓”,也写作“笆篓”,但笔者以为,该当为“巴篓”,该当是起源于古代巴蜀的一种运输工具,目前在张家界的桑植屯子仍旧存在(笔者家里也有)。大家留神一下这首山歌的断句,是不是跟楚辞很像?同是湖南人,但武陵山区的人是听不懂湘方言,而同属于西南官话的四川话、湖北话,跟张家界武陵山区的人互换起来却没问题。屈原的出生地是秭归,由此可以判断,屈原《离骚》的唱法,该当靠近于武陵山歌的唱法。
综合这些成分,基本可以判断,遗落在武陵山区的老学堂师长西席的诗歌古诵唱法,该当跟楚辞的唱法差不多,只有方言上的细微差异。
古代"巴篓"的存在是印证楚文化和蜀文化在武陵山区腹地交融的活化石
(3)历史成分。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交通相对便利的长江一带和湖南武陵山区以外的文化难免经历不同的演化,但武陵山区腹地由于相对封闭,也很有可能相对保存了古代诗歌文化和诵唱方法的完全性。比如几年前有央视宣布过的“天梯上学”新闻,就发生在笔者的家乡龙潭坪镇苦竹坪乡的张家湾村落,这也从侧面反响了笔者家乡历来的相对封闭。笔者家公的肖氏家族具有很好的读书传统,目前在龙潭坪镇红军村落的茶园和李家湾村落的沿场,仍住着肖氏家族的后人。这只肖氏家族在当地培养出了不少学堂师长西席、公民西席和一些读书人,尤其是红军村落的茶园,更是走出了不少读书人。
图为龙潭坪镇张家湾村落“天梯上学”宣布的新闻图片,该座山脉的另一边便是笔者的老家“红军村落”
其余,在红军村落有一处洞穴,名叫肖洞(由于贺龙曾带领红军在此洞藏身,现今也叫“红军洞”,但当地人仍旧习气叫“肖洞”),很多人只知张家界有黄龙洞、九天洞,却不知肖洞可能才是张家界最大的地下溶洞,而这个叫“肖洞”洞穴的存在,可能与肖氏家族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现今已不可考。正是由于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性,使得笔者的家乡一贯很少与外界有互换,即便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改变这里的古朴文化和习俗,尤其是儒祖传统,在这里相对保留得比较无缺。这也是这种古诗歌诵唱法能够得以留存的紧张缘故原由。
图为位于红军村落茅扶组的肖洞,比拟站在洞口的人便可知肖洞可能是张家界最大的洞穴
笔者有诗云,《七律·红军村落》:
茅扶天园听传说,一山巍巍一山峨。
大马可骑三步涉,山口而喘土皮坡。
壮士曾纵千古义,红歌今飘两叉河。
关门岩挡鬼神路,常使英雄怯半坡。
诗中的茅扶、天园、两叉河、关门岩、半坡均为红军真实地名(个中,关门岩是贺龙之女贺捷生的出身地)。诗歌描述的场景,也印证了这一带山区的封闭性。
肖洞之美宛若“地下皇宫”,作为当地人,我反而不肯望它像黄龙洞、九天洞一样被开拓,保留点原始气息吧
我用这么多笔墨先容武陵山区腹地的山歌文化和诗歌文化,与因我所写《诗载论》一文的缘故分不开。我认为,这些古老的山歌和诗歌,承载着最古朴、最纯洁、最俏丽的中华文化,这也是山区劳动人民不怕捐躯、勤恳年夜胆的源动力所在。本日,我把这种古诗歌诵唱法分享出来,也正是想借最原始之美的山歌和诗歌传播中华文化,而笔者作为这种古诗歌诵唱法的唯一继续者,更是责无旁贷。
二、神秘"古诵唱法"的详细先容:古诗歌的原始灵魂,方言诵唱更有感古诗歌唱诵法的要诀:(1)用方言唱更有觉得,无法阐明,笔者也试着用普通话唱过,但唱着唱着又回到了方言(也有可能是笔者普通话没学好);(2)结合诗歌原有的韵律、节奏,加入适当的拖音、变音,一样平常以“呃~”结束上一句,以“哦~哦”结束下一句;(3)诗歌唱诵的腔调非常像湖南桑植和湖北恩施一带的山歌民调,但又有明显的不同,笔者对音乐知识的理解有限,无法阐明;(4)不分三言、四言、五言和七言,都可以用这种古诗歌唱诵法;(5)“古诵唱法”以诗经、楚辞、唐诗为最佳,宋词元曲也能采取该种诵唱法,但诵唱时的意蕴和觉得,比较诗经、楚辞、唐诗要少很多(由此也可以推断,这种诵唱法很可能涌如今汉唐以前的春秋战国期间,乃至更早)。
用古诵唱法唱诗经,方知诗经意境之美
现将不同类型古诗歌的唱法分享如下:
1、三言诗诵唱法(以《三字经》为例)
人之初(呃~),性本善(哦~哦),
性附近(呃~),习相远(哦~哦)。
苟不教(呃~),性乃迁(哦~哦)。
教之道(呃~),贵以专(哦~哦)。
2、四言诗诵唱法(以《关雎》为例)
关关雎鸠(呃~),在河之洲(哦~哦)。
窈窕淑女(呃~),君子好逑(哦~哦)。
参差荇菜(呃~),旁边流之(哦~哦)。
窈窕淑女(呃~),寤寐求之(哦~哦)。
3、五言诗诵唱法(以悯农为例)
锄禾(~)日当午(呃~),
汗滴(~)禾下土(哦~哦)。
谁知(~)盘中餐(呃~),
粒粒(~)皆辛劳(哦~哦)。
4、七言诗诵唱法(以李白诗为例)
日照喷鼻香炉(~)生紫烟(呃~),
遥看瀑布(~)挂前川(哦~哦)。
飞流直下(~)三千尺(呃~),
疑是银河(~)落九天(哦~哦)。
(七言诗中间有拖音,稍不同)
5、楚辞诵唱法(以《湘夫人》为例)
帝子降兮北渚(呃~),
目眇眇兮愁予(哦~哦)。
袅袅兮秋风(呃~),
洞庭波兮木叶下(哦~哦)。
登白薠兮骋望(呃~),
与佳期兮夕张(哦~哦)。
鸟何萃兮苹中(呃~),
罾作甚兮木上(哦~哦)?
沅有芷兮澧有兰(呃~),
思公子兮未敢言(哦~哦)。
荒忽兮了望(呃~),
不雅观流水兮潺湲(哦~哦)。
6、词曲诵唱法(综合上述唱诵法)
宋词元曲,此处纷歧一举例。
7、骈文诵唱/诵读法(综合上述唱诵法)
骈文可以诵唱,也可以诵读,用方言诵读时,跟不通话诵读的觉得和意境也不一样。篇幅有限,此处就不举例了。
8、古文诵读法(综合上述唱诵法)
笔者家公读古文跟普通话读古文略有不同,有些断句的地方会有很长的拖音。哼读和诵读又有差异,哼读贵在自然,饶有意见意义;而诵读则声音洪亮,情绪丰富,拖音悠长,非常动听。家公曾多次取笑子弟们读书“干巴巴的”,一点韵味都没有。
图为张家界武陵山区腹地的标志性吊脚楼
以上便是诗歌“古诵唱法”的基本先容。闭上眼睛,便可想象出古代学堂师长西席上课时的场景,彷佛也能够感想熏染到那种诵唱诗歌的悠然自得,古朴山村落的诗书氛围,乃至古学堂师长西席与学生的神色。当然,有兴趣的古诗歌爱好者,不妨根据我的先容考试测验着诵唱一下试试,必能觉得到不一样的气息和韵味。
三、"古诵唱法"的代价:诗中悟道,传承原汁原味的古诗歌和道学思维我相信很多人都熟习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古诗歌爱好者要真正进入《二十四诗品》所表达的诗歌境界,是必须要理解这种“古诵唱法”的,否则,是很难真正进入到司空图所描述的那种诗歌意境中去的。道理很大略,古诗歌如果用现今的普通话去诵读,就好比用普通话诵读喷鼻香港著名歌手刘德华的盛行歌曲,比如这句“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如果不用唱的形式,而只是用标准普通话去诵读的话,刘德华《忘情水》中的这句歌词就立马变成一句“大口语”了。
用普通话诵读《忘情水》只会变成“大口语”
1.“古诵唱法”对诗歌艺术本身的代价
诗歌的传统诵读办法,是很常见的,也不分方言和普通话。但要真正进入到诗歌的灵魂与生命中去,那就必须理解这种“古诵唱法”。在家公传承下来的“古诵唱法”根本上,再结合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我对古诗歌总结出了八个字,即“情、境、意、韵、景、物、心、志”这八个维度,这也是笔者曾经在《诗载论》中表达过的不雅观点。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这种“古诵唱法”的熟习和理解,我是很难在《二十四诗品》的根本上提炼出这八个字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懂“古诵唱法”,基本上是读不懂《二十四诗品》的。
图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比如《二十四诗品》讲的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冲淡:素处以默,妙机其微;纤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沉着:所思不远,若为平生;高古:畸人乘真,手把芙蓉;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洗炼:如矿出金,如铅出银;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绮丽:金尊酒满,伴客弹琴;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如果仅仅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二十四诗品》的话,那么,你是很难明得道诗歌艺术蕴藏的真正灵魂和生命的。但如果你能够用“古诵唱法”去唱诗歌,那么,诗歌的“情、境、意、韵、景、物、心、志”便立时呈现于面前,涤荡于心间,这便是诗歌“古诵唱法”的玄妙之处。
每天感知并领悟诗歌的雄浑冲淡,或纤秾沉着,或高古典雅,或洗炼劲健,或绮丽自然,一定能够体会到诗歌艺术中的“俱道适往”,以及“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的心境。这大概便是笔者家公几十年如一日,直到90多岁逝世,“嘞呃复哦哦,晚五重朝九”,每天都沉浸于诗歌诵唱之乐的缘故吧。
图为《二十四诗品》网友书法作品(仅供参考)
2.“古诵唱法”背后暗藏的道学思维
笔者是诗歌爱好者,也从诗歌中领悟到了中华道学思维的玄妙。笔者对西方哲学和中华道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大学期间写过一篇《中西神学比较》的论文。“中学为变,西学为辩,变者道也,辩者哲也,道中有哲,哲中无道”,这是我对中华道学思想的不雅观点。其余,笔者也曾在《诗载论》一文中强调过中华道学思维。我提出道学“诗载论”,其一是我自己爱好诗歌,确实钻进去过,并研习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其二便是家公流传下来的诗歌“古诵唱法”在实际生活中给我的启迪。
首先,看看《二十四诗品》,司空图品的是诗,讲的实在是道。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是哲学,这点我是切切不敢认同的。我一贯主见道学是道学,哲学是哲学,强行把中华道学定义为“中国哲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沽名钓誉干的一件屈曲的事,而且误导了太多人。道学是不雅观变的,哲学是思辩的,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再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表示的实在正是“情、境、意、韵、景、物、心、志”千变万化,与思辩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负责读过《二十四诗品》,我创造司空图竟然有多达八次提到“道”。
(1)自然:俱道适往,着手成春;
(2)豪放:由道反气,处得以狂;
(3)委曲:道不自器,与之圆方;
(4)实境:忽逢幽人,如见道心;
(5)悲慨:大道日丧,若为雄才;
(6)形容: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7)超诣:少有道契,终与俗违;
(8)流动:夫岂可道,假体如愚。
其次,分享一下家公对笔者的道学启迪,家公肖大明先生长西席是懂道学的。我出生时,家公已不是学堂老师了,但“肖先生长西席”的名号,在十里八村落还是很响亮的。在我还是婴儿时,外公就常常在火坑旁翻古,我也因此习气了高频率地听到“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老子”、“孔子”等字眼,加上家公几十年如一日地诵唱诗歌,从小就在我的灵魂深处种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我说家公懂道学,其一是生活道学,其二是育人性学。
腹有诗书气自华,家公对名利看得非常淡泊,唯独对诵读诗歌情有独钟。我听母亲讲,家公曾有机会为官,并且乡亲们推举的,但家公却选择可在家种地,安度余生,平时也就常常帮乡邻写写对联什么的。我在《忆家公四首》中也描述过这个场景,有诗云:“踩霜石上走,踏月邻里求。督管八乡事,联对十堂秋。良言金玉贺,仁德清世留。落豪羲之字,只换一钱酒。”宁要“仁德清世留”的逍遥清闲,也不要官场的名利功绩,这便是笔者的家公。而实际上,或许正是由于家公的这一选择,在生活条件相对掉队的穷苦山区,他活到了93岁的高龄。
在说说家公的育人之道。说实话,在我影象里,家公从来不劝学,虽然《三字经》他背得滚瓜烂熟。家公比较看重不雅观察小孩子的天性和灵性,他坚持“爱读书的不用劝”。家公的实际行为也是如此,我不仅从来没有听到过家公劝学,他乃至连批评我一次都没有,当然,也有可能是笔者从小就很听话,哈哈。但说实话,家公实在一贯都在言传身教,他更看重给子弟树立榜样。比如,为了启示子弟诗歌的兴趣,他曾经多次讲起他年轻时用一首《屁之歌》捉弄学堂师长西席的故事。
这首《屁之歌》是这样唱的:“屁呃屁呃,肚里的气呃,有屁不放,作鼓作胀呃;屁呃屁呃,肚里的气呃,有屁一放,臭气满堂呃”。《屁之歌》的唱法与古诗歌的诵唱法稍稍不同,更像是羽士师长西席在已故亡人灵前唱的悼词。唱亡灵悼词时是不用吐字清晰的,只须要半哼半唱即可,以是用来捉弄学堂师长西席“挺得当”。这首《屁之歌》也是家公常常拿来逗小孩的歌。
回顾家公以前的点点滴滴,我在《忆家公四首》中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小伢跟前逗,故事烟斗收。躬勾说往古,围坐话商周。三劝人醒明,半哄儿睡熟。柴门访雪冷,让客火坑头”。个中,“柴门访雪冷,让客火坑头”描写的是冬天下大雪,家里来客人了,小孩子要“让客”的故事。
在这里,笔者多分享了一些家公的往事,但正是这些看起来很平凡的往事,却从侧面反响了家公的诗歌行为,也验证了诗歌“古诵唱法”确实是可以培养一个人的“道心”的。
末了,既然这篇文章是聊诗歌,就以诗歌来结束这篇文章吧不知不觉前面已经分享了三首《忆家公》的诗,索性把末了一首也分享出来吧。笔者忆家公诗云:
阶檐翻书旧,灶膛弃卷丢。
明镜儒中理,恳切世上修。
光亮磊落道,光明正大走。
奈何此生命,不活九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