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他是天下户外运动的先驱;他是最调兵遣将最资深的“驴友”,他是中国第一个登山鞋品牌——“谢公屐”的发明者。
他是名门之后,才高八斗,他本来该当有一个锦绣的出路。但是上天给他的一手好牌,他根本不睬解珍惜,而是将它恣情任性地打烂,终极落得一个被诛杀的了局。
但是,他没有什么好同情的,由于没有人刻意要杀他,他也没有什么悲壮的要赴去世的情由,他是实在活得不耐烦,于是一步步自己作去世了。
他,便是南北朝文学家、墨客谢灵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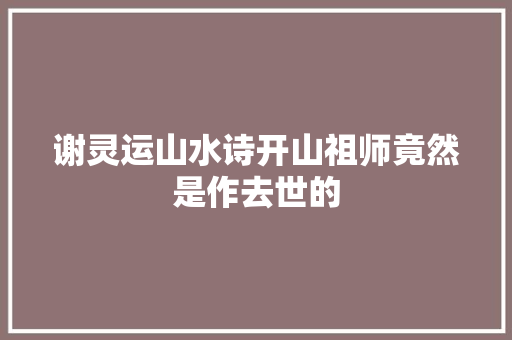
上天对谢灵运是极其偏爱的。由于他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降生在一个世家大族,是东晋名将谢安谢玄之后。
谢安和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谢家因此收成了巨大的政治光彩,成为无比清贵的豪门,和当时琅琊王氏并称“王谢”。
谢家不但有显赫的战功可以自傲,而且文人辈出。
谢灵运的族姑谢道韫是东晋著名的女墨客,有咏絮才女之称,她对谢灵运教导有方,是谢灵运在文学上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谢灵运的从叔谢混,被时人誉为“风华为江左第一”,是中国山水诗文学的先驱人物之一。在谢混的谆谆教诲之下,谢灵运在山水诗的写作方面表示出了很高的才情。
谢灵运的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南朝梁时虞和的《论书表》中记载:“谢灵运母刘氏,子敬(王献之)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氏。”
在家人的精心教导之下,谢灵运聪慧非常,诗书俱佳,少年时文章已名冠江东。
公元403年,谢灵运继续了祖父谢玄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食二千户。
崇高的出身,既给了谢灵运超乎凡人的自傲,也让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许。他具有强烈的功名意识,视报效国家、规复家族的昔日辉煌为己任。
2、嬉戏为主之仕途按理说,有先辈搭建的官场平台,谢灵运的仕途该当会平顺一些。
但是,天下上从来没有什么理所应该的事情。
谢灵运出仕之初,适逢晋宋易代之际,最高统治阶层之间,不断地上演誓不两立的权利之争。
作为臣子,一旦站错队,就会受到连累。轻者被贬官,重者会和主子一起丢了性命。
谢灵运,也常常面临着这种困难的选择。
在刘毅和刘裕的皇位之争中,刘毅兵败自尽,谢灵运转而投靠了登上皇位的刘裕。
没想到,刘裕对他还不错,他在短短的五年之内连升了五级。
但是他和刘裕的次子刘义真走的太近,在另一波宫廷政变中,刘义真被杀害,作为翅膀的谢灵运也遭到了贬谪,成为永嘉太守。
之前,朝廷将谢灵运的公爵降为侯爵,从食二千户降为食五百户,两件事加起来,使谢灵运的心里极其愤懑。
以是,到了永嘉,谢灵运根本无心政事,他干脆带着一帮随从游山玩水去了。
史籍这样记载:“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竟然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诉讼,不复关怀。”
谢灵运完备将公事抛诸脑后,醉心游历。
每天他还把他们走过的景点,让随从拍很多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他的同事们纷纭点赞,但也在心里愤愤不平:天下那么大,凭什么你旷工去看?
逐渐地,他觉得到了大家对他的不满,反正他本来就不奇异太守这个职位,他索性辞职回老宅始宁墅消闲去了。
临走时,大家都说,看看,还是人家官二代洒脱。
公元426年,应宋文帝的约请,谢灵运重回康健,再度出山。
谢灵运本以为宋文帝要向他请托什么重任,没想到让他回来,不过是修撰《晋史》。
谢灵运自觉有经天纬地之才,修史对他来说太没意思了。于是他又开始悲观怠工。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他“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天子交代的事,公然不做;给天子打工,想去玩就去玩,连呼唤都不打一个,并且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啧啧,这豪情,这胆量,恐怕也就只有谢灵运了。
大家都说谢灵运太自高自大、太不遵守劳动纪律,天子还每天坚持坐班,时时地中心公众年夜众号上发个政府动态,你一个修史小官,竟然常常给老板玩失落踪?
他的同寅们排成队,来到宋文帝的办公室,强烈哀求把谢灵运这样散漫的公务员从干部队伍中清退。
谢灵运只好第二次回到始宁墅。
3、狂妄之极吞国产
始宁墅占地面积三十多平方公里,湖光山色,秀美无比。它的规模,它的豪华,“连古罗马帝国的大栽种园相形之下也望尘莫及”。
始宁墅是谢家赫赫功业的象征,是谢灵运内心自满感的来源,也是他走投无路时的归宿。
谢灵运来到始宁墅,并不闲着,他常常带着一大帮家仆,连续浩浩荡荡地出行。
他的出行,不是随随便便地看看山,玩玩水,而是非常专业的户外运动。
为了开辟新的旅游线路,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其声势之大,有一次竟被当地人误认为来了山贼。
较之玩水,谢灵运更喜好爬山。他非常富有寻衅精神,哪里的山最高、最峭,他专门爬哪一座山。
为此,谢灵运还专门发明了一种登山鞋——谢公屐。这个“谢公屐”上山的时候,把前齿去掉,下山的时候,把后齿去掉,方便之极,用了的人都说好。
李白就很喜好谢灵运发明的这个登山神器,他大赞到: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如果谢灵运只是纵情山水,虽然存在着轻度扰民,但不一定招致去世罪,令人神共愤的是,他竟然狂妄之极,想侵吞国家财产。
始宁墅的阁下有一个大湖,谢灵运一贯想将它据为己有,围湖造田。当地太守孟主座武断不同意,但谢灵运就想讹诈打单,一来二去,他和孟太守邋遢已深。
为了保住国家的资源,孟主座不得不修书一封,向宋文帝禀告谢灵运有谋反之象。文帝不相信一个文人有此大胆,为了不让他再招惹祸事,宋文帝让谢灵运去做临川内史。
任临川内史时,谢灵运还是不安分,天马行空,故态复萌。
有人又告他的状,司徒刘义恭派人赴临川去搜捕谢灵运归案,谢灵运反而扣留了青鸟使。
有人向宋文帝进言:“乱臣贼子谢灵运写了一首反诗”。
宋文帝说:“给我看看”。
他看到:
韩之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水,忠义感君子。
宋文帝依然不相信这是谢灵运写的。
但是别人相信。他们忍他已经良久了
终于,公元433年,谢灵运在广州被诛杀。
4、恣情任性终作去世
关于谢灵运的生平,我想了很永劫光,也没有创造他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他的性情特色倒是很光鲜:自视过高,狂妄至极,任性而为,目无法纪。
在他的理念中,彷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他。皇权,岗位,国家制度等等,这些没一样对他是有效力的。
在别人都在忙着事情的时候,只有他真正实现了个人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他从不考虑自己做任何一件事的后果,或者他考虑过了,认为不管他做什么,怎么做,都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比如他想占湖造田。
他之以是这样做,是由于他太狂妄太自大了。
他以为他是谢灵运,谢玄的孙子,自然可以在这个天下任意驰骋,谁还敢整顿他?!
他的心里一贯有一个声音在说:没有我的爷爷,就没有淝水之战东晋的胜利,你们这帮龟孙子说不定早就成炮灰了。
本日你们得势了,就来给我横,你们配吗?
但是,新的统治阶级不这样想。
他们大多出身于寒门,对自身身份的自卑,以及出于对皇权的保护,他们费尽心机抑制和打击士族势力。
谢灵运这样的家族,实在便是他们打击的紧张工具。
对这一点,谢家的谢瞻、谢弘微等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以是他们平日里为人处世,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唯恐招来杀身之祸。
唯独谢灵运,没有这种危急感。
时期早已变了,他还一厢宁愿地沉浸在家族昔日的辉煌之中,不睬解及时地进行身份转换,反而凡事往过火里做,直至当朝统治者无法容忍。
他的危急感的缺失落,正好解释了他的情商低下,对时势的觉得迟缓。
都说“识时务者为英雄”,一个连时期的主流力量都看不清的人,何以成为英雄,何以报效国家?
吃米不知米价,还想有所作为,这或许是发生在谢灵运身上最大的笑话。
以是,在一种盲目的自傲中,谢灵运一起高歌年夜进,为所欲为,他还将自己的这种行为艺术标榜为“个性”。
等待他的,就只有屠戮。
罗素说:“过分的自傲很随意马虎使人产生毁灭性的傲慢”,这可能是对谢灵运命运的最好表明。
5、山水诗歌之鼻祖
只管谢灵运的个性不为众人喜好,但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却具有无与伦比的才华。
他是中国第一个以写山水诗著名的墨客,并使山水诗从此成为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自己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山水诗鼻祖”。
山水是谢灵运创作的永恒的主题,也是他生命中的主旋律。
在谢灵运之前,山水诗因此写意为主,描写物象只是从属地位,所谓情为主,景为客。
直到谢灵运涌现,山水诗的写法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在诗中风雅地捕捉山水景物的造化之境,让山姿水态真正地站起来,活起来。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谢灵运“极貌以写物”。鲍照也曾评价:“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清新可爱”。而毛泽东称谢诗“一物化然”、“匠心独到”、“在新在俊”。
的确,当人们读厌了那些“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溘然打仗到谢灵运的典丽新声,怎么能不线人一新?
被贬永嘉、两番归隐和外放临川的前后十年,是谢灵运诗歌创作的黄金期间。
在这一期间,谢灵运以忧愤之情合山水之音,用文学的琴键弹奏清丽的山水旋律,写下了数十首山水诗的名篇。
在这些名篇中,不得不提的是《登池上楼》。
《登池上楼》做于谢灵运担当永嘉太守期间。诗中抒发了作者怫郁苦闷的心情,既有孤芳自赏的清高,也有政治失落意的牢骚,还有归隐山水的志趣。
《登池上楼》一诗最大的代价,是它为人们贡献了一个随处颂扬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此句一出,众人狂热追捧,叹服不已。
元好问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朱熹曰:“共说仙翁闲日月,不因春草梦池塘”。
王安石曰:“春草已生无好句,阿连空复梦中来”。
谢灵运也深知自己具有盖世才华,以是他底气十足地说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
听听,这是什么样的气概!
带着他的一斗之才,带着他的狂放不羁,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就这样逐步地,逐步地,隐没在了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