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荣
在毛泽东生平中,喜雪,爱雪,喜得痴迷,爱得亲切。下雪的时候,他总是以为很愉快,有时乃至到了忘情的地步。据毛泽东身边事情职员回顾,走在雪中的毛泽东童心未泯,他专爱走有雪的地方,专爱用脚去踩雪,厚厚的积雪淹没了他的双脚,乃至灌到了他穿的布鞋里也全然不顾,完备自我陶醉在一片银白色的天下中。
雪授予了墨客伟大的灵魂,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肚量胸襟。雪的意象也常常涌如今毛泽东的诗词中,以寄托他对雪的不屈常的情绪。让我们走进毛泽东的诗词中,感想熏染那不朽的咏雪篇章。
毛泽东曾自满地称自己是“马背墨客”,他曾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韶光,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虑。”的确,在残酷的革命战役年代,他的诗词常常是骑马或坐担架于行军路上所作,成为了他领导革命战役的真实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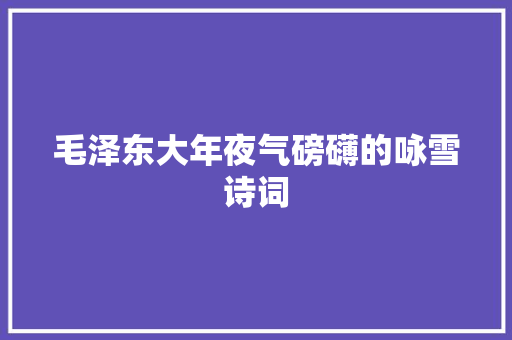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这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是1930年2月毛泽东在由闽入赣,由进攻吉安转为进攻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的行军途中所作。这是生平钟情于雪的毛泽东第一次用诗笔写下的雪景,写下的与猎猎红旗交相照映的雪景,仿佛是一幅壮美的雪里行军图。
“漫天皆白”,起句脱口而出,自然流畅。“漫”天——寥廓天空,急风卷雪,飞雪舞风;“皆”白——茫茫大地,山川原野,素裹银装。这氤氲万状的雪,就为词人所歌咏的主体——挺进于风雪征程的工农红军渲染出既紧张庄严又充满活气希望的氛围。红军战士以挟风雪之势席卷江西去欢迎革命高潮的急迫心情,与面前翻舞的雪花、皑皑大地之景物十全十美,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领悟,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不雅观主义的光辉。虽然身临的是“漫天皆白”,将去处也是“风雪迷漫”,但在作者笔下却看不到一丝寒冷、凄苦和畏惧,只感到兴旺的斗志、火样的激情亲切、倔强的力量和胜利的信心。
正像长征属于中华民族的传奇一样,长征诗词也是属于毛泽东的传奇。长征之苦,最苦在爬雪山过草地。岷山,在四川、甘肃交界处,山顶终年积雪,称为大雪山,是长征最困难的路段。可涌如今毛泽东《七律·长征》诗中,却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巨山大川之后涌现的冰清玉洁天下,让墨客感到“更喜”,集中显示出墨客对冰雪热爱的审美意见意义。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手迹。
昆仑山的南支向东延伸后与岷山相接,因而红军长征时所经由的岷山,也可以看作昆仑山的一个支脉。伫立岷山之巅,感想熏染横空出世、雪峰如海的昆仑,毛泽东体会到人类的过去,畅想着天下的未来,构思出一首大气磅礴的《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这首词题目虽未标明写雪,实际上从头至尾都在写雪,刻画雪的形象,反响雪的意境。披挂在昆仑山身上的冰雪,一冷一热地更替,凝聚了人类文明的万世沧桑,它孕育了多少彩色生命,又荡涤了多少万物生灵。“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以气吞六合的气概、声震天地的威势直接与昆仑山对话:要改造你这高寒多雪的旧貌;要倚天抽剑,按人类的意志和历史的须要把你剪裁开来,分给天下各国,使人类寒暑相同,凉热均等,人类共享幸福太平。
作为墨客,毛泽东由这首词走向纵论天下的诗坛;作为政治家,毛泽东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从延安走向天下舞台。
1936年2月,中心红军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两个月后,一场纷纭扬扬的大雪把陕北秦晋高原装点成银装素裹的洁白天下,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看着这统统,一种神圣的义务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他一气吟哦成了后被柳亚子师长西席定评为“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毛泽东《沁园春·雪》手迹。
只管毛泽东钟情于雪,咏雪的诗句多而精彩,然而以“雪”冠题的词却只有《沁园春·雪》这一首,又取雪为物象,旨在作为情思的抒怀载体。词中所咏之雪,可不是一样平常的雪,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雪;是结束了空前壮举的长征,持续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几次“进剿”,正欲挥师东征抗日之际,在中国北方秦晋高原所见所感的雪;是墨客融入自己的情怀、抱负、空想、愿景的雪。正是气势威猛的雪装扮了祖国壮阔俏丽的河山,而这又激发起墨客评说历史英雄、指示江山的豪情壮志。由雪到江山,再到英雄,诗词英气纵横,荡民气怀。
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会谈时,将《沁园春·雪》这首词赠给柳亚子师长西席。1945年11月14日在《新民报晚刊》首次公开拓表,轰动山城,影响遍及全国。众人从而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卓越的文学家和才华横溢的墨客。然而,蒋介石却从这首词中读出了毛泽东的“狂妄”和“野心”,他责令御用文人对抗毛词,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坛大战,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奇不雅观。
毛泽东闭幕了一个时期的噩梦,用他的诗篇为创建新中国的长卷写下了有力的结尾。一个外国人在读过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诗篇之后,由衷地夸奖道:“一个墨客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1953年冬毛泽东在杭州。
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是毛泽东外出察看到的最多的地方之一,他称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1953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时,这里竟飘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景象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墨客毛泽东又想起了雪,也想起了雪中的梅花,并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期精神,为梅花创造了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峭壁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手迹。
这首《卜算子·咏梅》词,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雪,本是寒冷的象征。但在墨客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风雨也罢,飞雪也罢,都挡不住“春天”的来临,它暗示的正是革命胜利的前景,洋溢着革命的乐不雅观主义精神。
1962年,春天如约来临,在飞雪中来临。梅花与雪的故事还在连续。是年冬天,12月26日毛泽东迎来了69岁生日,他并未追忆自己的昔日峥嵘,而是又作《七律·冬云》诗以言志:“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占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畅漫天雪,冻去世苍蝇未足奇。”
这首《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整首诗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充分显示了墨客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公民的领袖立足涛头、砥柱中流、不畏霸道、力挽狂澜的决心和勇气,以充满战斗激情、雄奇苍劲而又闪耀着深刻哲理的诗篇,为我们奏响了一曲高亢的时期乐章。
在毛泽东笔下,雪既是一种自然征象,也是一种困难的象征,更是一种信心和胜利的象征。毛泽东对雪的反复吟咏,从一个侧面反响了他的精神天下。在其生平中,他对人、对己都追求高度的纯洁性。他哀求人们做一个“纯粹的人”,哀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辅导思想都保持高度的纯洁性。这些,都表现了他个人的襟抱和卓识,成为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转载请联系《党史博采》
侵权必究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年夜众号:dangshibo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