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办法,逐句剖析为人熟知的《将进酒》,从浅层的释义开始,阐明诗句表达的“意思”和“道理”,进而深入感知李白诗句中鲜活多变的语气语调,以及蕴含个中的墨客跌宕起伏的生命情绪,由此,一个正在和好友饮酒、穿梭于放荡欢畅和巨大忧闷之间的李白之形象,涌如今我们面前。终极,本文通过对《将进酒》的细腻剖析,让我们明白,只管这首诗的“内容”是悲观的,李白却用高亢昂扬的姿态面对人之必去世这一“万古愁”,他用强烈的生命激情宣誓着“存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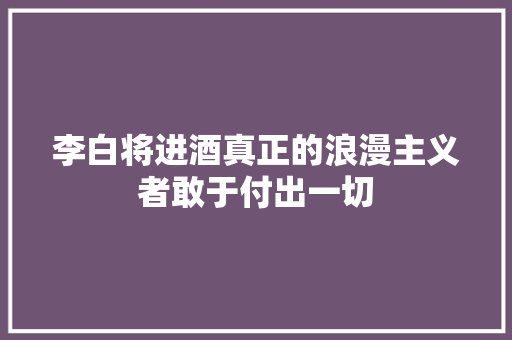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役夫,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敷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当年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作甚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劝酒歌:为什么“该当”饮酒?
《将进酒》是一首劝酒歌。将进酒的“将”(qiang,平声),“请”的意思,将进酒便是请饮酒。饮酒是最常见的情景,聚餐助兴,独酌消愁,古今一样。饮酒最能调动人的感情和情绪,是人情绪愉快度最高的时候,也最易触发诗情。古代中国有很多饮酒诗、劝酒诗,个中李白最有名,“李白斗酒诗百篇”,写了很多。我们来看李白的这首劝酒歌,讲饮酒的道理,为什么“要”饮酒,“该”饮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第一句显得突兀。上来就呼唤,“君不见”,意为“你难道没瞥见吗?”,即“请看,请把稳”的意思。提请把稳什么呢?“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黄河从高入天空的青藏高原奔流而下,过黄土高原,东流入海,单向流动。这是客不雅观的事实描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看到了,但这和饮酒有什么关系?意图目前还无法确定。
第二句:“君不见”,同样的提示,请看,“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同样的句式,同样的语气。这一句意思清楚明白,在一壁大镜子前看着自己的白发形象,创造人的生平太短匆匆,朝暮之间就从年轻成了年迈,黑发成了白发。知晓第二句的意思后,黄河奔流一句也就清楚,李白并不但是让你看黄河奔流的事实,它还是个比喻,也是在讲韶光的流逝,一去不返,个中有生命流逝的悲哀。第三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意为:光阴仓皇,生命短暂,愉快的时候难得,快乐时让我们尽情饮酒欢快吧。如此一来,前两句加后一句,三句诗的重心落到了题目所示的“将进酒”,构成一个完全的劝酒过程,逻辑清晰,意思完全。
南宋 梁楷《李白行吟图》
我们由此看到,诗歌中措辞的意思并非由单独词句完成,而是一句一句构造起来、语句之间相互投射,然后形成完全的意思。读诗时,我们先把稳到一个句子单独的意思,而后才明白它在整首诗中的意思。我们读完第二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一句把韶光压缩,效果强烈,有戏剧性),明白这句是写韶光流逝、生命短暂的,而后才意识到,前一句写“黄河奔流不复回”写的也是韶光一去不复返,生命的流逝无可挽回。若没有第二句,我们是无法确定第一句诗的意味的。我们要读完第三句,才明白写第一、二句的情由和根据。因此,理解诗句,不仅要理解其单句,还要在意群中、在整首诗的意义和逻辑关系中更准确地理解。这是“意思”上的理解。
《将进酒》艺术魅力的秘密
上述三句诗的意思很大略,讲的是饮酒的情由。实在什么道理讲起来都是大略的,纯挚、明确,在这里即是生命短暂,应抓紧韶光饮酒享乐。而诗的力量绝不仅仅在于意思和道理,一些诗的意思(思想内容)概括起来非常大略,关键在措辞,诗歌的神秘力量来自其措辞的惊人效果。诗不仅仅是意思的表达,更主要的是表达意思的办法和效果,这是诗作为一种措辞艺术的核心所在,也是李白这首《将进酒》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的秘密之所在。
比如起始两句,表达的是“我们一次性的单向奔流的生命太短暂了”,却用了气势惊人、一泻而下的排比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句表达同样的意思,却用如此繁复壮不雅观、充满戏剧性的语句,有着震荡民气的效果。
在这两句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有着空间上的阔大,把一个巨大空间中间隔迢遥的事物——黄河所来的天上的高原,和黄河所去的东方的大海——放在一个画面中,两者同时为我们所见。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现实的视点上,我们不太可能同时看到黄河从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经晋陕大峡谷,再奔驰流入大海这一实景。李白当时可能站在黄河中下贱一带,两者都看不见,因此这是一种想象,而李白的想象如此准确。把天海之间发生的事放在我们面前,呈现在我们的视觉之内,这是诗的措辞所授予的惊人景象。第二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谈的是韶光。正如第一句诗把辽阔的空间放入一幅画,第二句则把韶光的速率放快,生平被压缩成一天,这使人生的韶光有了强烈戏剧性。是日然可以被视为夸年夜,但这种冲击力正是诗歌艺术的效力。
清 苏六朋《太白醉酒图》
这三句诗是在讲道理,但诗歌的艺术在于让这道理为读者直接体验到,让你目睹,让你置身个中地感想熏染到,而不仅是让你理解一种抽象的说理。这种详细性、直接性、直觉性的措辞给人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赛过抽象的道理,更让人信服。《将进酒》进入的办法非常直接,让我们直接感触到情绪、意象、场景,把我们直接导入惊人的意境中,充满气势的黄河之水、悲剧性的一日之间生白发,让我们全体身心感知到直接的冲击,然后才一点一点明白它的道理。由此,这道理是浸透了人的强烈情绪和人生体验的。《将进酒》起句突兀,感情高昂,劈空而来;第二句连绵而至,措辞紧张强烈,气势撼人。这两句描述了一种事实,而这描述蕴含着强烈的情绪和深奥深厚的生理能量。构成前三行诗的,一是年夜声大呼的语气,二是气势磅礴的景象,三是两个排比句式,四是诗句意思的悬疑和连绵。
“君不见”是呼唤语,直接对你说话。在古诗中,这种直接诉诸读者把稳力、和读者说话的,少有。这首诗特殊的语气还表示在后面,“岑役夫,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墨客对劝酒的工具直接说话。李白善于用先声夺人的办法,平地一声惊雷炸响,而不是逐渐展开、交代、进入。李白诗中这种调子高昂悲壮的起句例子很多,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以气势撼人,如一阵大风,将读者席卷而去。这是一种高歌激越,倾注了墨客全部的情绪与力量。
前两句写了生命短暂、光阴急迫这一事实和道理,高昂的调子趁势而下,顺理成章地得出要捉住韶光、纵情生活,让有限的生命尽情绽放,享受人生:“人生得意须尽欢”。人生本来短暂,而得意之时在人生中更是稀少难得,以是要捉住,必“须尽欢”。怎么尽欢?便是饮酒,尽情地喝。“莫使金樽空对月”,樽是羽觞,金樽,黄金打制的很贵重的羽觞。空对月,在月光下空着。在月光下是美好的光阴,也即前一句所说人生得意之时。“得意”在此不是“得志便专横狂”的那种得志,而是月光下、东风里,朋友相聚,这样自由写意的美好时候。
对现世代价和历史代价的寻衅
第一轮劝酒完成。接下去是: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句同样有些突兀,是新一层意思。怎么一下子说到自己?实在这句的重点是钱的问题,要办理饮酒享受所用的钱。前面所写都是议论和思考:人生短匆匆,尽情饮酒享受吧。但这只是理论上得出来,还没实际去喝,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才进入吃肉饮酒的行动。最自然的逻辑是:“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先顺承前句理论上的饮酒,再详细喝起来,然后办理饮酒要担心的钱的问题。这里,先办理饮酒的钱的问题,然后再进入饮酒,逻辑上有一种跳跃,但效果是,关于钱的考虑被夹在热气腾腾的饮酒的两句之间,诗歌效果非常好。
其余一点是,这诗氛围热烈,这个跳跃也完备可以消纳,并且更增长了这种热烈氛围:墨客彷佛口不择言,任性而出。更特殊的一点是,就整首诗的逻辑来说,这一联的重点是钱,但就这两句诗本身来说,重点却在“我”,“我”的自傲:“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一意外效果,更增长了一种因自傲而来的热烈。什么都不如充满自傲、对自己未来充满信心更能助长人的快乐,让人全身心投入欢快,发自内心地感想熏染欢快。前面五个联句的全体逻辑如下:人生事实和道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态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办理行动顾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和人生行动(“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役夫,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这是一个插入句,用了散句,歌中的道白一样,中断了前面的诗语之流,起到转调的浸染。由于前面太高昂,太激烈,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开始,一贯在最高音萦绕,标志是前面五个联句,十个单句,每一句都是非常响亮的警言名句,一贯处于高峰之上,句子之间密欠亨风,每个句子都情绪饱满、感情紧张。诗当然不能一贯勾留在高音区,就像音乐一样,须要起伏。读者的感情也一样,不能一贯处于紧张状态。因此这里放低下来,涌现了调节。首先是节奏变了,变成连续的三言、五言、七言、杂言的散文节奏,语气上很亲切,直呼一起饮酒的朋友名字,“岑役夫,丹丘生”,内容很详细,很生活化;“将进酒,杯莫停”,喝起来了,我给你们唱首歌吧,你们听听。接着劝酒,助兴。这里的描写非常生动夷易,现场感十足。此处涌现了歌本身,“与君歌一曲”,自然转入一下段“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敷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当年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这是所唱之歌,也是第二轮劝酒,是对饮酒人生之正当性和精确性的论断与宣示。它对现世代价和历史代价发起寻衅,音调断然肯定,激越高亢。第一轮劝酒的情由是人生苦短(曹操《短歌行》发轫的主题),个中留下一道逻辑缝隙,“人生苦短”还不是饮酒的充分情由,人们也可以说,正由于人生苦短,以是更要积极作为,早点成名,得到富贵(“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一轮劝酒的情由显示,其他选择没意义,世间权势富贵(钟鼓馔玉,钟鸣鼎食)不值得看重,无法让人欢快知足,而道德高洁的古圣先贤贫苦单调,寂寞无名,都不如饮酒沉醉的人生更有代价,不如饮酒的人生活得精彩热烈且能留名后世。然后李白举出一个留名的饮者,曹植。曹植是王子,才华横溢的墨客,过着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他被夸奖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在洛阳平乐不雅观大摆酒宴,喝知名贵名酒纵情欢快。这便是“与君歌一曲”的“歌”的内容。
饮酒的情由不仅仅是前面所言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还上升到人生不雅观、代价不雅观和天下不雅观的高度,一种绝对的高度。这是李白不同于一样平常醉翁的地方。他要使饮酒成为“政治精确”。这完备是颠覆性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对圣贤和历史的代价进行了颠覆。李白饮酒彷佛从来不但是饮酒,还在喝代价不雅观与人生不雅观,但都不如斯次具有颠覆性。他在《月下独酌·其四》中说,“当代不乐饮,浮名安用哉”,在《行路难·其三》末了一句说,“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一不雅观念来自他多次在诗中夸奖的晋朝的张翰。
《晋书》张翰传云:“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张翰选择面前的快乐,以损失身后名为代价而不在乎。到李白这首《将进酒》,说这些圣贤什么都得不到,不仅没有当世快乐,后世也籍籍无名。饮酒的人,既有当下的快乐,还将在后世被人传颂。这必须得喝了。
明 陈洪绶《蕉林酌酒图》
“同销万古愁”
主人作甚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里从唱歌中跳了出来,进入饮酒的现实,或者说,他的高歌被钱的问题(现实问题)打断了。此处面临一个理解上的迟疑:这个“主人”指的是什么人?唐诗中,主人一样平常指地主,家主,东道主。但这里如果是宴客招待的家主人,怎么会对客人说钱不足?因此,我们设想这场酒是在酒店里喝的,不是在家里。设想便是黄河边的酒馆,三个人一边看着黄河奔流一边喝,然后李白直接以面前的黄河起兴,唱了这首劝酒歌。“主人作甚言少钱”,这句谈钱,既顺承上面“陈王当年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又照料“千金散尽还复来”。这里的跳跃有种笑剧性的诙谐感:正沉醉在兴头上,喝着酒对着朋友唱歌、谈着历史代价人生不雅观的李白,被打断了,要钱的人来了,店主来催账了。第一次劝酒提到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主题又涌现了。
前面仅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来应对,这次要实际支付了。但李白不搭理他,不在乎钱,直接对朋友说,这店主说钱干吗?咱们只管拿来喝便是了,没问题,“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浪漫主义墨客李白纵情饮酒,始终面临钱的问题。这是抵牾,他不回避,且每次都能战胜,充满信心。讽刺性的现实被崇高的激情战胜,这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敢于付出统统。“径须沽取”,不惜统统、拼尽所有,只求有酒。个中原因,除前面诗句说过的“千金散尽还复来”,还由于他通过饮酒要办理的是人生最重大的问题,远远超出钱财这身外之物:“与尔同销万古愁”。
本来为“尽欢”而饮酒,末了成了为“消愁”而喝,并且不是一样平常的愁,而是“万古愁”。诗在结束时来了一个大迁移转变。末了一句,取消了前面所鼓吹的行乐,可谓否定之否定。什么是万古愁?便是贯穿古今、无从破除的绝望。万古,指与天地同长久。这种和人的生命与生俱来、无法消解的人类共有的最根本痛楚,当然是韶光,是短暂的生命本身蕴含的有限性(去世亡)和无限的存在希望之间无解的冲突和痛楚,是面对无限时空的人体认到自身微小短暂的存在之痛楚,是人类存在终将面临去世亡这个最大仇敌,不能自由如愿的希望挣扎。这便是我们的万古愁。
元 钱选《扶醉图卷》
中国的饮酒诗传统始于《诗经》的雅颂传统。“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高朋,鼓瑟吹笙。”“我有旨酒,以燕乐高朋之心”(《诗经·小雅·鹿鸣》),一种亲友相聚宴享的欢快友爱,符合儒家其乐融融的伦理空想。这些诗句常常被后世引用,曹操的《短歌行》就引用了前四句,也是写“宴享高朋”的情景,但曹操引入了个人存在的危急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欢快的众声合曲中,透出了个人独唱中痛楚的腔调。
李白这首劝酒诗完备是个人之歌,和曹操的《短歌行》同样浸透了生命的欢快和痛楚。他劝饮酒既发自欢快,又出于忧闷,饮酒是与欢快相伴的悲愁,与悲愁相伴的欢快。从曹操开始,酒就和忧闷联系在一起。曹植的《箜篌引》也将饮酒与光阴迅捷、生命短暂联系在一起,在快乐和忧闷间转换。在李白这里,起于尽欢的饮酒,末了落到理解愁,而且是万古愁。生命的痛楚无法办理,只能躲避、遗忘,沉醉在酒的愉快中。这种暂时的解脱也是令人感到痛楚的。这首诗的起与结,感情都非常强烈,悲哀劈天盖地而来,中间尽欢高歌而饮,又在痛楚弥天中而终。但李白反抗宿命的悲剧性英雄英气终属人间。
刁悍生命力的不屈
李白这首诗是人对韶光流逝、生命注定消亡的命运的反抗。诗是一种有关强度、深度、高度的艺术。很多诗的履历,乃至主题,都是共有的,差别只在诗的强度和深度。表达得最深切、最强烈的诗,便是最好的诗。尤其是强度(intense)。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体会《将进酒》之以是好就在于它的紧张、强烈。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将进酒》编在鼓吹曲中汉铙歌之眼前,此目之下还收有李贺的同题诗一首: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喷鼻香风。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李贺这首诗写了饮酒的盛大场面,酒具奢华(琉璃钟,钟是盛酒的羽觞),酒的名贵(琥珀浓,珍珠红),酒菜的珍稀(煎炒烧烤的龙凤之肉),饮酒环境的豪华(罗帏秀幕,绣着花的绫罗绸缎围成的地方),助兴乐队的精彩(用龙骨做的笛子,用鼍皮,鳄鱼皮做的鼓,年轻女子的歌舞)。韶光是暮春,桃花纷落的时节。意思是,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氛围、场合,这么好的光阴,你赶紧喝吧(劝君),喝他个昏天黑地(终日醉酩酊)。刘伶是魏晋绅士“竹林七贤”之一,随时准备醉去世,让人扛着铁锹随着自己,醉去世在哪儿,就在哪儿把自己埋了。但酒没让刘伶去世,是韶光让刘伶去世了。因此,你就抓紧韶光尽情喝吧。李贺这首诗,用的都是贵重珍稀之物品,来渲染夸饰场面,但缺少激烈充足的内心力量的驱动,这些物品、场景只是被堆砌在一起,没有强烈的情绪传染力,整首诗像一篇应景作文。
类似的劝酒诗很多,再举白居易的一首《劝酒寄元九》:
薤叶有朝露,槿枝无宿花。君今亦如此,匆匆匆匆生有涯。
既不逐禅僧,林放学楞伽。又不随羽士,山中炼丹砂。
百年夜大分半,一岁春无多。何不饮美酒,胡然自悲嗟。
俗号销愁药,神速无以加。一杯驱世虑,两杯反天和。
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复兀兀,吾孰知其他。
况在名利途,平生有风波。深心藏陷阱,巧语织网罗。
举目非不见,不醉欲如何。
白居易也爱饮酒,元稹是他最好的墨客朋友,这是给他写的一首劝酒诗。道理都一样,生命短暂(犹如太阳一出就消逝的清晨藠头(薤)叶上的露水,只开一天的木槿花),你的生命也如此短暂。你不学和尚读经(学楞伽经),也不学羽士炼永生不去世药丹(炼丹砂)。白天很短,春天很短,生平的好日子很短,总是悲叹,不饮酒怎么过?然后讲饮酒的好处。同时处于官场中,那么凶险(有风波,藏陷阱,织网罗),每天睁开眼就瞥见这统统,不饮酒沉醉,日子怎么过?以是要喝。这些话就像平时的闲聊,整首诗很平淡,没有传染力和说服力。
和这些诗一比,李白《将进酒》的非同凡响就显著出来。李贺和白居易无疑是经典的精良墨客,上述引用的两首诗虽然非常一样平常,但也表示出他们各自的诗歌风格。不过李白就像他自称的大鹏一样超出“凡鸟”很多。李白诗的卓尔非凡之处就在于其情绪和措辞的强度,这种高强度的生命和措辞闪耀光芒,如烟花般爆发出残酷之光。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籍》中说自己写的那封信是“剖心析胆”,“一快愤懑”,便是把自己的激情亲切、羞辱、心肝都捧出来。这本身便是一种天赋。李白诗中的激越高扬,有一种刁悍生命力的不屈和反抗。
有时诗不在于内容如何悲观,而在于面对这悲观和绝望时,人的心性和气度。李白这首诗实质上很绝望,已经认定生命的无意义,但他仍旧引发出更大的生命激情亲切。这首《将进酒》一开始便是与韶光、与生命之流逝的对抗,中间涉及历史和现实,末了又落到无限的悲愁。但内容虽然悲观,墨客的精神态度却能振奋民气。李白有点类似加缪所言的“荒谬英雄”,无论如何无意义,仍要让生命尽情燃烧。这种英雄之气让人激动。李白诗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高亢昂扬,气势撼人,壮怀激烈,年夜方悲歌,震烁古今。古代描写过这种歌的风格,《列子·汤问》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薛谭随着秦青学唱歌,认为学会了,哀求离开。秦青到城外的路边为他饯别,唱了首送别歌,唱的时候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听了非常冲动,哀求再跟他学,再也没提过要离开。秦青的歌我们无从听到,而那传说中的“响遏行云”的高亢悲歌,在李白这首《将进酒》中真实地被我们看到了。他诗歌的腔调穿透我们,把我们带到激情的高空,让我们行云一样在散漫漂浮的人生中,惊异地停下来,等这歌声落下好一阵之后,我们才能从这激情中脱身,规复散漫的常态。
作者/雷武铃
编辑/张进 李阳
校正/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