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苏轼已经娶了继室夫人王闰之--她是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的堂妹,在王弗去世三年后嫁给了苏轼,从此跟随苏轼 “身行万里半天下”,辗转于大江南北、天涯海角,默默得陪伴着苏轼渡过他人生中起伏最大的一段韶光。
苏轼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一起上走走停停。他们先是到了陈州(今河南淮阳),和弟弟苏辙一家相聚,住了两个多月。
然后苏辙又陪着哥哥一家连续前行,一贯送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这里兄弟两又一起拜会了致仕(退休)后定居于此的欧阳修。年过六旬的欧阳修,虽然须发皆白,有些老眼昏花,但日子过得还算清闲,他说自己: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书一万卷、金石佚文一千卷,加上一个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因而自号“六一居士”。欧阳修见到苏轼兄弟,分外高兴,他们一起游湖、饮酒、赋诗,快意畅谈。苏轼还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一诗。盘桓二十多天后,苏轼依依不舍得动身履新去了。没成想,这竟然是苏轼和恩师欧阳修的末了一晤--第二年,欧阳修就因病去世了。苏轼俗务缠身,无法前来奔丧,只得满怀悲痛写下了《祭欧阳文忠公函》,以托哀思。
苏轼和弟弟苏辙也不得不在颍州分别了。出路漫漫,苏轼一起上意兴阑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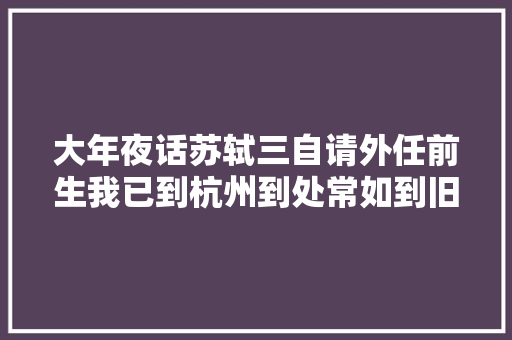
我行昼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一、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熙宁四年十一月尾,苏轼一家终于抵达杭州。“上有天国、下有苏杭”,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留恋于这座山明水秀、富庶繁华的城市。本朝的仁宗天子也不由得惊叹这里: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
苏轼很快情不自禁地陶醉于这片湖光山色之中,那些烦恼和忧郁不知不觉地溶解在这秀山丽水里。杭州三年,大概是苏轼人生中最幸福的光阴,他乃至情不自禁地在诗里吟唱到: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轼在杭州的官邸位于凤凰山顶,可俯瞰西湖,南见钱塘江。
俏丽的西湖一年四季如画,苏轼在他的诗中感叹道:湖上四季看不敷,惟有人生飘若浮。
他喜好在望湖楼上看月牙初升:
月牙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
他喜好在宁静的月明之夜,乘以小舟,在西湖里清闲地荡漾,算作群的鱼儿在船边细细,看朵朵荷花袅袅婷婷: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
西湖变个天,都那么可爱,风雨交加都是一番风景: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西湖的画意,在苏轼的千古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合适。
西湖在苏轼眼中,切实其实便是善变的仙女,他不禁深情得说道: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有美堂遗址
出了西湖,官邸附近的有美堂,也是苏轼爱去的地方。这处位于凤凰山顶的景点,因仁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而得名,是登高览胜的绝佳去处--左临钱塘江,右可俯瞰西湖。一个初秋的午后,苏轼和朋友相聚于此,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一声巨雷轰隆而起,顷刻间,乌云密布,狂风呼啸,山下的钱江水被风裹挟着飞溅而起,瓢泼大雨一会就急奔而来。苏轼诗兴大发,挥毫写下
《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
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说到钱塘江,自然就要说不雅观潮了。所谓“八月十八潮,壮不雅观天下无”。一年一度的不雅观潮时节又到了,这天,苏轼和知州一行来到预先选好的不雅观潮处。江边,早已聚拢了成千上万的不雅观潮者。忽然,一线银白涌如今远处的江面上,顷刻之间,彭湃的潮水,如成堆的积雪一样平常就涌到了跟前。惊涛拍岸,彷佛直上云霄,江畔高耸的青山都被隐没在了浪花之后。心情澎湃的苏轼,忽然以为这仿佛像是当年西晋大将王濬率领兵士顺江而下,攻灭东吴的情景。于是,苏轼写下了咏钱江潮的名作: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
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玄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万人喧哗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江边出生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叫江水向西流。
吴儿成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张,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二、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在杭州,苏轼留下了无数幽美的诗篇,也留下了许多浪漫的故事。苏轼本便是一个随意马虎亲近的人,他才华横溢,妙笔生花,自然是很随意马虎成为那个时期的男神的。
于是,江湖上便流传了许多男神的传说。
一天,苏轼和著名词人张先等几个朋友在孤山前临湖亭上闲坐。忽然瞥见湖中央一艘画舫缓缓行来,停靠在亭子前面。船上是几位淡妆女子,只见个中一位稍年长的女子,看起来风采绰约,低头拿起一张古筝,旁若无人的弹奏起来,一曲《长相思》弹完,又接着弹了一首《高山流水》。其声缥缈空灵,如梦如幻,如泣如诉。
正当众人还沉浸在余音绕梁的韵味中时,这位女子缓缓起身,向着苏轼深深道了个万福,然后亲启朱唇说道:
“我自幼仰慕苏师长西席的才情和为人,尽力包罗您的诗文,常常一读数遍,爱不释手。可惜总是无缘相见,最近才听说您已来到杭州任职,不禁大喜过望。便不顾已为人妻,抛头露面,特意期待于此,为师长西席献上一曲,聊表心意。”
说完,就转身返回船舱中,船便划行起来,不一会儿就消逝在湖山远处,只有模糊的歌声远远随风传来,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等苏轼回过神来,不觉有些痛惜若失落,于是提笔写到: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践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三、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杭州是人文荟萃之地,湖光山色中,有不少文人绅士搜集,也有不少得道高僧隐居于此。苏轼在杭州,常常漫游名山古寺,与许多高僧结为至交。
苏轼可以说自幼成长在一个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苏洵很喜好与名僧交游,母亲程夫人也笃信佛教。耳濡目染,加上成年后仕途上的各种阅历,都让苏轼对佛学的兴趣日益浓厚。
于是,他在不少诗文中,写下了自己从高僧、名寺中得到的抚慰和感悟。比如,初来杭州时,苏轼拜访名僧惠勤和诗僧惠思,相谈甚欢,回到家里,还久久沉浸在那超尘绝俗的清幽天下里。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闪动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屠。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遽遽。
作诗遑急追亡逋,清景一失落后难摹。
宁静的山林,让徜徉其间的苏轼以为匆忙禅意,也引发出这位才子的无数官员人生的哲思。在《书焦山纶长老壁》这首以诗谈禅的作品里,苏轼记录了在高僧开示下,顿悟的过程。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
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
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
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
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高下,一夜着无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每与师见,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海月辩公真赞·引》),和这些“世外高人”相谈,彷佛现实的痛楚与烦恼就很随意马虎得到解脱。在这样一次次的对话中,苏轼逐渐了悟人生,超越是非。这种教化后来成为他坎坷人生中极大的精神助益。
四、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神仙在高堂听说,苏轼曾以为自己前生是杭州的一名僧人。一则离奇的故事,大概可以解释这种情愫。一天,苏轼和朋友来到西湖边的寿星寺嬉戏,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苏轼,竟然以为这里的一起都非常熟习,一时之间,惊诧莫名。他忽然转身对朋友说:
“从院门到经堂该当有九十二级台阶。”
朋友震荡不已,就派人去数,果真一点都不差。苏轼又提及寺庙后院楼阁亭台和假山的支配,竟然也全部吻合。
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来。几年之后,苏轼在提及这件事时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常如到旧游。” (《和张子叶见寄三绝句》)
杭州这片奇丽的地皮,一度给予天涯流落的苏轼家的觉得。他深爱这里,作为一名地方官,他也深爱这里的公民。
熙宁五年秋日,苏轼和知州陈襄专门调集一批父老,讯问民间疾苦。大家险些异口同声说百姓饮水困难。
陈襄和苏轼这对合营默契的同寅,立时找来精通水利的人,在唐李泌、白居易等任杭州刺史时管理西湖、建筑六口大井的根本上,重新进行修复,修补,使得这六口大井重新焕发生机,清泉满满。
巧的是,第二年夏天,一场大旱就不期而至,杭州公民由于有这六口井,不仅有足够的饮用水,乃至还有富余,可用于沐浴和喂养畜生。
苏轼写了《钱塘六井记》,阐述六井由来和政治过程,并在文中指出了急民之所急,才能防患未然。
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
三年的通判生涯,苏轼险些走遍了杭州府的哥哥属县,富阳、新城(今新登)、临安、于潜等,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足迹所至,苏轼被山林野外间奇丽的风光和淳厚的公民所吸引,这些自然率真和恬淡安宁便常常被苏轼写入他的诗词中。
他写乡间炊烟袅袅,人们煮芹烧笋,为春耕准备饭菜:
《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竹篱茅舍,野桃含笑,柳枝婀娜,乡间父老,煮芹烧笋,吃好了就要闹春耕了。苏轼忽然被奇丽的风光和恬淡的生活所冲动,听着潺潺溪水声,缓缓地放慢了缰绳。
《新城道中二首》其二
出生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
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
小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主座清。
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田间地头,农妇村落姑,赤着白皙的双脚,在斜风小雨中行走,显得康健而充满活力。举头望去,远处的苕溪悄悄流淌,两岸杨柳依依,一个俏丽的村落姑正在临水对影装扮...
《于潜女》
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
觰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
老濞宫妆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
苕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
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
建德风光
然而百姓的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彷佛总是短暂的。北宋虽然富庶繁华,但那是对付统治阶级而言,下层公民,尤其是村落庄,清贫大概还是常见的。而在靠天用饭的农业时期,自然磨难一旦来袭,大饥荒便不可避免。每当碰着这种情形,爱民如子的苏轼险些是席不暇暖,整日里奔波在外,在十里八乡的田间地头,时而组织防涝,时而抗旱,时而捕蝗虫,时而赈济灾民。
随着他越深入地打仗公民,更深刻地理解民众疾苦,他便更痛恨那些高居庙堂之远的官僚权贵:
《雨中游天竺灵感不雅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神仙在高堂。
五、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此时的大宋,王安石变法正在风起云涌地全面开展中。这场变革,当然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性的。
于苏轼而言,他可能在政治上没有王安石那样的计策高度和眼力,但毋庸置疑的是,苏轼是心系苍生,爱民如子的--面对亲眼所见的民众苦难,他没办法视而不见,情不自禁地用手中的笔,替他们叫嚣。
熙宁新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统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改革的成果,再加上没有很好筛选、险些只要支持变法就提拔起用官员,于是不可避免得会扩大和加深对下层民众的剥削。
作为地方官员,苏轼目睹贫苦百姓在天灾和酷政的夹击下,难以为生的惨状,心情十分悲愤。他只能在权益范围内,尽可能地“因法以便民”。(《宋史 苏轼传》)
面对群众苦难,苏轼无法缄默坐视不理,哑忍不言,他总是常常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
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这个不详的年份,稻谷长势缓慢,眼看秋风渐起,却阴雨连绵,稻穗纷纭倒下,好不容易盼到天晴,一家人没日没夜得抢收。风雨洗劫后,仅剩下一点点稻谷,千辛万苦送到集市,价格却贱得如糠!
只管这样,也得把它卖了--由于官府对西北用兵,出了规定,赋税和免役,都要用现钱!
可怜,这一点点钱哪里够呢?在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吏昼夜催逼下,只能把屋子拆了,牛卖了,才勉强逃过一劫。明年又要怎么办呢?!这里已是雪上加霜,那边一个救援青黄不接为民的青苗法,又是一个要人命的陷阱。原来规定借贷志愿,在官府邀功请赏,各类打单之下,逐步就变成逼迫性的“抑配”。春借秋还,本利相加,假如碰着天灾人祸,根本无法偿清。于是豪强便趁机放印子钱获取巨额利润。
青苗法是让国家得利了,贫苦的民众却深受其害。许多元老重臣也明白,以是自青苗法颁布之日起,他们便勉励反对。苏轼早在《上神宗天子书》中便提出了反对见地,来杭州后,所见所闻,更是让他对青苗法强烈不满:
山村落五绝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落处处花。
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闷。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为了贷款、纳税、还债,村落民走上几十里山路进城,贷来的青苗款,几经辗转,早已不名一文。唯一的收成竟然是随着大人跑来跑去的孩子,不知不觉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
烟雨蒙蒙中的山村落,时时传来鸡鸣狗吠之声,多少农人就这样世世代代勤恳朴实地生活着。只要不饿去世,基本生活有保障,他们就会循规蹈矩,很随意马虎知足。假如这些什么这个法那个法不那么严厉,他们怎么会卖掉耕牛,换成刀剑,铤而走险,去贩卖私盐呢?
很快,官府就对这些武装贩卖私盐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朝廷更是派专人前来督导,一时之间,监狱里便人满为患。作为通判的苏轼,自然是免不了审囚犯,判案件的,于是便常常“朝推囚,暮决狱”。坐在威武的高堂之上,苏轼听着饱受反攻的贫苦百姓不断哀嚎,心里难熬痛苦不已,却不得不签下一张又一张的无情判词。连除夕之夜,苏轼都不得安宁:
大年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落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六、耳冷心灰百不问?使某不言,谁当言者?苏轼的这些诗歌一经写出,便被人们争相传抄。对民众的悲悯,在有心者的眼里,自然便是对新法的不满,苏轼当然也明白。他有时也会想起离京时表兄文同对他的劝告,“休问事”、“莫吟诗”,关心他的亲友也常常提醒他,苏轼也常常这样告诫自己。有一次苏轼和好友孙觉相会,怕又是牢骚太甚,便立下规矩: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可是,就像他的父亲早就预言过的那样,苏轼不睬解“装饰”,“不吐烦懑”才是苏轼的个性,“使某不言,谁当言者?”
为民请命、为国谏诤,苏轼认为那是士大夫应有的任务和责任。
苏轼对下层公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爱护,他在乡野奔忙间创造的新法弊端,他认为自己是有任务要说出来的,这样才“有补于国”。更难能名贵的是,苏轼彷佛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可以站队--他有着自己的思考,有着独立不倚的立朝大节。这样的勇气和节操,这样的良知,真当是难能名贵的--这大概也是苏轼在诗文之外永久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的地方。
苏轼很快将结束他的首次杭州之旅,接下来的仕途,又会何去何从呢?
参考资料:
王水照 崔铭《苏轼传》
林语堂 《苏东坡传》
《宋史·苏轼传》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续资治通鉴》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