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县人
实在,无论内在的思想,还是外露的言行,顾随都是很摩登、很新潮的,一点都不死板。论教诲背景,他毕业于北大英文系;论交游,他与当代诗明星冯至等人是石友;论师承,他自谓出自周作人门下,而平生最崇拜之人是鲁迅;他在燕大教书,随口飙的都是流畅英文;他也动笔写新小说,还入选鲁迅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年往后,他是专注于古典诗词,但其剖析理路,除了主打传统的“感悟兴发”,还是有深厚的西学作垫底的。
顾随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学问博识外,便是至情至性,而且还多才多艺。诗词就不说了,结集6本俱是大里手手笔,一九三四十年代的京城,诗词界无人不知“苦水词人”大名,只管齐心专心求变求新开刀搞“实验体”,造诣也有争议;他论书法,乃沈尹默门下高足,有渊有源,含咀精髓,足以称家;他乃至可称得上“准哲学家”,他讲禅宗,虽乏修持参证终是“票友”,但那种识见之高明,仍是同时期知识分子中少有的风光——或许不及周叔迦的湛妙,可比之胡兰成顾毓琇之流,毕竟要行家很多。
这样的人,实是民国时期,为人“新思想”与“旧道德”融汇无间,而“旧学邃密”和“新知深奥深厚”又能水乳交融的范例人物。纷纭泊泊时期里,天边无伴月,海上一孤鸿,衔杯且自从容,但身后所隐是一座辽阔而清峻的文化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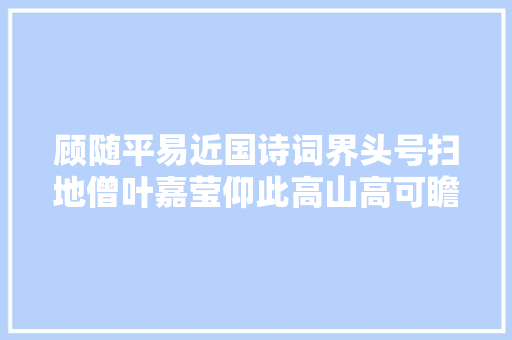
如今,也说不清幸或不幸了,顾随是“生前身后皆寂寞”。张中行晚年写文章,嗟叹为“实过其名”。
最有名学生叶嘉莹女士
不幸,是如此风骚人物,还是培养出叶嘉莹、周汝昌、吴小如、史树青、邓云乡等一众大佬的“当代学界祖师爷”,竟长达数十年英名埋没而不称,以至于那些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都不晓得,“五四往后,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大神”。我们的学术荒诞剧,从没停滞过上演。
顾随的寂寞,是我们的不幸。从1950年代~1995年前后,并没多少人能有机会领略此等风采,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呀!
读不读袁行霈教材有何关系呢,而顾随论诗词,何尝输给钱钟书、缪鉞、罗忼烈、吴小如诸老?提及来,文史学界实在至今也有不少此类“冤屈积案”,比如写出《宋诗选讲》的陈寥士、出版《黄庭坚诗选》的潘伯鹰、《海绡说词》的作者陈洵,如今即便文学博士又真的熟习吗?
潘伯鹰,1904年-1966,安徽怀宁人
所谓“幸”,这是说,寂寂寞寞本便是他平生心愿,所谓“短长何必付公论”,遁世藏名是他自身想讨要的。如此,实也可免遭我等自媒体文痞荼毒,被无所不至的键盘侠一次次消费到不堪。钱钟书何尝想“暴得大名”?一旦“天下无人不识君”后,代价便是被各种讹言媟语丑化到体无完肤。他们这是有先见之明的。
顾随是1995年前后,以“被遗忘的诗词大家”的身份,被挖掘出来“重新出土”的。这当然是实至名归的殊荣,是他应有的身后报酬。诸如《顾随诗词讲记》、《苏辛词说》、《东坡词说》,辞采宏富,文笔光昌,险些每篇笔墨都值得抄录几遍呀!
当代学人谈文论艺的书本,其数何其伙颐,但顾翁那几本始终是鄙人最得力的两三部之一。张中行说他,“笔下真是神乎技矣”,我也有同感。只管,这些书基本都是教室随口讲来的。
顾随讲诗词,最大特色在见情、见性、见趣、见人。他说“老杜七绝,选者多选其《江南逢李龟年》一首,此选者必不懂”,由于“此首实用谰言写出,坠坑落堑,入窠臼矣”,一样平常人哪敢发此“狂论”?他说“初唐王绩的《野望》,众人皆知颔联‘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辉’乃是名句,岂不闻颈联‘猎马带禽归’一句便胜却王维《不雅观猎》全诗,唐诗之凝练,之蕴藉,之气概皆在此句中灵光一现”,真是好新颖的评价,独到且深中肯綮。
他批黄庭坚,说“平日读山谷诗,最不喜他‘看人获稻午风凉'一句。此大墨客不独如世所谓严厉少恩,而且险些全无心肝。获稻一事,头上日晒,脚下泥浸,何等辛劳?”如斯,狂辞怪论又无懈可击,当年我读来笑过大半天。顾翁放言无忌,什么都敢说,但令我重新认识了各种“诗”。他对诗词乃至诗词天下中人,有着流自肺腑不克不及自休的关心。
叶嘉莹毕业时
顾随诗词专家、又能作诗,且深受西方文明洗礼,以是谈诗论词总能人所未言,发人深省。他之所谈,力破八股气、讲章气、刺绣气及烟雾气,实不止是在议论学问了,而是总能抖擞出一股能够提凘生命的真实力量。他遗世独立,他卓尔不群,他至情至性,他畅快淋漓,虽不免有偏颇,也不好说字字珠玑,然而却是“真正的墨客”,同时又是“深邃的学者”无疑。
有人说他是“民国诗词界第一扫地僧”,这话岂完备是笑谈?
我看顾随,以为他最大遗憾,在于说得多、写的太少,是“述而不作”一类,导致“千古文章未尽才”。他把所有情怀与担当,险些都用在了培养学生上面了。
对付学者而言,这是最大的无私。他实是学费自煎式的好老师。活了63岁,一辈子都在教书。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没有3千弟子的环抱,乃至也没提出过什么特出的教诲理念,统统彷佛都是无心插柳,漫然无所存心。但在我心中,他不仅是一流的诗词学者,也是一流的教诲家。
自1920年,北大英文系毕业后,除了前几年教了会中学,他余生都在燕大、辅仁等大学里当教授,直到归于道山的末了光阴。他诗文所透露的信息,已经很明白:始终认定“西席”是最大本分,三尺讲坛是施展学术抱负的最主要舞台,而因性施教造就英才便是最高天职。
高弟周汝昌
他是“天生西席”。他的性情,是极其和蔼可亲的。张中行说他“身材较高,秀而雅”,待人接物没有一丁点光滑油滑的样子,说学生与他交卸,每每只交谈一会,就会无端深受冲动,当是实录。叶嘉莹也满含泪水说过,顾老师对他人尤其是对学生,是意外的宽厚,处处为人设想,尽其所能关心人,唯恐别人有丝毫不满意,或受到委曲。
他中年往后,感于国事是非,曾一度沉迷于佛学。但他作为“著名佛学家”,绝非那种言疾辞厉、清肃远人的道学家样子容貌,而是典重不乏风趣,满满都是释家的慈悲心。有人说,像他这样一个人,对学生的好,与那种予人的温暖清闲,“是罕见的”。
他教课,派头犹如名角登场。周汝昌晚年回顾,说讲课是顾翁的“当行本色,为他人所难以伦比”。还说他是一位传道解业、最长于讲堂说“法”的“艺术大师”。周汝昌年轻时上的是燕京大学,是见过世面的人,不大可能胡扯,大概当年的顾随真的让他屡屡惊艳吧。75年后,女弟子叶嘉莹老人依然说,“仰此高山高,可瞻不可及”。
这样擅学善讲的巨星名宿,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得意的弟子,诸如周汝昌、叶嘉莹等位,后来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受他沾丐之深,终生时刻不忘。他该当是最懂因材施教的那种老师吧,教子路收、教颜回放,精进无有息时、树人唯恐或倦,真教诲家也。
“忘年交”张中行
看他学生们,历经水火兵虫与岁月播迁,保存下来的那些教室笔录,那份严密、周详、谅解、温煦、精辟,真犹如亲聆謦欬,自由感想熏染到一股大关怀、大激情亲切及大情怀,早已熔铸在里头。
如前所述的,顾随被众人遗忘了几十年,一大缘由便是他真的无心成名成家。如今薄有声名,完备不是他本意。
女儿顾之京,河北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
他穷究不立笔墨的禅宗,自身下笔也自持得很呀。他生前,同行间虽也有名气,也是名教授,甚或是名词家,但是他基本没有写过什么著作。他写诗填词,完备是自抒怀志,是自娱自乐,是与友朋们互换感情的借物;他也出过一本论禅宗的小册子,也不过是私淑弟子张中行“盯梢”而来——彼时的张中行,刚毕业籍籍无名,靠主编一刊物谋生,听闻乞助之声,他如何袖手旁观呢?
诗词天下
他现在那一摞摞作品,从书稿到文稿,绝大部分都是讲课条记,是老学生叶嘉莹、女儿顾之京等人念念不忘于他,在他身后给爬梳整理出来的。比如上海古籍出的那部《顾随文集》,厚厚达700多页,可多是诗词、禅理、戏曲的讲记,是“教室条记”,并非他专程执笔而就。顾翁韶光固然宝贵,可是真的无法抽出一点点空隙,将这些零金碎玉整理付梓吗?只能说他是不愿吧!
他是求“教书为乐、内心安顿“之人,与时下那些所谓“名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筐还要绞尽脑汁出书扬名的,实有寰宇之别,也是两路人。去年,某豆瓣读者留言,“顾随的存在,足让康震郦波们无地自容”,是耶非耶?
人都说,“最难忘,名心一段”,但是成名成家对他而言,彷佛是毫无意义的。他勤奋地读书,完善自己的学识与情操;他全副身心付诸教书、濬发溉沃般地授徒,像只负重万里的“骆驼”,只希望造就出能“透网金麟”的一些弟子,传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妙聪慧与不朽精神;他爱国如护惜己身,眼见沦灭之危,他常为之黯然下泪,还由于矢志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过。对付磨难,他是渺然忽略的,他不是那种壮怀激烈的读书人,但有这种气节。
因是“教室条记”而来,其作品引文也会有疏漏
无论是共倒金荷的青年时期,还是哀乐中年时的寒光零乱,亦或是晚凉幽径期间,顾翁所念怀所自期的,始终都是做一个本分人,做一节人梯,从没预想过会有一天能如今天这么出名。
春日将尽风过蔷薇,荼蘼之后便是凋零。我常常想,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学者,此后也再难见到了。
民国学者确实是有“范”的,顾随即“范式”之一。不说那种“风骚高格调”了,单他这种治学风范,只怕也是在古典圈绝迹了。这些年,借了各种缘由,我也见识过不少古典文学从业者,实在也有不少大名在外的,学问不可谓不好,唐诗宋词也是张口就来,但一开口就不免冬烘气十足,见识也很卑陋,内心是很失落望的,更分外怀念顾随这样的学者。我常嘀咕,当所谓“传统”适成捆绑精神之枷锁、所谓“古典”沦为束缚心量之绳具时,我们学而习之的意义到底在哪呢?
以是,我特殊感谢很早就碰着顾随,或许能间接管到一丁点警觉。想我初读顾随,始于高中毕业那一年。彼时,与二三朋侪携手同游礐石风景区,途经著名的“汕头购书中央”时,省下了买“班尼路”上衣的钱,买到一本他的《诗词讲记》。从此往后,常持常读,屡怀惊喜,心怀感念。
“民国范”.视平线\摄
在我心中,顾随该当还称不上“学问大师”,但他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顾翁临终前,留下词句,“凉雨声中草树,夕阳影里楼台,此时怀抱向谁开”——这个疑问,真的可以接着想几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