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族群中,尤以北方族群为多,北方族群的代称中,又以“胡”为多,与“胡”相似的,还有“虏”与“胡虏”两词。
三者都是意义较为宽泛的代称,可以指代不同工具,那么“胡”“虏”与“胡虏”有什么关系?三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唐代“胡”的含义
唐代“胡”的含义。关于“胡”,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在“胡汉语境”消亡之前,“胡”与“汉”的并存成为史乘书写的常态。然而“胡”作为一个定义模糊的词汇,并不具备精确的界定例模,故而学界对付“胡”有不同的认知:森安孝夫认为唐代“胡”指粟特人,这当是“胡”所指代的最小范畴。蒲立本认为“胡”紧张指印欧语系的西方及中亚人,粟特人只是个中最突出的代表。王国维认为“胡”在六朝之前指高鼻、深目、多须之北方外族,古代曾专有“胡”名之匈奴亦在此类,汉唐之后,匈奴势微,北方兴起之鲜卑、蠕蠕、突厥、高车等皆与匈奴异种,西域诸族因描述类似匈奴,故而专有“胡”名。
作者对中国古代“胡人”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对这一观点的变革进行了阶段划分,其根据外面特色作为剖断胡人的标准并不完备适用于唐代。作者所论“西域诸族”亦不甚明晰,由于西域在汉文语境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二者所指并不相同。谢弗的认知与王国维大体相同:“在中世纪,包括在唐代,‘胡’紧张用于称呼西方人,特殊是用来指称波斯人—虽然有时唐朝也将天竺人、大食人、罗马人都称作‘胡人’。”谢弗对“胡”的主、次语境都予以解释,较之于王国维所指更为详细,但也并不能完备将唐代胡人席卷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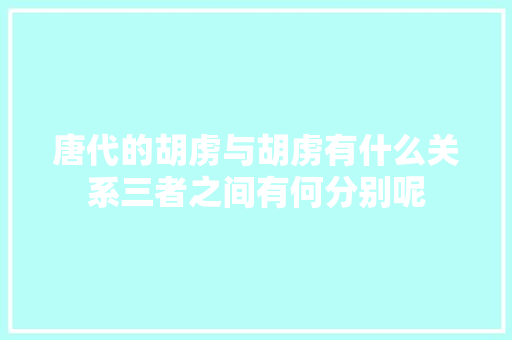
谢思炜对唐代诸多“胡”的例子进行了考释,认为其都属于对文有别,统言则一,“胡”与突厥对言是指西域胡人,但同时仍可用以统言北方、西方诸族。作者指出了“胡”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含义,并否定了古人关于“胡人”在唐代专指西域胡人的不雅观点。李鸿宾认为“胡人”是早期农耕汉人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的称呼,后来转向西域,以粟间谍资主的“高鼻深目”的中亚人为范例,有一个从北转向西的过程,北方游牧系统的“胡人”到唐代已正式退出中原汉人的不雅观念。邓小南认为在唐代“胡”并非单指塞外胡族,也包括内附诸族,二者分别在贸易、艺术和政治、军事等方面对唐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胡/汉”区分成为唐的内忧。
由于作者着重于谈论由“胡汉之分”到“华夷之辨”的转化,无须对唐代“胡”的详细范围做一界定,但其指出“胡”包括内、外两个群体,将这一种族问题与政治问题相联系。荣新江从西域粟特人、西域龟兹人、西域于阗人、印度人、突厥人、唐前期汉人、唐后期汉人平分歧群体出发,谈论了其各自主场上的“胡人”内涵,对“胡人”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胡人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狭义的胡人紧张是指操波斯语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更狭义的胡人才指粟特人,用胡人指代粟特人或许是由于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政权中人数最多的缘故。
此外,作者指出,唐代文献中与“胡”连用的诸多词汇,大多也是指粟特胡。作者在诸多学者见地之上做了概括剖析,但并未局限于汉人视角,而是从不同群体出发,剖析各自语境下“胡”的含义,末了,又对“胡”做了广义、狭义、更狭义的区分。
大体而言,“胡”最狭义的含义特指粟特人,当“胡”与突厥对言时,即指西域胡人,更广义也可代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但这并不能将“胡”完备包含。以下诸族亦可用“胡”表示。
奚、契丹等。在唐代文献中,契丹也可能被称为“胡”:《旧唐书·地理志二》“幽州大都督府”条载有“东北蕃降胡”,有研究认为,个中“降胡”并非指“杂胡”、九姓胡,而是指奚、契丹、室韦、靺鞨、突厥等部落。《资治通鉴》亦记载王武俊自称胡人,此时“胡人”成为与汉人相对的泛称。同样亦有奚及靺鞨自称胡人的例子,史宪诚听闻李㝏去世后,对韦文恪自称胡人。
沙陀。此外,沙陀也有被称为“胡”的情形,据《资治通鉴》载“沙陀劲勇冠诸胡”,关于“诸胡”是否包括沙陀,并不难辨别,须要谈论“冠”的含义。《辞海》将“冠”阐明为“位居第一”,古代汉语中大意也是如此。笔者仅包罗《资治通鉴》中部分“冠”的利用,如单雄信名冠诸军、王伏宝勇略冠诸军、王秀士宠冠后庭均是此类,其他文献中也有许多类似材料,仔细剖析,大意均为“在自身所处的群体中为第一”,因而沙陀也包含在“诸胡”之中。
杂胡。与“诸胡”相似的是“杂胡”,对此学界有不同见地:陈寅恪认为“杂种胡”即九姓胡,唐长孺对与匈奴有关的屠各、卢水胡、羯胡、乌丸、乞伏、稽胡等部族做了剖析,将“杂胡”界定为混血、混种。李志敏对此提出了不同见地,他将魏晋至隋唐的“杂胡”比定为“小胡”,否认特指混血之义。黄永年认为“杂胡”并非某一特定民族,而是对付多个胡族的泛称,实在用工具视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革。鲁西奇对魏晋“杂胡”做了研究,认为“杂胡”起初是胡人中占主导的种类对其他规模较小、地位较低之种类的称呼,意为“其他的”“较小的”,汉人沿用此类划分办法,随着“胡”所指范围的扩大,“杂胡”遂成为建立政权的某一胡族对其所掌握的其他胡族的称谓。
王义康对李志敏的不雅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杂胡”是指其种类繁多而言,并非指其小弱。其观点有一个变革过程,魏晋时“杂胡”是指匈奴帝国解体后,曾经与匈奴部族有过政治统属或血缘关系的有关部族。至唐代,匈奴杂胡均已消逝,惟西域昭武九姓胡依然保留有种类繁多的特色,故在隋唐往后昭武九姓逐渐独擅杂胡之称。学界对付“杂胡”的谈论是基于“胡”的条件之下得以进行的,魏晋六朝“杂胡”也不能与唐代等同,但仍可以给予我们一定启迪。
唐代“虏”的含义
“虏”并不专指外族,在中国古代,“虏”的另一个含义常常指代“仇敌”,是日然是一种贬称。刘邦在被项羽射伤后说“虏中吾指”,此处“虏”自然指代项羽。在汉代以“虏”表示外族时紧张指匈奴,也有指代羌族及汉人叛乱者的情形。
以上诸例为汉及以前“虏”的含义,这种指代“敌对者”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大体是稳定的,差异在于不同政权所面对的仇敌不同,但均可包括外族与本族两大类型。
敌对者。用“虏”指代敌对者的情形自唐初至唐末始终存在,在不同阶段,政权所面对的详细敌对者也有不同。在隋末战役中,与李唐逐鹿的诸政权中,王世充、萧铣等均被后世史家以“虏”称之。河间王孝恭攻萧铣时,在进军江陵、攻陷水城之后,散船于江中,诸将因此劝诫曰“虏得贼船,当藉其用,作甚弃之,无乃资贼耶”?萧铣见船被江而下,果真屈膝降服佩服。魏徵在与徐世勣的信中同样用“虏”指代王世充,称李密“败于奔亡之虏”。李密败后,魏徵归降李唐,并劝诫徐世勣归降,便用“虏”加以贬称王世充。贞不雅观期间,魏徵欲以目疾辞位,太宗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此处“仇虏”当指李建成,“任公以枢要之职”当指政变之后,太宗未介怀魏徵的身份,依旧加以擢用,同胞兄弟既为仇敌,以“虏”称之便不足为奇。
李唐统一之后,面对叛乱之敌,仍会用“虏”表示,至朱泚叛乱,仍有此类用法,《旧唐书》记载朱泚乱后,朱忠亮“为虏骑所获”。《郝玼传》中记载郝玼“声振虏庭”。到了唐末,黄巢叛逆,唐臣则蔑称其为“前日贩盐虏耳”,以表示黄巢之卑微,此乃张濬说服平卢留后王敬武时的辞吐,以劝诫王敬武切勿舍累叶天子而归贩盐虏,王敬武也屈服了张濬的劝告,未投靠黄巢。对付藩镇兵将,也可用“虏”指代,元和十二年,李道古攻申州时“为虏所杀”,李抱真遣使诈降于王武俊时,王武俊亦自称“虏将”,《资治通鉴》中另有武俊自言“胡人”及“胡虏”的记载。
外族。用“虏”指代外族在唐代史估中较为常见,由于每个朝代所面对的外族不同,故而“虏”所指代的外族会有所差异。
突厥、铁勒、回纥、薛延陀。突厥于隋末唐初最为壮大,故而涉及突厥的记载,在此阶段最多,用“虏”指代突厥的例子亦有不少。大业十一年,突厥犯边,李渊备之,“虏见高祖,疑不敢战”,《新唐书》亦记载李世民解隋炀帝雁门之围时,世民亦称突厥为“虏”。武德七年,颉利、突利入寇,李世民引兵拒之,《资治通鉴》记载世民与李元吉对话“‘今虏骑凭陵’……”元吉惧曰:“‘虏形势如此,奈何轻出……’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此段对话中多次涌现“虏”,可谓范例。贞不雅观初年,突厥入侵肃州时,公孙武达与之力战“虏稍却”。
武周朝,突厥入寇河北,武则天任命薛讷为将门,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讷因称其为“丑虏”,此类例子还有许多,不能逐一列举,可见突厥被称为“虏”是较为常见的。贞不雅观年间,薛延陀率回纥、同罗击李思摩,薛万彻援之,于途中“与虏相遇”,“虏”为薛延陀、回纥、同罗所组成的殽杂力量。关于铁勒,仆固怀恩叛乱,引吐蕃、回纥、党项入寇,史乘载“虏寇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此处的“虏”自然指代的是仆固怀恩及其所纠集的吐蕃、回纥、党项等大军,或用以指代其较为繁芜的构成,阿布思及仆固怀恩均为铁勒部人,自然也是“虏”。
高丽、百济。南北朝期间,高丽、百济趁势崛起,自隋统一,炀帝攻打高句丽至唐太宗、高宗连续征伐,此阶段与朝鲜半岛三政权冲突较为激烈,史家在记载时自然也会利用贬低性的称谓。《资治通鉴》记录了大业九年隋炀帝与侍臣的对话,称其为“高丽小虏”“蛮夷”“小寇”,都是对高丽的贬称。唐高宗时,苏定方伐高丽,围平壤不克,高宗乃诏刘仁轨与金法敏议去留,将士皆欲还,刘仁轨亦称其为“虏”。
契丹、奚、室韦。平定高丽之后,奚和契丹在武周朝开始崛起,侵扰东北。《旧唐书》记载万岁通天年间王孝杰平叛契丹时写道“孝杰军至东峡石谷遇贼,道隘,虏甚众”。神龙三年,姜师为备奚、契丹之寇乃为平虏渠,此虏为奚及契丹。开元二年六月,薛讷讨奚及契丹,为契丹及奚所败,玄宗乃有制曰薛讷“衄之虏境”并除其爵。“衄之虏境”即表示薛讷在讨伐时的失落败。王武俊之孙王承宪墓志亦记载承宪先祖“由余去虏,来仕于秦”。
吐蕃、党项、吐谷浑、羌。自松赞干布统一以来,吐蕃逐渐壮大,不断东扩,蚕食李唐边陲,安史乱后,乃至攻进长安,又趁机盘踞河西,成为唐的劲敌,故而对付吐蕃的记载较多,也会用“虏”指代。
杂虏。除却“虏”的单独利用外,另有“杂虏”一词也较为广泛地为史家所利用,其详细指代工具针对不同的语境会有所改变,是较为笼统的称谓,与“杂胡”一词较为相似。仆固怀恩叛乱时,曾有记载:“八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山贼任敷、郑庭、郝德、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是时,急召子仪自河中至,屯于泾阳,而虏骑已合。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虏围之数重。”
此处“杂虏”当是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山贼等诸多群体的统称,用以表示叛军繁芜的构成。贞元十八年,韦皋攻打吐蕃,在进攻维州时,赞普遣论莽热“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此处“杂虏”表明吐蕃纠集诸族兵力予以反抗,但确切构成不得而知。与之相似的还有朱滔,朱泚叛乱之后,立朱滔为皇太弟,兴元元年正月:“滔驱率燕、蓟之众及回纥杂虏号五万,次南河,攻围贝州。”此外,还有“党项杂虏”、“邠宁、鄜、夏杂虏”、“北边杂虏”等诸多表述。
唐代“胡虏”的含义
作为“胡”与“虏”的合成词,“胡虏”所指代的工具并非这两个词的合集或并集,而有着较为确切的指代工具。早期指代匈奴的例子很多,如《史记》中记载,元朔八年,李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途中为匈奴所围,李广之子李敢率数十骑直贯匈奴,还与李广曰“胡虏易与耳”,李广以弩连杀数人,因而称“胡虏益解”。
此外,《汉书》及其他史乘中也有许多称匈奴为“胡虏”的记载,这是由于汉代所面临的紧张外敌是匈奴。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期间,外族生动,相继建立政权,至隋唐完成统一,所面临的外族更为多样。“胡虏”所指代的工具也是多变的。在唐代,紧张有以下几种情形。
突厥。贞不雅观初年,突厥归降,关于如何处置突厥,大臣有所争议,据《通典》记载:“时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诏议安边之术……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虚矣。”温彦博并不认同此举,太宗终极屈服了他的建议,处降人于朔方之地。《旧唐书》亦记载:“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突厥传》中记为:“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资治通鉴》中同样记载“可以化胡虏为农人”。弘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笃禄入寇,朝议欲废丰州,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要冲,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疆。”
吐蕃。撤除突厥以外,史家也常以“胡虏”指代吐蕃,自松赞干布统一以来,吐蕃逐渐壮大,因而不断东扩,与唐冲突渐增,安史乱后愈甚。《资治通鉴》记载仪凤三年魏元忠上言御吐蕃之策时说“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及马嵬驿之变,将士以杨国忠勾结吐蕃为由,将其诛杀,情由便是“国忠与胡虏谋反”。对付将士来说,这或能增加其动乱的正当性,毕竟勾结外敌罪不容诛。
其他外族。首先是西域胡人。自魏晋以来,中原受西域胡人影响渐增,涉及宗教、舞乐、饮食、衣饰等诸多方面。《通典》记载,贞不雅观初,太宗合考隋朝南北之乐,称“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音乐之外,隋唐时期舞蹈也受外族影响,“浑脱”便是其一。浑脱本是出自伊朗的舞蹈,经由龟兹传入中原,北周大象元年尾月在正武殿上使胡人作此舞,以水浇身,谓之“乞寒”,唐代以武后、中宗时最盛行,不但都邑相率为之,宫廷中亦舞《浑脱》。
神龙元年大水,上乃诏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极谏,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但吕元泰反对胡俗之议并未被采纳。对胡风的排斥恐怕要到安史乱后方才明显。此外还有关于西域胡人的例子,安史乱后,睢阳之战中,张巡恪守,带兵不依古法,人问其故,张巡曰:“今与胡虏战,云合鸟散,变态不恒。”《资治通鉴》记录此事时也在注文中写道“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
其次是回纥等。至德二载肃宗借回纥平叛,攻入西京后回纥欲劫掠,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劝复东都如约,百姓、军士、胡虏见俶拜者,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
”“胡虏”自然是回纥及西域兵。《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代宗幸陕时“及在泾阳,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因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叛乱,郭子仪屯军泾阳以备之。“胡虏”一词亦是对仆固怀恩所率叛军的统称,看重的是其外族属性。
结语
吐蕃一样平常不被称为“胡”,但可被称为“虏”及“胡虏”。高丽、百济可被称为“虏”,但又不被称为“胡”或“胡虏”。胡最初是指代匈奴、月氏等游牧民族,外面上高鼻多须、经济上以游牧为主,均与汉人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匈奴解体之后,其治下诸族入塞内,使得“胡”的分布及观点逐渐泛化,指代北方及西域诸族,其种族与文化均有别于汉人。吐蕃一样平常不被称为“胡”,一方面是由于吐蕃至唐代方才兴起,并非匈奴之系统。另一方面,吐蕃在史乘中一样平常被简称为“蕃”,这在相称程度上替代了“胡”。
高丽等族在外面及生产办法上类似汉人,且自古与中原联系密切,受中原礼乐影响较深,在种族与文化上均类似汉人,故不被称为“胡”或“胡虏”。“虏”是对付敌对者的蔑称,并无民族之差。“胡虏”则是对付外族敌对者的蔑称,故而吐蕃也包括在内。
参考文献
1、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2、〔加〕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丁俊译,中西书局,2018年。
3、王国维:《不雅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4、〔美〕薛爱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5、谢思炜:《“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6、李鸿宾:《“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期间的两个观点的讲授》,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7、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期间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8、《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9、王永兴:《唐代经营西北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