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纭,
路上行人欲销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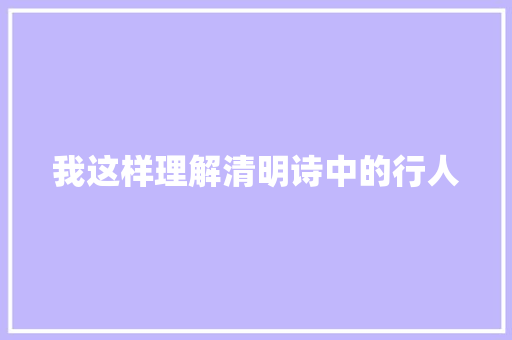
牧童遥指杏花村落。
唐朝著名文学家杜牧的《清明》诗,几千年来人们传诵不衰,从权贵富贾到文人士子甚而是妇孺少幼,都能随口吟来,是一首千古名诗。 清明,又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比较主要的节日。此时,大地复苏,春意盎然。柳绽鹅黄,杨芯吐绿。人们或相约外出踏青嬉戏,赏春景,放鹞子,挖野菜,会朋友;或随家人到祖坟扫墓祭拜,追思先人,哀悼逝者,抚慰心灵。墨客恰在这两天外出,又逢春雨,便写下了这首千古名诗。
《清明》诗作是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第二句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第四句写答话带行动,是整篇的精彩所在。全诗利用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末了的手腕,余韵邈然,耐人寻味。
几千年来,人们对《清明》诗作的注释和欣赏涌现了不同之处,紧张集中在“行人”的身份认同。这是全诗的关键点。有的阐明为作者自己,有的阐明为扫墓者,有的则阐明为踏青嬉戏者。结合全诗的意境,我认为不应把“行人”理解为作者自己,也不是扫墓者或游春者,应理解为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较为得当。
先看一看两种阐明。
踏青嬉戏者
古时出门的工具有限,踏青嬉戏不会行走多远,且对当地的地形路径较为熟习,即便碰着春雨,没有带雨具,抚玩的心绪被毁坏,也不至于“销魂”,更无须向“牧童”问路,探求酒家。因而此阐明从情理上阐明很是勉强。
祭拜扫墓者
虽然从上古期间就有在清明前后祭拜扫墓的习俗,但正式的形成吊拜祖宗的风尚却在明朝,唐朝期间的清明节还是以踏青嬉戏为主。再者说,扫墓者算不上“行人”,勉强为之,也断没有这边哀伤“销魂”、心境凄苦,立时又打听“酒家”,消愁欢愉。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意境大大相径庭。既然是扫墓,间隔不会太远,不会向牧童问路。牧童还在放牛,也解释“雨纷纭”韶光不长,或者下雨也不是很大。“清明时节”解释不一定是清明这一天,这就派出了扫墓者的可能。
以上两种对“行人”身份的认同都难以成立,只有“行人”即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才能同诗中描写的情景相吻合。
“行人”即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春雨纷纭,对上坟祭祖者或踏青游春者影响都不大。但对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就不一样了,由于永劫光的跋涉,又累又饿,还没有带雨具,偏偏遇上春雨纷纭,衣服淋湿了,精神怠倦了,一股凄迷孤独之感涌上心头,就有了“销魂”之态。精神不振,感情不佳,或相爱相思,或惆怅失落意,或暗愁深恨。凄苦疲倦使“行人”产生了急需探求一个酒馆的欲望。歇歇脚,解一解劳乏;避避雨,缓一缓精神;喝点酒,驱一驱寒气。是外地人,以是才“借问”,符合身份特色。“遥指”意味着还要走一段间隔,但顺着牧童所指的方向眺望,杏花开处,隐约可见酒馆门前的酒幌子。全诗戛然而止,别的的情境就由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至于有人提到“行人”即作者自己,我不以为然。诚然,一首作品离不开作者的主不雅观感想熏染,有的乃至便是作者自己的亲自经历,但我以为,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那种把作品中的人物身份等同于作者自己,作品的意境和格调就显得低端了。
综合剖析,这首诗中的“行人”便是“行旅之人”,而非踏青游春之人和扫墓祭拜之人,更不是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