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群体中的一员,其诗歌写作一如其书法,也是有怪异的艺术特色。这种艺术特色,在《竹石》题画诗的第一句中凸显了出来。为谈论方便计,笔者先把全诗转引如下: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一样平常认为第一句有“先声夺人”的效果是对的,而且由于形象感强,后来作为名句被人引用在各种场合。问题是,为何这一句可以有“先声夺人”的效果?难道仅仅由于是处在第一句的位置,是最早发出的声音,才有了“夺人”的效果吗?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实在,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这第一句涌现得没头没脑,在不交代行为主体时,就溘然抛出一个执着武断的行为动作,从而给人设置了巨大悬念。此外,要把“青山”“咬定”,而与之关联的行为主体居然是竹子,这与青山又是多么不匹配、不相称,以是让人在本来的有关动作的悬念中,添加了一份主体与工具不对称的奇崛感。我们当然可以把“咬定”视为拟人化的修辞手腕,也由于是拟人而不是比喻,以是只描写一个动作的同时,无需交代行为主体的名称。这样,由于主体的缺席,就暗含了一种召唤构造,将写作者乃至读者召唤进去,进入一种与描写工具共情的体验中。
相对来说,第二句“立根原在破岩中”,是让描写的奇崛回落到平实中,通过更写实的笔法,把第一句的悬念加以消解、加以阐明。第一句中,不但“咬定”的拟人修辞用写实的“立根”来代替,让想象中的人回到了写实中的物,而且,既穿越漫漫韶光又霸占巨大空间的“青山”,也被“破岩”代替了。换言之,开头那种飞扬的想象,那种“咬定”透出的强大意志力,因此第二句写实中“立根”的自然征象为依托的。“破岩”一词中的“破”,既可以理解为形容词,由于根总是成长在岩石开裂的缝隙中,但也可以作动词理解,是立根的巨大力量,从岩石中挤出裂痕,深深插入个中,终极让竹根和岩石,彼此牢牢地缠绕在一起、咬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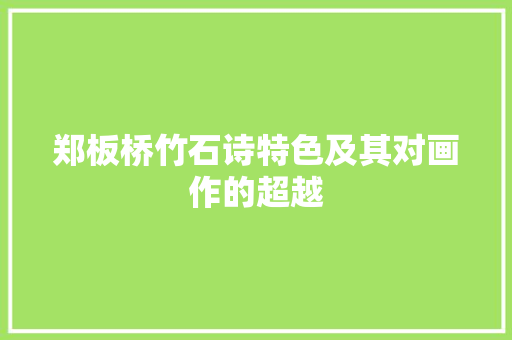
如果说竹子生根的岩石是其依托的、咬合的、乃至融为一体的工具,那么竹子周边也有对立的与之较劲的工具。第三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便是在写一种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保持和坚韧。一方面说,竹子自身的坚韧品性,可以搪塞“千磨万击”;另一方面,由于从岩石、从青山中得到的支撑力量,也使得打击并不能让竹子有所屈从或精力萎顿。这里,作者再次引发了读者的一个悬念,让读者陷入迷惑中,由于它与第一句极为相似,在描写“千磨万击”时,同样没有交代行为的主体。
而在末了一句“任尔东西南北风”中,第三句的悬念得到基本消解,由于在这里,作者交代了,在山上,对竹子“千磨万击”的行为主体,紧张便是东西南北风,可能还有风所携带的飞沙走石或者雨雪冰雹等。但这两句,又不仅仅是悬念和释念的大略关系,而且,这里还有工具呈现或者说视角的深刻转变。当竹子经历了风的千磨万击后,有了一个对竹子自身品质的回顾或者自我核阅的“还坚劲”,犹如在验看中得到了确证,于是把眼力从竹子自身转向外部天下,转向对方,“任尔”不但极其鄙视对方,而且带有相称的寻衅性子,犹如说,既然“我”经历了千磨万击还这么“坚劲”,那么“尔”有什么招数就只管即便使出来吧。如果这样的理解大致不误的话,前一句貌似的自我验看,实在更该当是在向对方示威。
总起来看,虽然作者以竹子和岩石为紧张描写工具,但正好在首句引入青山这一较为高远的名物,结句又带出开阔的东西南北方位,使得这首本可能是比较局促的咏物诗,有了较为开阔的意境。即便东西南北的方位是作为风的存在、作为竹子的对立面涌现的,但不仅仅是其依托的青山,也是其对抗的风所在的开阔天下,才把竹子带向了一个广大高远的天下中。
由于是题画诗,也有人从诗与画的关系来剖析其构造特色:
这首题画诗,前两句交代了画面内容,有整体有局部,展现了画之形。后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画笔无法绘出的内容,而这两句揭示的正是画之“神”。这个“神”也正是作者之画、之诗都要表达的主旨所在。
这样的剖析虽意在揭示诗画间的相同或者差异所产生的互补性,但仔细考虑,又以为其结论是有待完善的。
当初,大画家顾恺之提出“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著名不雅观点,彷佛给绘画表达的“神”,留下了一个有待战胜的难题,也启示墨客从笔墨角度来迂回填补绘画的可能缺憾。但如果据此认为,绘画只是在表现“神”这方面无能为力,而在表现“形”这方面可以大显技艺、没有障碍,实在也是想当然的。
即以前两句言,说前后有一种整体到局部的关系,仅仅是就诗歌本身而言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与所谓的“画面内容”的整体和局部实在是不对应的。由于就作者所要表现的物象而言,竹子和青山的大小比例实在太不相称。只管传统国画中的空间透视关系并不像当代写实画那样严格,但大意还是须要表示出来的。以是,如果画面要让人依稀感到青山的整体,就必须无限缩小竹子,而如果要画出竹子的主体物象,则青山的壮不雅观和气势就难以进入画面中,最多也便是画出竹子依托的一片岩石或者青山一角的大概。事实上,郑板桥的画作,便是这么处理的。笔者看到两幅题写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竹石图,个中一幅,在画面右侧边缘,垂直抹几笔像峭壁的一角就示意了青山,然后从右下角伸展到画面中心的是竹枝和竹叶,霸占了整幅画面的紧张位置,左侧留下较多的空缺,在左上角有题画诗。这样,无论是整体意义上的青山,还是局部意义的与岩石咬合的竹子根部,都没涌如今画面中。另一幅,石头从下边往上延伸一部分,也很丢脸出山的样子。换句话说,单单就物象的形来说,前二句正好是通过诗句,补充了在画面很难呈现的内容,由于画面呈现的是物象的“中不雅观”之景象,而诗中第一句力争展现的宏不雅观与第二句深入下去的微不雅观,实在都超越了画面可能呈现的格局。以是,以为诗歌表达了画面已然呈现的物象之“形”,又进一步表达了画面难以形容的物象之“神”,这样的剖析判断,是失落之大略粗糙的。
更进一步说,纵然画面中表现出了竹对山石的一种依托,但诸如“咬定”这样的拟人化手腕,实在也已经把画面中“形”的取向转成了“神”。而“千磨万击”“东西南北风”,这样的数量词利用和方位叠加,彷佛又让人看到了详细的形。或者说,诗歌表达,是在形的描写中,让人感想熏染了神,而在神的表现中,又让人遐想到形。在充分呈现的措辞魅力中,也让人清楚看到了对绘画固有艺术特色的超越。(詹丹)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