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蝶恋花》
说到王国维,很多人知道他的《人间词话》,知道他提出的“人生三境界”,还知道他末了因此自沉昆明湖的办法离开了人间,却不知他的人生故事不止于此。
王国维生平有过两次婚姻,和那个年代很多夫妻一样,他的婚姻并不是志愿选择,第一段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第二段婚姻是为了有人照顾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可以说都算不上是由于爱情。
因此,有人可能会预测他与妻子的感情不好,婚姻不合。但是,从他留下的词作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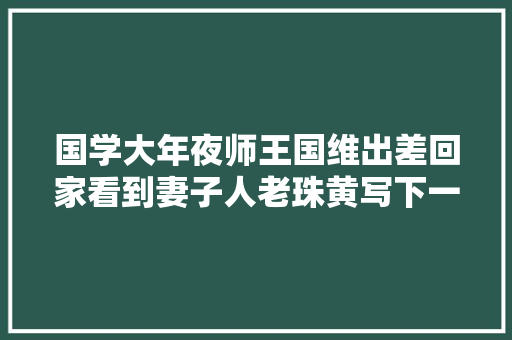
国学大师王国维出差回家看到妻子人老珠黄,写下一词,却流传千古。
王国维
王国维和莫氏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城,家族世代书喷鼻香,王氏家族因在宋代出了抗金英雄,以是在海宁受到当地公民的长期敬仰。这都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少年期间,王国维不仅进了学堂接管了启蒙教诲,而且在父亲王乃誉的辅导下广泛阅读、博览群书,这都为异日后进行国学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本。
1894年甲午中日战役往后,中国的国门进一步被打开,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输入中国,少年期间的王国维也便是在这时打仗到近代前辈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这使他萌发了强烈的追求新学的欲望。
然而,由于那时父亲并不支持他外出游学,以是未能成行,但他依然时时关心时势,纵使在家乡做家庭西席,却一贯不能安心。这也是他多次参加科举始终未及第的一个缘故原由,他资质聪慧却志向不在科举,而是神往新学。
奇迹暂时不成,那就先成家。
王国维与莫氏的婚约,实在早在他14岁的时候就定下了。
父亲王乃誉不同意王国维出国紧张是考虑家族传宗接代的大事,在父子双方相互妥协之下,父亲提出一个条件:王国维必须先成亲,再出国。
1895年11月,18岁的王国维与第一任妻子莫氏成婚,这么早结婚是由于他求学心切。
1898年,父亲陪同王国维到了上海,他进入了《时务报》报馆事情,在那里一边学习日文,一边学习英文、数理等课程。
1900年,他终于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在罗振玉的帮助以及两位日本老师的帮助下,他于当年底到了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
罗振玉
自王国维留学开始,他的生活就四处奔波。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分居生活。中间王国维也曾回家,只是在家待的日子都不久。
不过,在十几年的分居生涯中,王国维一贯坚持操守,没有与任何女子发生过暧昧不清的事情。而且,只要一有空闲,不管身在何方,他都会回家看望妻子,看望三个孩子。
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两个年轻人在此后的年月中,虽不能惜惜相伴,却情意渐深。
陆续几年,王国维和妻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一离开家,家里的就只剩下莫氏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
丈夫不在家的日子,家中非常凄清,莫氏昼夜操劳家务。
对付妻子莫氏,王国维究竟有没有产生过爱情,这首《蝶恋花》或许能够给出一些端倪。
公元1905年的春天,四处奔波的王国维回到了家乡海宁,夫妻团圆,本是一件欣喜的事情。可是,莫氏向来体弱,又是范例的贤妻良母,一个人要操持家务、照顾公婆、拉扯三个孩子……几年过去,她看起来十分干瘪,尚不敷三十岁已经显出苍老。
丈夫远行,她也没有再打扮自己的心思,加上昼夜思念丈夫,人变得更加干瘪了。
1906年农历四月,王国维因病返返国内,五月回到家中养病。夫妻久别相逢,本来是一件很让人欢畅的事情。丈夫归来,对莫氏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她都没来得及精心装扮打扮,急急地出门欢迎丈夫。
王国维乍一瞥见妻子的时候,愣住了。异日思夜想的妻子怎么变成这般样子容貌了,明明才二十多,怎么明显显出了苍老和干瘪。
他忽然明白了诗词中所述的女子: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岁月是把杀猪刀,岁月是个神偷,不知不觉统统都变了,它改变了女子的容颜,换上了白发,拿走了你的年轻力壮……统统还来不及好好珍惜,就已经溜走了,只是想想,都会以为很伤心。
但令人更伤心的是,光阴一点点侵蚀了你所爱的人的容颜,让她犹如凋零的花儿一样平常,仙颜不再。
王国维不禁万分感伤,写下《蝶恋花》。
整首词充满伤感。上片首句“阅尽天涯离去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直抒胸臆,不是他不恋家,可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奇迹追求,他不得不长期离家,离去给他们夫妻带来了无尽的痛楚,既是感慨离去,也是道出长久的心声。
真的是“思君令人老”,“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一个句子中两个“辞”字,王国维用类比的办法感慨妻子容颜逝去,犹如枝头的花瓣飘零,都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规律。虽然明白不可阻挡光阴流逝,但依然忍不住流露无奈和伤感。
整首词虽然没有直接书写他与妻子的爱情或者对妻子的赞颂,但却字字含情,表达着他对妻子的关怀。夫妻二人虽常年分离,却各自珍惜,洁身自好。可见王国维极有担当,也表露他对妻子的感情至深,他懂得妻子为家庭的付出,懂得戴德。
大半精力付诸学术
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中国诗词最辉煌的时候,宋代之后的此人,再难达到两宋的高度,是词人们创造了两宋的辉煌,也是那个时期造就了词人们的精彩,后世的词人,再也没有天时地利能在艺术性和表现手腕上到达两宋词人的高度了。
但是清末的王国维却做到了,他不仅是国学大师,同时创作出来的词也是可以媲美宋词。
王国维家中本事以人丁茂盛,包括他在内有六子二女,但是接连遭遇家庭变故,三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是在父亲和继母的照顾下终年夜的。
1906年,刚迈入而立父亲去世,享年60岁不到一年。
不久之后,也便是在王国维给妻子写下《蝶恋花》后不久,1908年,莫氏就因产褥热去世了,才不过34岁。
妻子一走,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那首词竟是一语成谶。
屈原《离骚》中写:“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白居易在《简简吟》里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就连杨绛师长西席也曾在《我们仨》里写道:“人间没有纯挚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久。”
自古至今,中国文人感慨美好的逝去,光阴如梭,流露的感情都是那么相似。
而后一年多,1908年,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去世了。
大概是这些人生打击,在贰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悲痛,使得他的诗词中总带有一种婉约的悲情。
王国维的三个儿子中,他最看重的便是宗子王潜明,而宗子也不负众望,曾通过喷鼻香港大学的高档考试,本有大好的前景,可以远渡重洋去英国留学,可他却选择了去海关事情。
更让王国维惋惜的是,宗子与他的石友罗振玉之女罗孝纯结婚没几年,居然病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惜,失落去爱子之后,罗振玉溘然带走了女儿,与王国维断绝联系,让他更加悲痛。
幼年失落恃、壮年失落怙、丧妻、丧母、丧子,乃至与石友断交……人生不过才四十多年,各种大起大落的悲痛,王国维都经历了。
他不但是经历了,还把心中的感情都融在了诗词里,无论是意境,还是写作手腕,完备可与宋词相媲美,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家庭的变故、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王国维更加重视学术奇迹,使他在学术上不断向高峰迈进。
数十年间,时局动荡,忧心国事,烦恼家事,王国维的事情也多次变动,然而无论身在何处,面临着若何的环境,王国维都从未停滞其学术研究。
他先后写出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许多蜚声中外的国学专著。
他还在著作《人间词话》中提到了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干瘪;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顾,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他做学问中感悟的三种境界,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经历的三种境界——从立下目标,到为其无怨无悔,再到与成功的不期而遇。
与其说是尽力所得,不如说是努力到一定程度之后任天由命,有一种沉着和复苏的意味。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在报社事情时,接管了泰西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力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可以说在当时是一部眼力长远、中西结合的一部作品。
自沉昆明湖
生平无心科举的王国维,在46岁时,清朝已经覆灭之后,却选择做了溥仪的文学侍从,直至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而告终。向来无心仕途,也齐心专心追求新学的王国维,为何会为一个已经覆灭王朝的废帝做官,旁人不得其解。
溥仪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位才子,却毫无前兆的选择了自尽,对付他的自尽,至今仍旧是个谜。
1927年,中国正处于风云激荡、新旧交替、场合排场突变的历史关口:北伐风起云涌,高歌年夜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些人奋力抗争,尽显风骚;还有一些民气灰意冷,自身命运宛如彷佛流水浮萍,无力自主。
1927年的初夏,国学大师王国维彷佛也走到了一个死活决议的人生关口。
近一年来,宗子病故,亲家失落和,国家场合排场动荡不安,诸多成分让原来就心境忧郁、敏感的王国维更加寡言少语,自尽已经是思忖良久。
虽心意已决,王国维却并无半点流露,或许他不愿身边的人担心。
1927年6月1日,附近端午,清华国学院的师生都忙着毕业事宜,师生们相互作别,老师给学生题字,大家彷佛都没想起来来过节的事。
那天中午,清华国学院举行师生叙别宴会,王国维在席间一贯沉默不语,但是大家也并未在意,由于他一贯寡言少语。
那天下午,王国维本是到陈寅恪家闲谈,不久听说有学生去他家里拜访,于是告辞,回到家中和学生们畅谈。
陈寅恪
越日早上,统统如常。
他照常起床洗漱早餐,然后至清华国学院,先是让研究院的工友到家中将他遗忘在家的学天生就册带至办公室,随后与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聊起放学期招生事宜,谈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在那之后,王国维向侯厚培借得五元纸币,在清华校门口坐上一辆黄包车前往颐和园。
到颐和园大约是上午十点,初夏的颐和园,植物郁郁葱葱,王国维穿过长廊,在鱼藻轩容身良久,逐步地抽完了末了一支烟之后,纵身一跃跳入昆明湖。
王国维自沉入湖之时,头先入水,口鼻均为污泥所堵塞,全身尚未湿透便气绝身亡。颐和园中园工听闻有人落水,赶来施救,急忙将王国维从水中捞出,然却早已气绝而逝。
他在自沉之前留下一封遗书,开头有这么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去世。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对付他的去世因,至今是个谜,人们有各类预测,却没有定论。他走得很干脆,却让众人来不及反应。
或许,他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活得太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