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一样平常把书信写在洁白的绢帛上头,绢帛长一尺旁边,称为尺素,以是书信在古代被称为“尺素书”。洁白的尺素常结成双鲤之形,以是又被称为“鱼书”,授予了人们美好的生活情趣。汉代无名氏的《饮马长城窟》诗云: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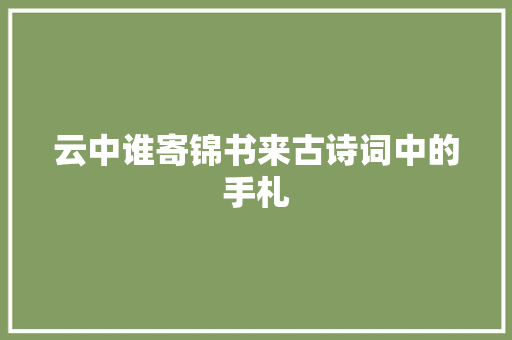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唐代墨客李治的《结素鱼贻朋侪》诗云:
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
要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
宋代秦不雅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词中写道:“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都是指的鲤鱼和书信的关系。鲤鱼腹中当然没有书信,那只是一种生动而美好的比喻,但弥漫于字里行间的那种亲情、交情和爱情,千百年来让我们回味良久。
除了鲤鱼,书信在古代还常和鸿雁联系在一起,这源头,最从前夜概起源于苏武牧羊时“鸿雁传书”的故事。以是在古诗词中,书信常常被古人合称为“鱼雁”。唐代墨客韦皋的《忆玉箫》诗云:
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
长江不见鱼雁书,为遣相思梦入秦。
杜牧在《赠猎骑》书中写道:“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宋代词人晏几道的《蝶恋花》:“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都是取的这层意思。
纸张发明往后,人们制作了一种小巧精美,专门用来题诗和写信的纸张——“笺”,并以此作为书信的又一代称。宋代词人晏殊在《蝶恋花》中写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传说唐代幽居成都邑郊浣花潭畔的女墨客薛涛特殊长于制作一种赤色小幅诗笺,并以这种赤色小笺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因而驰名文坛,当时人称“薛涛笺”或“浣花笺”。唐代墨客李商隐有诗赞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
书信,满载着深情厚谊,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朋友、恋人犹如面聚,因而显得特殊宝贵。唐代墨客李绅《端州江亭得家书》诗云:
雨中鹊语喧江树,风处蛛丝飏水浔。
开拆远书何事喜,数里手信抵千金。
在墨客眼里,数里手信代价高达“千金”!
语极夸年夜;然而,比起老杜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李绅的这个比喻彷佛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杜甫中年后遭逢战乱,常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兄弟四散,居无定所,“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在那种情形下收到家书,珍惜和宝贵之情自不待言,“家书抵万金”恐怕也不能完备算作夸年夜之语。
山长水阔,音信千里,如果能收到远方的来信,那种激动之情确实是可以想见的。南北朝时的南朝墨客庾信因故滞留北方,某天,当他收到南方老朋友的来信时,一韶光激动得泪如雨下:
《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跟他相似的还有唐代墨客元稹,看看他在《得乐天书》诗里怎么写的吧: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平凡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既然有人如此期盼远方的来信,那么,朋友啊,你就多写几封书信吧。远居边塞的唐代墨客岑参便是这样叮嘱他长安的朋友的:
《玉关寄长安李主簿》
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
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千言万语又岂止是一两封书信可以尽言的?即便写好了书信,待发未发之际,仍会以为还有太多的话没来得及写上,因而大费犹豫。比如唐代墨客张籍,他的《秋思》诗写道: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
俱往矣,现如今随着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发达,“天涯如比邻”已经不是一句空话,因而最近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书信日渐衰落,正在逐步退出我们的生活。校阅阅兵古人诗词中这些关于书信的描写,忽然没来由地生出了几许怅惘。韶光荏苒,世异时移,惟愿凝聚在古人书信中这些难忘的亲情、交情和爱情不随光阴而流逝,熠熠发光,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