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明显觉得没有“怼”过瘾,于是决定把这件事写进他的著作。然后嘱咐门下的信徒,承其衣钵,怒“怼”惠子二千余年。
后世“怼王”从中受到启示,早已不知足于仅仅是利用方言和汉字来“怼人”了。韶光来到了光耀万代的大唐,两位“怼林”高手横空出世,一个叫李白,另一个叫杜甫。
李白说:写文章“怼”人不给力,编成歌词,唱着“怼人”更狠。千百年后,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唱我的“歌词”,每唱一遍,都是在替我骂人!
杜甫则说:呵呵哒,写一首歌词有什么意思呢?要写就一次写六首!
我一边骂,还一边给他们讲道理。所有听过这六首“歌”的人,都夸我骂得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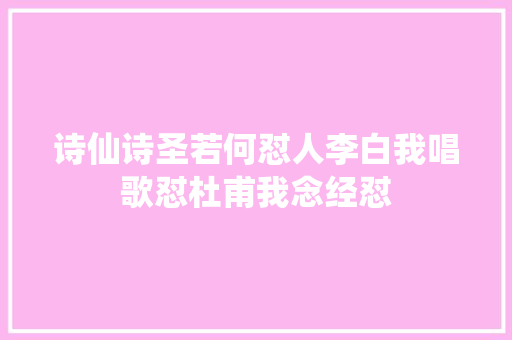
谁假如胆敢说我骂得不对,那么就对不起了,原诗里直接摘出一句话,直接怼他脸上,“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上李邕》——唐·李白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众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相传,李白这首诗是在他未出四川之前写的。李白十八岁的时候,听说渝州新上的刺史李邕是一个爱才之人。他常常在官邸开宴会,广交各路英雄,于是李白就想跑过去想交个朋友。
也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概是由于李白的口气有一点点大,然后遭到了排挤。于是,少年李白怒写了一首诗说:
有朝一日,我会像大鹏一样乘风高飞,平步青云九万里。如果风溘然停了下来,我跌进了大海,我的身体依然能搅得沧溟之中海水翻滚。
有人想问:凭什么?就凭我伟大啊!
我在天上是大鹏鸟,落到海里就变成了鲲。我便是这么能耐,嘿嘿嘿。你们由于我的言行独特,以是一听到我讲话就大笑。《老子》曾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敷以为道,说的也便是你们这些“下士”了。孔子都说“后生可畏”,为啥你们不听他老人家的话呢。看来圣贤书也是白读了!
“怼王”李白凭借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势,一边唱一边“怼”,唬得所有人一愣一愣地。这一首诗内容看似直白,但是实际上却是气势非凡。
诗中接连引用《老子》、《庄子》中的典故,借儒家的先师孔子来嘲笑那些看轻他的人是有眼不识泰山,算是做到了情理交融。
“怼”人有时候便是要“先声夺人”,上来便是一声“呔”。然后靠着诗仙的才华,大鹏终有展翅日。只差一个机会,我就能乘风奋飞九万里。在天为鹏,在海为鲲。
看一看,这样的想象是多么地俏丽,特殊适宜编成“歌”来唱,而且还适宜千古流传,成为后世那些“怼林”中人神往的目标。
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在人们眼中一贯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诗圣”,敢称“贤人”,那么肯定是君子端方,绝不会口出恶言。但是事实上,杜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他实在非常会“怼人”。
《旧唐书·杜甫传》记载,“(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意思是说,杜甫当年流浪到成都,投靠好友严武,在严武的部下当一名幕僚。
结果有一回他喝高了,居然跳到了严武的床上,指着他的鼻子骂:严挺之怎么生了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呢?当然,这都是别人的八卦。
不过,他曾经写了一组七言诗,便是专门“怼人”的,非常有名,那便是《戏为六绝句》,原文如下:
《戏为六绝句》——唐杜甫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先哲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文字,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先哲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首诗大意是说:
庾信的文章,到了晚年之后就变得更加成熟了。然而,很多人却只是嘲笑他文章华美,只看重辞藻,这完备便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们完备看不到庾信后来笔下的凌云之志,与纵横开阔的气候。如果庾信还活着的话,一定会以为:哎呀呀,真是“后生可畏”啊!
然后杜甫说,初唐四杰行文风格骈丽,以是受到今人的攻击。这些人便是一叶障目,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完备是无理取闹。
对付这种不讲道理,还妄下结论的家伙,我只有祝他被历史埋没了。而四杰的文章,一定会像长江、黄河一样,万古流芳。
接着,他进一步借别人调侃初唐四杰的话来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四个人的文章不如汉魏,而靠近《诗经》、《楚辞》,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的文章就像龙和虎背上的纹饰,华彩天成。他们的人和他们的文,穿越了历史、地理的界线,经受住了韶光的磨练,才来到你们的面前。
你们这些人,才华也不如他们,当中更没有一个精彩的货物。还有一些人,表面上看似主见要学《诗经》、《离骚》》,结果背地里又去学习六朝那些“悲翠戏兰苕”之类句子。
不睬解文章的立意,不具备超越古人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本色还这么低下,怎么能够像在碧海中骑鲸遨游一样,进行文学创作呢?
学做文章,既不能菲薄今人,同时也该当爱戴古人,清词丽句与言之有物并不相抵牾。你们既然想学屈原和宋玉,有种就学到和他们并驾齐驱,为啥后来又步了齐梁艳诗的后尘呢?
自己没有达到古人这种高度的本事,就不要跑去乱疑惑古人的水平!
创作不能因循守旧,一个抄一个,你们谁是谁的老师?裁掉那些守旧因循的“伪体”,老诚笃实去学习《诗经》、《离骚》是可以的。与此同时,也该当客气学习别人的文章。不怕师傅多,这些人统统都是我们的老师。
杜甫这一组七绝诗,创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当时正是他在严武的部下当幕僚的时候。有人认为这组诗是他在替庾信和初唐四精彩头,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替自己说话。
大概是由于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的创新,弹劾遭到了一些人的嘲讽。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组诗,借着帮“古人”说话,来“怼今人”。
当时唐朝的诗坛优势行“复古风”,有人看不惯庾信和初唐四杰那种骈丽的文风。但是,事实上庾信和王勃等人在后期,已经开始主动进行文章的改革了。
然而,那些无知的人们,还是拿着上述这些人从前的诗文来品头论足。文辞华美又怎么了呢?《论语》中说:“文质彬彬”才能相得益彰!
有好的内容,也要配上好的措辞修辞。以是,杜甫怒怼了当时文坛上那种“厚古薄今”的歪风。他通过反讽、比喻、说理等修辞办法,怒怼“今人”不能以发展的眼力看待庾信的进步。
同时,他提醒所有的人把稳:初唐四杰的文章,是经由了韶光磨练才流传下来的。在这一段中,杜甫提到了“龙文虎脊”,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刘勰的《文心雕龙》。
后者在书里的《原道篇》中曾经提到:“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这些都是大自然授予动物身上的纹理,是最天然的,也符合“道”的文。
再说,评价一个人文风的利害,不能分开时期背景。在后面,他又嘲笑这些“今人”不接管文章改革,只会一味地主张仿古、摹古。
个中“尔曹身与名俱灭”一句,更为“怼界”千古绝句!
结语
但凡有哪位名人遭到了攻击,他的支持者只要祭出此句名言,就可以做到“一击必杀”!李白是一个自傲心和自傲心都非常强的人,而且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才华。以是他在《上李邕》中引经据典,骂得那叫一个畅快淋漓。
杜甫作《戏为六绝句》的时候已经49岁,但是看样子火气也还是不小。他一边讲理,一边“怼人”。以是,他写下了一组七言诗来“怼”当时文坛上的“歪风邪气”。
他用“尔曹身与名俱灭”、“历块过都会尔曹”和“才力应难跨数公”等数句“明骂”,再用“不觉先哲畏后生”、“若看翡翠兰苕上”、“窃攀屈宋宜方驾”“暗讽”,把“今人”完备贬成了渣渣。
在花式“怼”人的同时,杜甫还以这组七言诗,不仅首创了古代文人“以绝句论诗”的先河,而且这一组诗中还包含了一套比较完全的杜甫诗歌创作理论。
李白的《上李邕》虽然气势恢宏,但是表达的中央思想无非是“莫欺少年穷”。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则不一样,他是一边“怼人”,一边也在给这些人讲道理。
以是,无论是从诗歌本身的造诣来看,还是从杜甫那句经典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网络骂战中的“杀伤力”与“控场能力”来看,杜甫以诗“怼”人的本领,都是远超李白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李白这首诗虽然主题迂腐,但是毕竟在“怼”人的同时,显得很有诗意。而杜甫这一组诗看重说理,更像是把李白的“唱歌怼”,发展到了“念经怼”。
“怼人”的实质,还是属于一种“干架”行为,以是到底是“唱歌怼”更好呢,还是“念经怼”更强呢?这个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而且很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也不会写古诗。以是他们既不能学庄子著书立说来“怼”,又不能学李白“唱着来怼”,更不能学杜甫“念着经来怼”。
以是,他们在“怼”人的时候,一样平常都只能“叉着腰、跳着脚怼”,或者是“蹲在地上、画着圈圈怼”了。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