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刘禹锡 〔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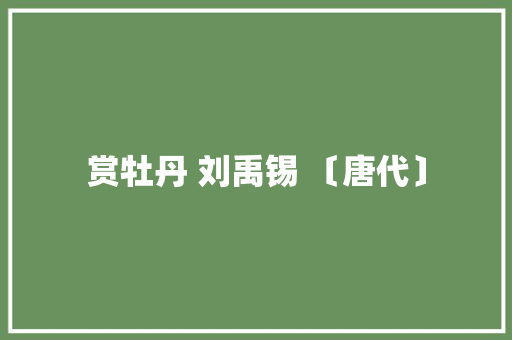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译文及注释
译文庭前的芍药妖娆艳丽却缺少骨格,池中的荷花清雅清洁却短缺情韵。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到了着花的时令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全体京城。
注释牡丹:著名的不雅观赏植物。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后以木芍药称牡丹。一样平常谓牡丹之称在唐往后,但在唐前,已见于记载。庭前芍药:喻指宦官、权贵。芍药:多年生草本植物,属毛茛科,初夏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妖无格:妖娆俏丽,但缺少标格。妖:艳丽、妩媚。格:骨格。无格指格调不高。芙蕖:即莲花。国色:倾国倾城之美色。原意为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此指牡丹富贵美艳、仪态万千。京城:一样平常认为是指长安,但刘锬编的《咏花古诗欣赏》、鲍思陶等编的《中国名胜诗联精鉴》以及谢明等编的《历代咏物诗选读》认为此诗中的京城是指洛阳。
赏析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墨客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好的花卉,然而墨客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不雅观赏代价的花卉,但听说到了唐代武则天往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不雅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清洁的面孔涌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由于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不雅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不雅观赏代价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好。《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快场面,而同期间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以是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韶光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革。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往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低落,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以是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常常以清高清洁面孔涌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不雅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以为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栽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好,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清洁,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轶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料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以是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由了负责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响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忙相告,争先抚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个中又深含了墨客丰富的审美思想。墨客没有忘却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壁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墨客用拟人化和陪衬的手腕,奥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