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柳永只会呆在青楼,只写卿卿我我的闺阁之乐,出些《混在青楼的日子》那样剧情狗血的脱销书,事实上,柳永是个伟大的旅行家。流落江湖几十年,除了很少回老家武夷山,其足迹遍布北宋各地。每到一地,必去稽核风土名胜,光顾风月场所,对当地的文化娱乐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辅导。杭州、扬州、苏州等大城市,就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墨宝。如他传颂至今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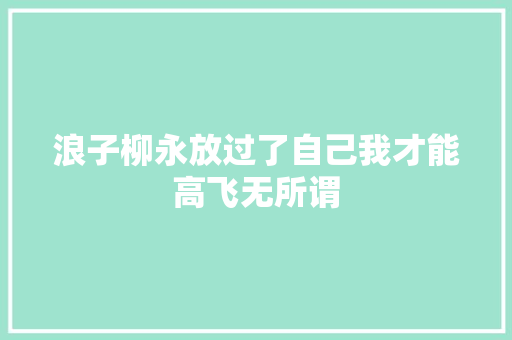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是至今为止杭州最好的广告文宣之一,足以把苏东坡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合适”比下去。看这首词的风格,不像婉约派,倒像是豪放派了。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的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可谓“承平气候,形容曲尽”。
词的上阕紧张写杭州城市的繁华。特殊是“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与苏东坡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阕写西湖,“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让人有立时去西湖一游的冲动。金主完颜亮也是这样想的,相传金主完颜亮听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往后,便倾慕钱塘的繁华,从而更加强化了他侵吞南宋的野心。我估计这个故事,是在南宋的哪个天子授意之下编出来的,紧张是推脱打不过金国人的任务。故事虽不可信,但也解释了柳永词的杀伤力。
末了一段紧张是礼节性拍马。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一派暄赫声势。一位威武而又风骚的地方主座,饮酒赏乐,啸傲于山水之间。“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意思是说,祝您早日升官发财。
柳永是个多情种子,他的词不会专美杭州。他还歌咏过苏州、扬州、成都、洛阳等,为宋代都邑繁荣留下了形象的画面。他对宋代城市文化的描写,对后世的影响,不比张择真个《清明上河图》小。
柳永生平流落辗转,每见官场之阴郁,便牵起自己的一腔凄凉,每见歌女之可爱,就会多几个红颜心腹。他一贯在离去,离去总是伤感的,他一贯在彷徨,内心总有很多悲慨。因此,不管是他的离去还是羁旅行役之词,都能击中我们内心深处最优柔的部分。如《雨霖铃》:
寒蝉悲惨,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仕女伤春,壮士悲秋”,秋日总会给人以莫名的惆怅之感。在离去之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风住雨停之时,便是我们的离去之期。当代墨客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深情地写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同样是离去,徐志摩是洒脱的,但柳永是伤感的。都门寒帐之外,美女为柳永送行。二人执手相望,泪水横颐,这是一个风情万种的时候。那船老大却不解风情,大声催着上船。这场景,像极了当代电影中恋人在火车站话别的桥段。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谁知我今夜酒醒时身在何处?怕是只有在杨柳岸边,面对凄厉的晓风和黎明的残月了。“问世间情为何物”?我柳永一腔苦楚向谁诉?
柳永念念不忘的功名,终于在五十岁旁边成为现实。虽然“及第已老,游宦更迟”,他仍旧表现出极大的政治激情亲切和干劲。很遗憾,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他,只能辗转僻州小县,屈居下位,最高官职做了个屯田员外郎,估计相称于专管农业技能的处级干部,以是人们都叫他“柳屯田”。这样的人生显然很“拧巴”,就好比是一个著名艺术家,你非让他去种地,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这种事情,在后来的“文革”中也发生过,大批知识分子被关了牛棚,下放劳动,对宝贵的人才资源来说,切实其实是暴殄天物。不过柳永的优点在于,他永久留一条后路给自己,失落败了不要紧,从官场再次转战情场,连续在红裙翠袖的温顺乡中麻醉自己。
大约在1053年,66岁的柳永去世了。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乃至连棺材钱都没有留下,宋朝婉约派大师去世得极其悲惨。一班名妓们凑钱安葬了他。柳永去世后没有亲族祭奠,每年的清明节,也是这班名妓粉丝相约到他坟上祭扫,相约成为习气,习气演化成习俗,时人称之为“吊柳永”或“吊柳会”。
柳永用他生平的经历见告我们,谁说只有做官才能青史留名?历史上做官的人不可胜数,但真正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有几个呢?除了屈原的自尽,为我们带来端午小长假,我们对他顶礼膜拜之外,还有谁会像柳永一样,创造了歌女们行业性的纪念日?娱乐行业的那些姑娘们,在看了我的文章之后,也请你们在清明时节,遥想宋朝,为天才浪子柳永奉上哀思和祝福吧。
柳永的生活虽然不堪,时人对他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宋词的贡献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只管他生平不合于流,操行为正统士大夫所不齿,但毕竟词论家们不能睁眼说瞎话。李清照说柳词,虽“词语尘下”,但“协音律”,苏东坡虽然看不起柳永,但读到《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时,也由衷地惊叹“不减唐人高处”。
柳永的生平极其坎坷。“三十功名尘与土”,仕途潦倒;“八千里路云和月”,四海流落。以至于末了葬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有人说是在湖北襄阳,也有人说是江苏镇江,反正他不管葬在哪里,却实实在在葬在了历史深处、宋词的高处。今人杨坤唱得好,“错与对,再不说得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柳永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他丧失落了仕途,却赢得了宋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