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一点残红欲尽时》由周紫芝创作,当选入《宋词三百首》。这首词写秋夜雨中怀念情人。上阕开头两句写室底细况,接着写室外环境。残灯如豆,梧桐秋雨,唤起客子的离愁。下阕开头三句转忆当年两人一起调瑟操琴,同唱新曲,互为心腹的愉悦。今夜“风雨西楼”,孤寂一人,今昔比拟更觉凄孤。
【原文】
《鹧鸪天·一点残红欲尽时》
作者:周紫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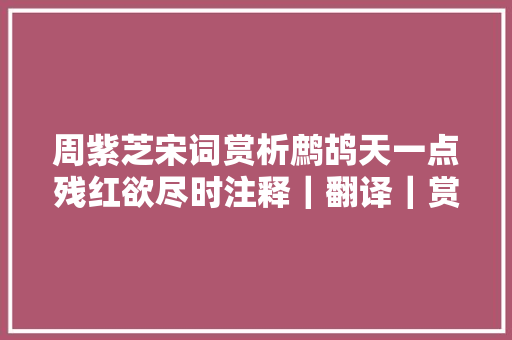
一点残红欲尽时,乍凉秋气满屏帏。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
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如今风雨西楼夜,不听清歌也泪垂。
【注释】
①残红:此指将熄灭的灯焰。
②“梧桐”二句:化用温庭筑《更漏子》词:“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调宝瑟,拨金猊,地时同唱《鹧鸪词》。宝瑟:指琴。金猊:喷鼻香炉。
③调:抚弄乐器。
④金猊(ní):狮形的铜制喷鼻香炉。这句指拨去炉中之喷鼻香灰。
⑤西楼:作者住处。
【翻译】
一点残灯将尽,景象刚刚转凉,秋寒的意味充满室内。已经到了半夜时分,表面正不才雨,梧桐叶片落下的水声更加凄冷。叶叶声声更增加我伤感的感情。我回顾起当时的情景,她调拨弹奏着琴,我去拨动金猊,那情景真是幸福难忘。我们俩一起齐唱鹧鸪词,绵绵情深直到天明。可是如今,独在西楼听着满夜的风雨,我不禁黯然消魂。
【赏析】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首因听雨而有感。出发点夜凉灯残之时,次写夜雨,即用温飞卿词意。换头,忆旧时之乐。“如今”两句,折到现时之悲。“不听清歌也泪垂”,情深语哀。
这首词写秋夜怀人,回环婉曲,情景相生,而吐语天成,毫无着力痕迹。词中抒怀主人公是男性,怀念的工具是一位歌女 ,因久别相思而为之“泪垂”。孙竞评周词曰:“清丽婉曲。”移评此词,亦可谓中肯之语。
上片首句“一点残红欲尽时 ”,写夜静更阑,孤灯将灭的景象。不说孤灯残烛,而说“一点残红”,盖油将尽则焰色暗红,形象更为详细。写灯,则灯畔有人;写残,则灯欲尽而夜已深;把稳到“残红欲尽”,则夜深而人尚无眠,都可想见。到下句“乍凉秋气满屏帏”,则从觉得凉气满屏帏这一点上进一步把“人”写出来了。“乍凉”是对“秋气 ”的润色词,虽然是从人的觉得得出,但“乍凉秋气”四字还是对客不雅观事物的描述,到了“满屏帏 ”,这才和人的主不雅观感想熏染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凉气满室而且悲惨满怀的境界。以上两句,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觉得,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以下两句再作进一步的铺展——“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上句彷佛是笔锋一转 ,由室内写到室外了 。但如细加体味,这两句原是一个意,是透露出男主人公心中的离愁的。离愁本是存在、潜伏着的,由于听到了“声声”,而触发,而加浓了。这“声声 ”,是来自楼外的“梧桐叶上三更雨”。梧桐”一句,是为了渲染男主人公心中的离愁别恨而设置的,所谓“因情造景”者是。这两句的落脚点仍是那听到了“声声”的人,即楼内人,写他的听雨心惊,这还是写的“室内 ”。两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词“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作者把“滴到明”的意思先寄在“ 残红欲尽”处,又把“叶叶声声”同“别离”即离情画了等号,也还是有点新意。词的上片把人的感情写得如此深奥深厚,却未用明着道出,而是于平淡之语中隐含款款深情。
下片回顾中的欢快之音与上片离去后的悲惨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光鲜比拟 。过变承接“别离”意脉,写出昔聚今离、昔乐今愁的强烈比拟,主人公的感情波澜起伏更大。“调宝瑟”三句是对昔日欢聚的追忆,由“那时 ”二字表示。“调宝瑟”是奏乐,“拨金猊”是焚喷鼻香 ,“同唱鹧鸪词”是欢歌,三件事构成一个和谐的生活场景,也是艺术场景。从中交代出男主人公所以为之产生离愁别苦的那人是歌女身份,两人有过恋爱关系。当时他们一个调弦抚瑟,使腔调谐和;一个拨动炉喷鼻香 ,使室中芳暖 。在这无限温馨的情境中“同唱鹧鸪词”,此乐以是使他至今不忘。“金猊”是铜制的燃喷鼻香用具,成狻猊形。陆游《老学庵条记》卷四记 :“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盖喷鼻香兽也。故晏公(殊)冬宴诗云:‘狻猊对立喷鼻香烟度。’”“鹧鸪词”当指歌唱男女爱情的曲子 。“鹧鸪”在唐宋词中大都以成双欢爱的形象涌现。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双双金鹧鸪”,李珣《菩萨蛮》中的“双双飞鹧鸪”,顾夐《河传》中的“鹧鸪相逐飞 ”,都是作为男欢女爱的象征。本词用“鹧鸪词”作为“同唱”的内容,其用意也在于此。这个“同”字既揭示了主人公与“别离”者的关系,还追忆了温馨欢快的昔聚之情,同时也就开启了今别孤单痛楚之门,盖言“那时同 ”,则“如今”之不“同”可知矣。于是词笔转回到“如今风雨西楼夜”的情境,连贯上片。当此之际,许多追昔抚今的感叹都在不言之中了,只补一句,便是“不听清歌也泪垂 ”!
本来因有离愁别苦而回顾过去相聚同歌之乐以求缓解,不料因这一温馨可念的旧情而反增如今孤栖寂寞的痛楚。这个“泪”是因感念昔日曾听清歌而流,如今已无“清歌”可听了,而感旧的痛泪更无可遏止。为什么?如今身处“风雨西楼夜 ”,自感秋夜之悲惨 ,身心之孤独“泪”是因此而“垂”的。
“也泪垂”的“也 ”,正是从上句派生出来的,当然离不开昔日欢娱而今冷落这个背景。“不听清歌 ”四字,正是概括地写出了这个背景。末端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迁移转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发人寻思。
此词条用昔与今、悲与喜、正说与反说两比较照的手腕,表情达意委婉弯曲而又蕴藉层深。全词通体浅语深情 ,虽“江平风霁、微波不兴,而彭湃之势,澎湃之声,固已隐然在个中。
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想熏染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想熏染更富传染力量。所谓“叶叶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绪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生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叶叶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顾,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喷鼻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旧是音响,不过这是回顾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顾中的欢快之音与上片离去后的悲惨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光鲜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迁移转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面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民气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往后,常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影象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叶千声皆是恨”的情形下,纵然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迁移转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革,以悬念办法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引言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系统编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次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相逢,本为久别再见,该当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落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迁移转变词意,把惊喜疑惑的神色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响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平凡。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迁移转变,有感情起伏。
两者比较,这首词所采取的手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腕,做到委婉弯曲而又蕴藉深奥深厚,确乎从小晏词变革而来。特殊是末端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迁移转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寻思。
【赏析】
周紫芝的《竹坡词》“清丽婉曲”。这首《鹧鸪天》可以安得上这个评语。词中以今昔比拟、悲喜交杂、委婉弯曲而又缠绵蕴藉的手腕写雨夜怀人的别情。上片首两句写室内一灯荧荧,灯油将尽而灯光转为暗红,虽说是乍凉景象未寒时,但那凄清的气氛已充斥在画屏帏幕之间。这里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觉得,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此系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想熏染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想熏染更富传染力量。所谓“叶叶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绪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生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叶叶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顾,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喷鼻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旧是音响,不过这是回顾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顾中的欢快之音与上片离去后的悲惨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光鲜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迁移转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面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民气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往后,常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影象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叶千声皆是恨”的情形下,纵然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迁移转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革,以悬念办法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引言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系统编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次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相逢,本为久别再见,该当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落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迁移转变词意,把惊喜疑惑的神色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响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平凡。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迁移转变,有感情起伏。
两者比较,这首词所采取的手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腕,做到委婉弯曲而又蕴藉深奥深厚,确乎从小晏词变革而来。特殊是末端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迁移转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寻思。
【作者先容】
周紫芝(1082—1155),南宋文学家。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安徽宣州市)人。绍兴进士。1145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为礼、兵部架阁笔墨。1147年(绍兴十七年)为右迪功郎命令所删定官。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1151年(绍兴二十一年)出知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退却撤退隐庐山。曾向秦桧父子献谀诗。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也能词,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刻意雕琢痕迹。著有《太仓稊米集》七十卷、《竹坡诗话》一卷、《竹坡词》三卷。存词150首。
【宋词英译】
Partridge Sky
Zhou Zizhi
Red flames of burned-up candle shed flickering light,
In chilly autumn air are drowned the screens in view.
The drizzle drips on plane trees at the dead of night,
Drop by drop, leaf on leaf reminds me of your adieu.
We played on zither dear,
Incense from burner rose,
Singing the lovebirds’ song, together we stayed close.
Tonight wind and rain rage in western bower drear,
How can I not shed tears
When none sings to my ears!
【词牌简介】
《鹧鸪天》,词牌名。双调,五十五字,押平声韵。曲牌名。南曲仙吕宫、北曲大石调都有。字句格律都与词牌相同。北曲用作小令,或用于套曲。南曲列为“引子”,多用于传奇剧的结尾处。别号《思越人》、《剪朝霞》、《骊歌一叠》......
“﹝鹧鸪天﹞,一名﹝思佳客﹞,一名﹝于中好﹞,采郑嵎诗:‘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按鹧鸪为乐谓名,许浑【听歌鹧鸪】诗:“南国多倩多艳词,鹧鸪清怨绕梁飞。”郑谷【迁客】诗:“舞夜闻横笛,可堪吹鹧鸪?”又【宋史 乐志】引姜夔言:“本年夜乐外,有曰夏笛鹧鸪,沈滞郁抑,失落之太浊。”故鹧鸪似为一种笙笛类之乐调,词名或与﹝瑞鹧鸪﹞同取义于此。至元马臻诗:“春回苜蓿地,笛怨鹧鸪天”;则似已指词调矣。
本调五十五字,实由七绝两首合并而成;惟后阕换头,改第一句为三字两句。通体平仄,除后阕首、次两句有一定,及前阕首尾,后阕末句之第三字不能移易外,余均与七绝相通。但应仄起,不得用平起。 且,词的上阙第三、四句和下阙两个三句一样平常宜对仗(鹧鸪天·别情未用)。
【格律】
鹧鸪天·别情 [宋]聂胜琼
玉惨花愁出凤城,
⊙●○○●●△(平韵)
莲花楼下柳青青。
⊙○⊙●●○△(协平韵)
尊前一唱阳关曲,
⊙○⊙●○○●(句)
别个人人第五程。
⊙●○○●●△(协平韵)
寻好梦,
○●●(句)
梦难成,
●○△(协平韵)
有谁知我此时情。
⊙○⊙●●○△(协平韵)
枕前泪共阶前雨,
⊙○⊙●○○●(句)
隔个窗儿滴到明。
⊙●○○●●△(协平韵)
注:聂胜琼(?-?) 长安(今陕西西安)妓女,后嫁李之问。《全宋词》存其词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