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便是古诗词,多读点古诗词,对一个人气质教化的提升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伴随终生的。尤其在本日这个时期,网络措辞与视频直播使年轻人与那种真正可以抵达民气的书面措辞拉开了间隔,这就更须要古诗词的滋养与熏陶了。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如果是一个德国人遭遇了挫折,我想他首先想到的该当是音乐,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音乐中德国是“统统民族之王”。而一个中国古代诗人若是科场失落意,他每每用诗歌来排解解忧。
说到诗歌,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便是唐诗。如王维的《相思》一诗,在中国人的情绪谱系里别具意味:“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原是寄给南方朋侪的诗,借红豆表达墨客的思念之情。但后人常将它作为一首情诗来理解。实际上,作者与读者对同一作品理解感悟上的差异是文艺史上常常发生的事。“相思”作为一种情绪类型,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内涵却十分丰富。“现在的人谈及相思,彷佛总以为是男女之情。很少有人会认为相思也可以是一种恩典。” 今年第一期《收成》杂志刊登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她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间间的一种情。“小说的男主人公,生平欠下很多情,彷佛人生处处在欠债的样子”。可见,“感情”有时候确实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词)。
与唐诗比较,宋词写“情”则更为真切动人。宋代词人晏几道曾写过一首《临江仙》,词云:“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是一首别后怀念歌女小蘋的词作。作者曾在《小山词》的自跋里说:沈廉叔、陈君宠家有莲、鸿、蘋、云几个歌妓,他每写一词,就交给她们唱,他自己同其余两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他的词也便是通过“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张宗橚《词林纪事》说“此词当是追忆蘋、云而作”。但词中只提小蘋一人,词的上片写梦后情景,下片追忆小蘋。全词虽措辞平淡,却感情深厚,十分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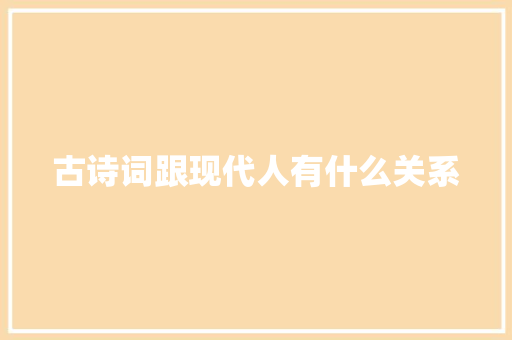
古诗词不仅富有情味,而且思想内涵十分丰硕。正如蒋勋师长西席在《“美”的最大仇敌是“忙”》一文中所说:“由于它看到大的,也关注小的。杜甫挤在难民里逃难,写出‘豪门酒肉臭,路有冻去世骨’。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以为不是诗的技巧,而是墨客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同样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都没看到。”在宋代诗歌中,直接反响国家政治、社会民生各层面的诗作数量较大,质量也很高,因而有“宋诗重事”的说法。
本日,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时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办法都发生了很大变革,但传统文化的血脉不能断,这是维系教诲的根本。自先秦至晚清,中华古诗词走过几千年,历史积淀十分丰硕。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对付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演化规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这段话,简要地勾画出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演化过程:从《诗经》的四言体到《楚辞》的骚体,再到五七言诗(以唐诗为最高繁荣阶段),末了到是非句的词和曲。
该当看到,在中国文学史上,古诗词的造诣是相称高的。尤其是诗歌,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经由近两千年漫长的发展、演化,到了唐代,无论是系统编制的完备,还是题材的多样,无论是意境的深邃,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响现实的广度,在封建社会,已达到了不可企及的境界。以是,鲁迅师长西席曾风趣地说:“我以为统统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往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算夜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可以说,诗和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来诗词并称。从风格上看,“诗家苍劲古朴”,词则“贵喷鼻香艳清幽”,有“诗庄词媚”之说。在表现手腕上,“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后来的元曲以“俗”为本色,表现手腕则“赋、比多于兴”。
但如上所述,古诗词的魅力还在于以情动人。古语说:“动听心者,莫先乎情。”没有感情的作品是没有传染力、没有代价的。法国一位作家说过:“感情是唯一永久有说服力的演说家。”
因此,我们在欣赏古诗词、进行文学创作时千万不要忘却感情成分。感情不但是主要的,而且是最富于个性特色的。在我看来,人类须要情绪,文学也离不开情绪。由于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绝望,对情绪的渴求和期望,都有可能成为诗。我在读诗作文之余,偶有兴会,也写几首小诗。但我宁肯把写诗的功夫用在捕捉诗意、深化内容、准确用字上,而不过于讲究平仄格式。用苏轼的话说,即“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条记》卷五)。当然,只有口语没有诗性、只有自由没有诗艺也弗成。
本日我们学习中华古诗词,不是为了当作家、墨客,而因此提升文化素养和生活品位为紧张目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胡中行在《“诗词大会”之后》一文中指出,对付古诗词,背诵是“根”,理解是“苗”,创作是“花”,做人是“果”。可见,学习古诗词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学习做人。这便是所谓的“诗教”。以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中国心”的中国人,光读古诗词还不足,心中要有诗。虽说几首古诗词改变不了当代人生活的缺失落,但是它给我们以思路上的启示,文学上的享受,想象上的惊奇。
(作者系上海市易学学习学院院长)
《中国教诲报》2017年2月2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