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风荡,桂枝喷鼻香,云天朗,江湖漾,秋色正缤纷。烟火,日常,温暖,收成,希望。行走,记录,用眼、存心、用情;感怀,思虑,此季别有味。今起请看一组《秋韵之行》。
今年超长的酷夏,险些看不到任何过渡,就断崖式地来到了深秋。桂花惊惶失措,来不及酝酿,于是申城的中秋完美地错过了满城桂花喷鼻香。但是只有人负花,没有花负人。大半个月后,在些许期待些许担心中,桂喷鼻香终于弥漫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大而美,只小而喷鼻香,低调、蕴藉、利他,桂花最契合中国人的代价不雅观。于是出身了许多的桂花诗词,于是桂花的喷鼻香成了中式的喷鼻香。
先看形状。“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出自南宋的朱熹。孔孟之后,朱熹是影响现实天下最深的一位哲学家。但他也是一位文学家,短短十个字把桂花的形态白描到了极致,切实其实便是诗歌里面的超写实主义,那深厚的笔墨功力透过纸背。
再听神话。在中国,有“花仙子”之说,许多花都被神化了,桂花是最被神化的一种花。中国人都相信,那一轮圆月上的影子,便是桂花。唐代《酉阳杂俎》记载了吴刚伐桂的故事。中唐白居易说“天风绕月起,吹子下人间”;南宋杨万里说“广寒喷鼻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广寒宫是嫦娥的住处,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本不相关的事情。他们都在玉轮上,一个住在宫里,一个在外“劳动”——无效的伐桂,听凭怎么砍,创口立即长好。对了,他们各有一个跟班,嫦娥的跟班是玉兔,吴刚的跟班是蟾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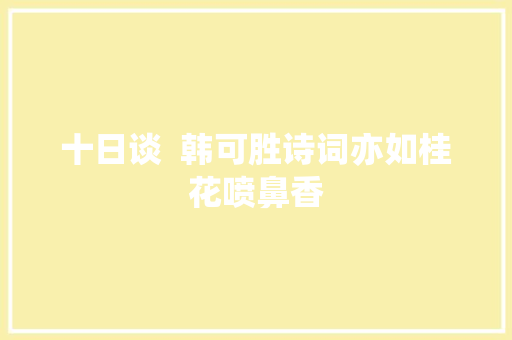
关键是意境。中唐墨客王建《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前三句大家都懂,第四句,古今人都说好,都说不同的好。我只以为深情、情深、有一唱三叹之味。同样的桂花,有人深情咏叹,就有人不动声色,比如盛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那份最幽深的禅意,不愧是出自“诗佛”之手。南宋有两位女词人,最著名确当数李清照,“何须浅碧深赤色,自是花中最高级”,把婉约词写成了豪放词。真正把桂花写到婉约深处的是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同样出自仕宦之家,更加婚姻不好,郁郁早终,父母将其作品付之一炬。“一支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喷鼻香”,美人采得一枝桂花,放在书窗之下,是人喷鼻香,是书喷鼻香,还是花喷鼻香?恐怕都是。一个和顺文雅的读书女孩跃然纸上。朱淑真更为著名的一首诗,写的是菊花:“宁肯抱喷鼻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透着不屈和抗争,也是她悲剧人生的象征。
赏桂胜地首推杭州。唐代墨客、武则天期间的宠臣宋之问,在灵隐寺写了一首诗:“楼不雅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喷鼻香云外飘。”前两句大气磅礴,后两句空灵缥缈。这么无缝衔接,只有大墨客才能如此驾驭。白居易北归之后,写了三首《忆江南》,大家最熟习的是第一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第二首写杭州:“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灵隐寺的桂、钱塘江的潮,成为千百万杭州景致的代表。写到这里,我要亮出我最喜好的桂花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作者是北宋大词人柳永,题目叫《望海潮·东南形胜》,这首词大开大合,波澜起伏,铺陈罗列,写尽了杭州的富庶和繁华,是我和女儿共同最喜好的一首词。“三秋桂子”险些成了桂花的通用语。遗憾的是,听说金主完颜亮,也是一位风骚倜傥、志大才高的墨客,读到这首词,动了投鞭南下之志,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南宋墨客谢驿作诗说:“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韩可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