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近代一位女墨客,上世纪30年代,就曾在《当代》杂志揭橥诗作,其诗被施蛰存称誉为“如琼枝照眼”。
然而,众人知道她,却是通过她的丈夫朱生豪。她在新体诗上的贡献,也被莎剧翻译家朱生豪的赫赫声名粉饰了。
她是宋清如。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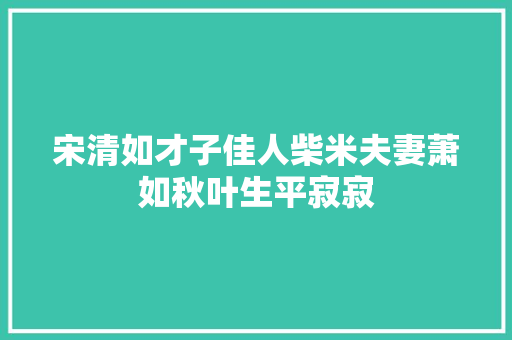
1911年,宋清如出生于江苏常熟栏杆桥的一富户人家,因排行第二,人们便称她宋氏二小姐。
宋家是地主家庭,家境殷实。清如天性聪慧,7岁时,父母请了一位秀才来家中启蒙。
父亲的初衷只是让女儿识文断字而已,他只希望女儿将来能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没想到,清如对读书的兴趣却愈益浓郁,险些到了嗜书如命的地步。
她立志要做一个读书人。强烈的求知欲使令她主动哀求到新式学堂连续读书,母亲拗不过她,只得答应。
1926年,宋清如又去苏州慧灵女中连续学业。正当宋清如全身心专一学业之时,却面临着人生一大决议,是婚嫁还是连续深造。
幼时,父母就做主与江阴华氏订下婚约。她读完初中,父母便操持起她的婚事,敦促她早点娶亲,还请来了木工开始做嫁妆。
这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姑娘武断不从,她偏执而断交地反抗着这桩包办婚姻,哭喊着“我不要嫁妆要读书”。
求知若渴的她,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满怀空想的她,想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终极,父母妥协了。
1932年夏,21岁的宋清如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读国文系。
在美景如画的之江大学,她仿佛得到了新生,开始攀登起新诗创作的高峰。
她向《当代》、《文艺月刊》、《当代诗刊》等杂志投稿。
《当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师长西席还专门给她回了一封长信:“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真不敢相信你是一位才从中学毕业的大学初年级学生……我以为你有不下于冰心之才能……”
她的诗作《再不要》、《有忆》、《夜半钟声》饱含蕴藉而幽美的悲惨色彩,表露独立自我的意识,展示当代知识女性对个人生命的体验,称得上新诗中的佳构。
《有忆》
我记起——
一个清晨的竹林下,
一缕青烟在环抱;
我记起——
一个浅灰色的梦里,
一声孤雁的长鸣
之江大学文学会合影(站立前排右四宋清如,后排右四朱生豪)
2
与此同时,她还积极加入了当时校内有名的“之江诗社”,在一次诗社活动时,她碰着了“之江才子”朱生豪。
朱生豪是浙江嘉兴人,才华横溢,中、英文成绩绝佳。
两个年轻的诗魂就这样相遇了,很快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诗词酬和,也开始长达十年的恋爱进程。
迎着早春的微风,他们相约去灵峰踏春探梅,去灵隐寺寻幽览胜。
西子湖畔、六和塔下都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一个边幅清丽,幽雅娴静,一个和蔼天真,身形瘦弱。
然而,两个相见恨晚的年轻人,虽已心潮颠簸情愫暗生,却始终把“爱”字珍藏在心间,从未点破。
直到1933年夏,朱生豪即将毕业,两人晦明晦暗的关系才有些微打破。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临别之时,朱生豪将1932年秋创作、1933年夏脱稿的三首《鹧鸪天》脱稿赠给宋清如。宋清如则把一支美国康克林墨水笔赠给朱生豪。
词作中,朱生豪不无自大地认可了“才子”的隽誉:
楚楚身材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
同游侣伴呼才子,落笔文华询不群。
……
直到那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映入眼帘,宋清如才恍然,这个内敛的才子已把未曾启齿的情绪,宣泄无遗。
自此,两人分隔两地,忍受着长久的别离。离去让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加浓郁醇厚,也更加绸缪缠绵。
3
战乱岁月里,他们笔墨往来,在长达九年聚少离多的相思之中,写下了大量互诉衷曲的书信。
自古文人皆情种。生性木讷,言语笨拙,且被朋友笑谑为“没有情欲”的才子,写起情书来却洋洋洒洒,笔底丰硕而辽阔,感情炽热而旷达。
外在内敛腼腆的他提及情话来,就像决堤的大水般大浪滔滔,无论谁人读之,都会为之心动。
“醒来以为甚是爱你。”
“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
“春天,我不忆杭州,只忆你。”
“我只乐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抚慰,像流星的光辉,照耀我怠倦的梦寐,永久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
“我乐意舍弃统统,以惦记你终此生平。”
伴着那些苦寂的光阴,他把满腹的痴恋,和着煎熬的思念,苦闷的心情,统统倾泻在笔端。他只恨情长纸短,思念如何也表达不完。
宋清如当年回给朱生豪的信,想必也是柔情似水,俏丽动人。奈何光阴久远,各类缘故原由导致她的字迹损毁太多,我们无法看到。
但是1934年春,她致朱生豪的一首情诗却留存了下来:
如果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
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
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了,
寂寞的路上只留着落叶寂寞的嗟叹……
循着这首情诗,我们彷佛看得到她身上那独属于墨客的气质和芳华,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温润情思。
朱生豪据此还填下了一首《蝶恋花》:
不道飘零成久别,卿似秋风,侬似萧萧叶,叶落寒阶生暗泣,秋风一去无。
倘有悲秋寒蝶,飞到天涯,为向那人说,别泪倘随归思绝,他乡梦好休相忆。
4
抗战爆发后,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天各一方,一别又是6年。其间,朱生豪只钟爱两件事,一是给远方的清如写信,二乃手不释卷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
朱生豪多年前就对莎剧饶有兴趣,曾反复研讨,决心要还莎翁之原貌。1935年,他在前辈的鼓励下开始动手翻译。
他把这一宏愿当作人生的至高追求,还决定把译著作为礼物献给宋清如。
可惜译莎稿件在战役中曾数度被毁,进展一贯烦懑。
每当头顶掠过日军的炮弹,朱生豪第一韶光想的是抢救自己的藤箱。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但藤箱是他的宝贝,由于里面装着莎剧译稿,那是他为之奋斗的奇迹和希望。
1941年,朱生豪第二次补译的全部译稿和重新搜集的资料再次毁于战火,心血之作付之一炬,他怒气冲天。
正当他陷入无止境的痛楚和落魄时,宋清如从重庆返回上海,来到他的身边。
1942年5月1日,国难深重的时候,朱生豪和宋清如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大略的婚礼。
相识、相知、相爱了整整10年的他们结束了漫长的离去和坎坷的奔波,终于走到了一起。这年宋清如31岁,朱生豪30岁。
一代词宗夏承煮为这对新人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贴切地表述出新人的情状,生动地表示了他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精神。
新婚合影中的宋清如以短颁发态,面庞清秀,眉眼带着盈盈的笑意。她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嫁给了最爱的人。
然而,浪漫的爱情过后,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生活的困苦。
5
这年夏天,他们从上海逃到宋清如的家乡常熟避难。
面对婚后的生活无着,也为了造诣丈夫的奇迹,这位酷爱文学,才识出众的女子,做了一个名副实在的“柴米夫人”。
宋清如钦佩丈夫的人品和才华,理解他的激情亲切和执念,她从心底里爱着这个孤独古怪的年轻人。
她像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为家庭而做出捐躯一样,选择捐躯了自己。
她转身变为主妇,挽起衣袖洗手为君做羹汤,看着因经济窘迫而长期营养不良的丈夫,仍不知疲倦地投入翻译事情,宋清如于心不忍。
1943年初,春节前几天,时局稍有稳定。朱生豪夫妇俩带着大略的行装,告别常熟,回到了嘉兴东米棚下。
他“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全力以赴地从事译著。
在虔诚于原著的根本上,他把博大精湛的古诗词教化,渗透个中。
他对翻译美学的追求和翻译标准的坚守从未游移过,终极让英国“天才墨客”的戏剧呈现出更具东方神韵的魅力。
可是,困苦的生活条件‚摧损了朱生豪的康健。
长期高强度的负荷拖垮了他原来软弱的身体,加上战役动乱,缺食少药,生活清苦,终致积劳成疾。
他被确诊为严重的结核病,得知病情的那一刻,他痛哭失落声,绝望之至,对妻儿深怀愧疚。
宋清如悲痛欲绝,只管她昼夜悉心照护,却拉慢不了去世神的脚步。
1944年12月26日,无情的病魔吞噬了朱生豪年轻的生命,一颗文坛翻译巨星在生命的天涯陨落了。
6
他在人生道路上才度过32个春秋,正处在奋发有为的年华。这一年,宋清如才33岁。
朱生豪留下已完成的31卷半莎翁戏剧,这是他以殉道者的精神,在10年中的无数个昼夜里,替中国翻译界完成的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他走了,她曾写下过哀伤的笔墨:“你的去世亡,带走了我的快乐,也带走了我的悲哀。人间哪有比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由病痛而致绝命时那样更惨痛的事!
痛楚撕毁了我的灵魂,煎干了我的眼泪。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只似烧残了的灰烬,枯竭了的古泉,再爆不动怒花,漾不起漪涟”。可她必须倔强地活着。
她一边抚养儿子,一边执教。同时,为了使《莎士比亚戏剧》的译稿得于见天日,她把全部激情倾注在亡夫未尽的奇迹上。
她独自完成朱生豪180万字遗稿的全部整理订正事情,并写下译者先容。1947年,天下书局先后出版了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辑。
朱生豪的译作问世后,博得了海内外学界的好评。美国文坛“为之震荡”,认为华人竟有如此高质量的译文,而且出自无名译者之手,实属奇迹。
不过,朱生豪还余下未完成的五部半莎剧。丈夫虽然去了,她要不惜统统代价,把剩余的翻译完成。
1955年到1958年,她请假前往成都,在朱生豪弟弟朱文振的帮忙下,动手翻译剩下的莎剧。一瞬间,那个年轻时的江南才女彷佛回来了。
她谨慎而持重地去从事这项意义重大的事情,殊不知,她在一边花费精力时,出版社那边竟早已落实了译者。
这真是个巨大的遗憾,但她却释然了。由于她知道这部浩大的著作,终于可以完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亡夫也终于可以含笑地府了。
7
1977年,宋清如回到了嘉兴南门朱氏老宅,住在楼下北面的一间偏屋内。这一年,她已经67岁了。
重新回到旧日的住所,目之所及皆是回顾。当岁月如云烟般逝去,此时的宋清如早已不复年轻时的样子容貌,她的明眸里蓄满了愁思,面庞上浸满了沧桑。
晚年,宋清如把伴随她40多个春秋的200多万字的朱译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供热心莎剧的人们和专家学者研究之用。
至于朱生豪写给她的那些恋人絮语,由于战役和动乱,极大部分信件均已毁弃。幸存下来的她本来要烧掉,究竟没有舍得。
她把这些信件编成朱生豪书信集,以《寄在信封里的灵魂》书名,于1995年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
朱生豪只是如秋风一样平常吹过,宋清如却生平寂寂萧如秋叶,度过几十年的漫长岁月。
1997年6月27日,宋清如走完了86载人活门程。
当年的之江才女在守望和相思中,坚韧地走完了寂寞清苦的生平。在与爱人分离53年之后,两人终于在天国相逢。
-作者-
溪月弯弯,愿用厚重作纸,清淡作笔,书写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