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曾巩《西楼》悟读
言为心声,诗如其人,读宋代墨客曾巩的诗作《西楼》,笔者深深震荡。诗歌是这样写的:
海浪如云去却回,
北风吹起数声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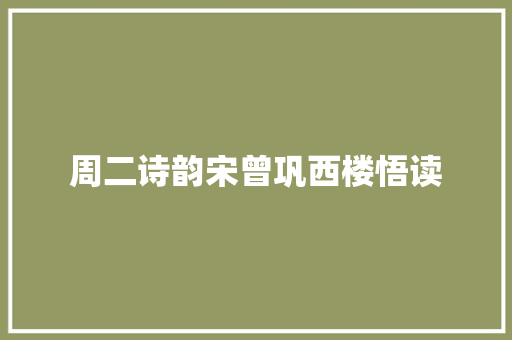
朱楼四面钩疏箔,
卧看千山急雨来。
面对电闪雷鸣,急风骤雨,面对海浪滔天,地动山摇,墨客泰然自若,卧不雅观风云,毫无半点惊惧之心,更无躲避、逃跑之举。
乌云滚滚,铺天盖地,海浪滔天,直干云霄。远了望去,海浪如云,云如海浪,云海苍茫,难分难辨。忽然,北风狂吹,闪电狰狞,几声炸雷破空而来,震天动地,震耳欲聋,一场狂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墨客满怀好奇,迫切等待,山雨欲来风满楼,江天云海壮肚量胸襟。描摹海浪,绘声绘色,气势壮不雅观,如云压城,如涛惊心,去而复回,来回变革,构成云海苍茫之间一道雄浑壮丽的风景。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千古江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奔浪涌,飞花溅玉,涛声如雷,光荣如雪,同样构成一道气势磅礴,震荡民气的巨幅图画。但是,诗词比较,曾公之浪突如其来,铺天盖地,苏公之浪千古如此,江天一隅;曾公之浪,声震云天,叱咤风云,苏公之浪摧枯拉朽,裂岸惊天:可谓各得其妙,各擅其壮。描写北风,狼吞虎咽,突兀而至,挟带闪电惊雷,滚过茫茫大海,粗粝强劲,触目惊心。而且,北风刚起,雷鸣即至,倏忽变革,令人惊惶失措。这是风云突变的及时写真,更是变幻莫测的神奇邪术。诗歌一、二两句写浪写云,写风写雷,极尽变革之迅猛,极尽声势之雄奇,足可看出墨客的壮浪情怀和博大胸襟。
一场震天动地的狂风雨立时就要到来,墨客在等待。他要欣赏,他更要渲染心中如云、如海、如雷的一腔情怀。墨客不是关门闭户,垂帘掩幕,他根本没有要躲避风雨,阻挡风雨的想法。相反,他用银钩把朱楼四面窗户垂挂的疏帘高高卷起,自己清闲地躺卧床上,他要不雅观看楼外海天千山风雨卷地而来的壮不雅观景象!
钩起疏箔,是为准备,是为不雅观赏,而且不止一壁,四面钩起,以便纵目四顾,大饱眼福。面对如此天风海雨,凡俗之人如伤弓之鸟,躲避唯恐不及,门窗关得牢牢的,拉上帘子,捂上耳朵,瑟瑟颤动,当心翼翼。可是这里,墨客却是打开窗户,拉开帘子,欢迎狂风雨的到来。卧看,是一种姿势,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胸襟。不惊不慌,不紧不慢,从容应对,沉着自若。看得舒心惬意,看得津津有味。
风雨磨练人生,海浪雕琢意志。面对海浪滔天,黑云翻滚,面对狂风骤雨,电闪雷鸣,墨客卷起高帘,闲卧朱楼,悠然不雅观赏,细细品味,这是何等开阔超迈的心胸,何等自由放旷的气度。墨客不为风云变幻所动,不为人生风雨所吓的精神品质,力求上进,欲有所为的思想境界,在西楼风雨之中展现无遗。墨客不雅观雨听雷,游目云海,实在是一展豪情,一抒怀抱。天不怕,地不怕,风不怕,雨不怕,云不怕,海不怕,无惧天地万千难,恒常一颗从容心。这便是墨客的精神风范。
【知识拓展】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很多人不知道曾巩怎么读,实在“曾”“巩”的读音都是后鼻音——曾(zēng)巩(gǒng)。曾姓是我国传统的汉族姓氏,他起初发源于山东省临沂市。如今湖南是曾姓的第一大省。巩字的本义是用皮革捆东西的意思。
曾巩出生于饱学之家,祖父曾经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是太常博士。曾巩资质聪慧,影象力超拔,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十二岁时,曾巩考试测验写《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概。18岁时他跟随父亲来到京城,与王安石结成石友,并拜欧阳修之为师。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遍四方。后来,曾巩更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并成为“唐宋八大家”,文学造诣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