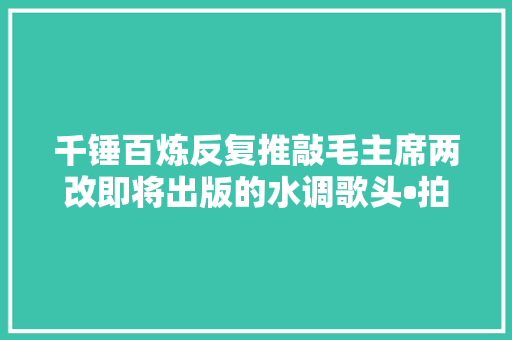《水调歌头·拍浮》
毛泽东 〔近当代〕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纵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天下殊。
词的上片写了作者刚刚喝到了长沙的水,现在又吃到武昌的鱼。在水流湍急的万里长江横渡,纵目了望,楚天浩渺无垠,高远伸展。不管长江的风急浪高,这样的拍浮,赛过在闲静的庭院闲步,本日我终于得以尽情流连。孔子在河岸上说,韶光就像这奔流不息的江水一样,昼夜一直地流逝着。
词的下片写波涛彭湃的江面,风帆飘荡,龟蛇两山悄悄地在岸边伫立,作者的胸中升腾起壮美的宏图。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将横跨南北,长江天险变成通畅的大路。我们还要在长江的西边筑起大坝,拦腰截住巫山多雨带来的大水,让三峡涌现平坦的水库。神女如果健在,定会惊异于天下发生的巨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首词是终极的定稿,之前毛主席做了多次的修正。每一次看似眇小的变革,都是他反复思考,不断权衡,千锤百炼的结果,他的作品有着精雕细琢的完美无瑕。
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原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主席在1958年和1963年出版的诗集中,曾将1957岁首年月次揭橥时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但这两次都是在终极准备印刷时,毛主席听取了多方见地,还是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清代墨客袁枚在《遣兴》中有“一诗千改始心安”之说,反复考虑是中国历代墨客的优秀传统。这个小逗号,被毛主席移动了很多次,究竟放在哪个位置,才能有最佳的效果。在反复权衡和寻思熟虑之后,这首词重新改回原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断句的位置,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别,虽意思没有变革,但重点部分却被弱化了。
“一桥飞架”,强调的是一座桥梁腾空架起,“一桥飞架南北”,则增加了空间的广阔感,一座腾空架起的桥梁将南北两地连接到了一起。后一句的“天堑变通途”,也随之有了强烈的震荡效果,无法超出的长江终于变成了一条通畅的大道。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