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我梦里,我在你梦里。在各自的梦里,我们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我们之间隔着光年的间隔,或者说趋于消逝。
时令的错位
北宋 佚名《玉楼春思图》
《春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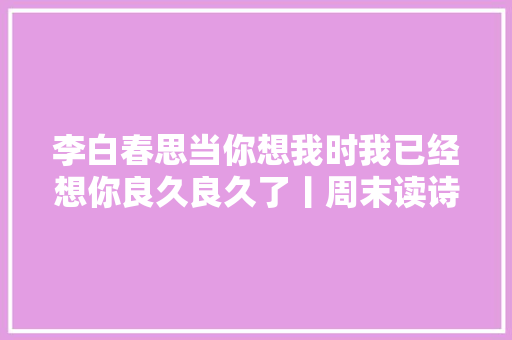
(唐)李白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东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已是春天。春天已来了多时。
对付独守空闺的思妇,春天像一场灾害,漫长的等待,一点点希望,被绿色点燃,又被绿色熄灭。思念,终归是自己的事,是春天也不知晓的秘密。
诗中的两地,征夫在燕,思妇在秦,一北一南,一东一西。燕北地寒,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寒温制造了无限间隔。太白此诗为思妇代言,造语夷易而近情,深婉而旷远,恐怕思妇自己也不能说得这么好。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起句思妇悬想燕地,春草才萌芽,细如碧丝,那里的春天刚刚开始,秦地的桑枝已绿得低垂。两句比拟,呈现出比地理间隔更迢遥的错位,他们不仅不在同一地,而且不在同一季。春天禀歧步,意味着思念不同步。
如果时令同步,韶光同步,你那里飞絮,我这里也飞絮,你此刻看到的玉轮,也是我此刻看到的玉轮,那么纵然相隔千里,我们也会觉得共时,间隔会被这些同步的事物抹去。但如果我这里看到玉轮,你那里还在中午,我们又如何天涯共此时?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这两句可以转译为:当你想我时,我已经想你好久好久了。作为当代人,我们对转译后的表达更觉亲切,由于这便是我们的日常说话办法,我们在个中立即看到自己。今人写情书不会写古体诗,纵或写了,对方可能也读不懂,读懂了大约也会以为造作,于身不亲,不能被打动,但在古代这样的诗就很自然,君、妾、断肠,这些古典命名,只能生于古代的人文环境。
古体与转译都是诗,其间差别不在古典与当代,这两句古体诗实则很当代,可以说最好的古典诗都是当代的。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感,君和妾的称谓,便有旧时女子的婉约,她在心里把丈夫看得贵气。古典的命名办法,又如“怀归”“断肠”,亦皆有古人的情态气质。
再转头读一遍:“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所谓景语即情语,对方怀归之意始萌,她在这里已等得朽迈,像桑枝一样低垂。前四句,两两相对,彼此照映,如《华严经》里说的“两镜相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沉痛至极,忽又飞扬,“东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这般笑骂,若嗔若喜,风骚闲雅,非诗仙手笔不可。太白另有乐府诗《独漉篇》曰:“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二诗对读,同是入罗帏,明月东风,一信一疑,各具妙意。
一贯以为你在桐庐
明 仇英《美人春思图》
《啰唝曲六首》其四
(唐)刘采春
那年离去日,只道住桐庐。
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
这首诗的作者,难以确证,《全唐诗》录《啰唝曲六首》,系于刘采春。晚唐范摅有条记集《云溪友议》,此书多载唐开元往后异闻野史﹐尤以诗话为多,个中写到刘采春,曰:“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并举引七首,个中六首《啰唝曲》与《全唐诗》所录相同,据此可以推论:《啰唝曲》是刘采春所唱,并非她所作。
刘采春生于中唐,是伶工周季崇的妻子,善歌唱,且会演参军戏。元稹在《赠刘采春》诗中,如此赞颂她:“言辞雅措风骚足,举止低回秀媚多。”又道:“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即《啰唝曲》,曲名源自陈后主所建啰唝楼。此曲在唐代很盛行,听说采春一唱《啰唝曲》,闺妇行人听了,莫不涟涟泣涕。
可惜后人听不到刘采春唱《望夫歌》了,我们本日只能欣赏其诗,而诗本身亦奇,造语明快泼辣,饶有民间小调风采。其一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不喜,生憎,活泼泼儿女子口吻,怨水憎船,无理得可笑,但是非常可爱。六首皆类,古色古心,着手成春,句句如痴,然而非痴无以言情。
在此选读第四首:“那年离去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离去之久,书函偶传,夫婿行踪无定,诗的意思很大略,但意味无限。西晋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诗》,诗曰:“昔者得君书,闻君在高平。今者得君书,闻君在京城。”京城繁华地,残酷多佳丽,周夫人的忧虑可想而知,墨客阐述却深婉,温顺敦厚,淡淡一笔,即转言道:“男儿多远志,岂知妾念君。”犹如《古诗十九首》的“弃置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同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人之旨。
刘采春所唱这首,语颇粗直,“那年离去日,只道住桐庐。”桐庐在浙江,那年离去时,夫婿说是去桐庐,她便一贯以为他在那里。哪怕她没去过,也不知道桐庐在哪里,仅仅知道这个地名,她的怀想也有个方向,他是有定处的。
“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桐庐已经很远,不知其期,今偶得书,忽得知他不在桐庐,而在广州。广州去家更远,更归期无日。几句平常话,无需激情亲切夸年夜,即已触目惊心。
唐代水陆商业发达,外出做生意的男人很多,妇女被留在家里,独守空闺,年复一年,怨怅感情弥漫。贩子行踪愈远,想家心思愈淡,白居易《琵琶行》曰:“贩子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那贩子是做茶叶买卖的,才走了两三个月,琵琶女昔为倡家,浮华惯了,已经不堪冷落,她的凄悲惨切,不为思念夫婿,宁是自怜自伤。
《啰唝曲》中的贩子妇,乃是良家女出身,经年累岁不得其夫,连他的人在哪里还会不会回来也一概不知,苦闷无助至极,诗句却如古乐府的素直,斩然而起,意尽言止,中间不作半点委曲。
一首诗里的时空交汇
传北宋 崔白《双鹅图》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我们读过,但值得再读,好诗总也读不厌,总也读不尽,且每读每新。
深夜,大巴山,秋雨绵绵。滞留巴蜀的李商隐,深陷雨夜,长安往事如梦里,连他自己也像一个回顾,此时此地,只有雨是真实的。
夜雨寄北,一作“夜雨寄内”,即寄给妻子。按诗中的情景,寄内彷佛更合理,但在此取“寄北”,情由有二:李商隐给妻子的诗,从未题过“寄内”;寄北可以是寄给亲友,也可以是寄给妻子,北是个方向,诗心所向,比寄内更能引发想象。无论寄内还是寄北,所寄怀者,必是私昵之人。
冯至有一首十四行诗,写雨夜深山,诗中写道:“深夜又是深山,听着夜雨沉沉。十年前的山川,廿年前的梦幻,都在雨里沉埋。”夜雨和深山把他封锁在这里,一间狭窄的小房,阴郁空间中的一个点,而他的心在呼唤大的宇宙。
李商隐亦身困山里,深夜又是深山,秋雨淅沥,池水涨溢,凄苦无聊之际,唯有回顾可堪抚慰,唯想象力可带他突围。诗的缘起,表面上看,是首句的“君问归期”,实则是夜雨,雨夜的困顿使他想起君问归期,因他此时更深切地觉得归期难至。
巴山夜雨涨秋池,这是此时此地,是当下他的处境,也是他拥有的人生。首句是对过去的回顾,浮现在深山夜雨。“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后二句遥想未来,本色也是回顾,是当下对未来的回顾,或者说飘向未来的回顾。
这首诗笔力之健,章法之妙,用情之深,古人所述备矣,我们却来看看诗中的时空。过去、现在、未来,连成一条直线,此是一样平常人的时空不雅观,诗中彷佛也这样呈现,首句是过去,次句现在,三四句未来。之以是如此,由于措辞表达本身就受限于线性韶光,我们没法同时说出几句话,只能一句接一句地说,这便产生了先后顺序。
但这种先后顺序并不真实,它仅仅出于不得已。诗的义务便是超越这种限定,尽可能地还原我们的真实体验。我们活在每个当下,无论是回顾起的过去,还是想象中的未来,全都被我们同时体验到。
《夜雨寄北》的读法,可以有好多种,从头读至尾是个习气,未必是最好的,一种读法即一种打开办法,我们可以发挥创意。如果纯挚地瞩目这首诗,视觉上四句同时呈现,就像电影镜头的场景并置,没有先后,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在这首诗中,过去不在过去,它浮现于夜雨,就在此时此地,未来也不在未来,未来已经存在。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 李阳
校正/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