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宋代: 朱熹《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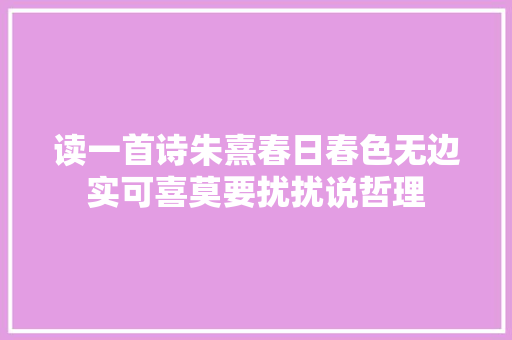
说到春天,每个人面前自然都浮现出一幅画面。不必是哪一年,也不必是哪一处地方,见到春天的实景,则都可以逐一照料。每年的春天,大都相似,而一旦一个新的春天来时,游赏的兴致都还依旧。春天带给人的,除了“无边光景一时新”的俏丽可喜,还有春尽花落的悲哀。俏丽的春天,总是随意马虎迟暮,伤春的诗词,绝对多于因春天产生的喜悦。
春天初来之时,万物焕发生机,柳绿花红,燕飞蝶舞,美景满眼,处处可不雅观。当此之时,纵使忧闷的人,也会欣喜于面前的美景,不会升起伤春的感情。昨日柳黄,今日花开,无不牵引人的游兴,想着一定要饱览大好的春光。
天地间的春,一下子一齐到来,今日花开,嫡花开,逐日一番新的光景。看过东边,则会错过西边。面前的不雅观赏不尽,更想望着千里万里,一览无遗。当然是不能得的。无论处于哪里,都有可不雅观之处,日日目接不暇,纵使其他的许多地方都错过了,也必不会留有遗憾。
朱熹这首《春日》诗,只写欣喜于春光之美,描述了春的轮廓,没有详细的意象,情也没有落到任何一个实处。并不像是在陈说某个春天游赏春景而喜,更像是写了一篇关于春的文章。虽然是写春天,不一定便是写于春日,可以是想到春天的任何时候。诗中的关于春天景致的描写,也不是详细的某一个地方。无论哪里的春天,用这首诗来描述,都不会有欠妥。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春天便是这样的。如果有印象更深的事物,则存在于各个人的心里,用想象为那个轮廓添枝加叶。
许多人纠结于“泗水”并非实事。据考证,朱熹从来没有到过泗水滨。泗水在山东,孔子曾在洙、泗二水之间讲学。于是他们遐想到朱熹并非在描写春光,而是心仪孔圣,实际上是在陈说理学,是一首哲理诗。不是春天的景致使他愉快,而是醉心学问使他愉快。如此讲,这首诗就顿时毫无意见意义了。我并不关心诗中是否蕴涵那样的哲理,我之乐于对着无边春光的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