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侯的世子诸儿,是个酒色之徒。诸儿只比文姜大两岁,异母所生。两人自幼在一起终年夜,每天凑在一处玩耍。文姜长成少女,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诸儿也已经成人,身材颀长,面如敷粉,唇若涂朱,范例的美男子。
诸儿情窦初开,见妹妹文姜仙颜,且举动轻佻,常常有调戏文姜的意思。文姜游荡不羁,性情妖淫,把男女大防,视作无物。兄妹之间措辞戏谑,常有市井间的污言秽语,丝毫没有避忌。二人整日里牵手并肩,无所不至,只是碍于周围宫人仆妇,仅是没有肌肤之亲。
郑世子忽助齐大败戎兵之后,齐侯常常在文姜面前夸赞郑世子忽高大帅气,英伟非常,为人又谦恭有礼,文质彬彬,并且正在议婚。文姜听了,心里高兴,昼夜愿望嫁给郑世子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等到听说郑世子忽武断辞婚,心中无限失落望,得了相思病,身上乍寒乍热,精神恍惚,食难下咽,睡不安枕。
后来诸儿与文姜兄妹悖逆人伦,腌臜如禽兽,自不必提。此时文姜心恋郑世子忽,本是正常男女之情,在古代也被广泛认可,诗经中多有描写男女爱情的诗词,以今人视为最古老之老夫子孔子的评价,也不过“诗三百,思天真”,并不以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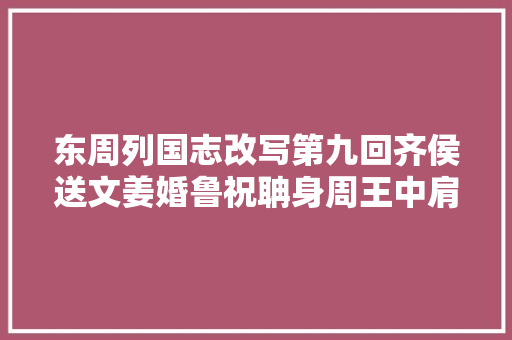
然而,纵然对文姜暗恋郑世子忽成疾这种古人不雅观念里都属正常的男女情绪,后人中也颇有微词。有人在诗中写道:二八深闺不解羞,一桩情事锁眉头。鸾凰不入情丝网,野鸟家鸡总是愁。依诗中意思,青年男女相互爱慕对方才貌人品,相互思恋,都属正常,但如思恋而成疾,格局和人品就降了不止一等,差别就如鸾凰与野鸟家鸡之大。墨客指出的问题,相称于本日的“以理智为辅导和统率的爱情是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样的问题,至于答案,见仁见智,未必同等。
以上闲话搁过不提。再说诸儿听说文姜患病,就常常以探病为名去私会文姜。到了之后坐在床头,用手遍摸文姜身体,假装问哪里疼痛难熬痛苦。因周围有别人侍候,仍未及乱。
一天齐侯去看望女儿,见诸儿在女儿房中,斥责道:“你们二人虽是兄妹,但依礼也应该避嫌。今后派宫人来问候就可以了,你不必亲自来。”诸儿诺诺连声退出,自此不敢再来,两人就很少见面了。
没过几天,齐侯给诸儿娶了宋女为妻,又纳了鲁女、莒女为媵,诸儿新婚,忘却了文姜,两个人见面就更少了。文姜在深宫之中,惦记诸儿,却又不能对身边人说,窝在胸中,心里孤独苦闷,病势加重。
却说鲁桓公登基的时候,年事已经不小,但还没有聘娶夫人。有大臣劝道:“古代国君,十五岁就生儿子了。如今主公还没有聘娶妻子,更没有儿子,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谁来继续君位?谁来主持敬拜宗庙?”
周秦之际,敬拜是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敬拜是和行军打仗同等主要的大事。像我们本日清明节俭墓祭祖,有一搭没一搭的,很多人连自己老爷爷的名字都说不出来,这在当时是不可想像的。
李白在诗中嘲笑鲁国腐儒,“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经世济民之策,到了唐代,已经成为统治者选人用人的必备稽核项目。但在周秦时期,社会管理大都是沿用部落时期的传统习气,统治者用敬拜等主要礼仪程序统治人的思想,用武力办理礼仪办理不了的问题。管理方法大略粗暴。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在祀与戎之外,又增加了“一断于法”的手段,但商鞅变法的所有设计,还是环绕戎事进行的。大约正因如此,在大争之世的战国时期发挥了决定性浸染的秦法,到了统一之后反而涌现了重大问题。面对涌现的大变局,秦统治者因循自以为已经得到成功的旧制度,连续实行严刑峻法,终极导致二世亡国。很可惜,秦人崇尚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的同时,却没有把稳到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的告诫: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由于之备。面对大争之世与统一的国家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而采取同样的管理办法,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有什么不同?怎能不败?
可笑今日有些学习法律之人,既不深入研究社会现实,又不能节制法学精神的精髓,仅仅翻几本西方法律著作,就以不得了的法学家自居,弃古代精良法学思想如敝屣,写几篇没人看的文章,几本没人读的书,就指天划地,其本色不过是流连于几个圈注,几个外文的术语词汇,他们和李白诗中鲁国整天沉溺于句读的腐儒有什么实质差异,误人误己,为国挡贤而已。如果非说有差异,腐儒腐则腐矣,可能误人子弟,却不会为国挡贤,不会去争什么协会职务、代表、委员之类。
汉初对政权的处理,部分采纳了封建制,办理经济发展问题的办法,采纳无为而治、与民安歇的办法,相称于回到周时的管理办法。国家只管敬拜、打仗,物质资料生产吗?老百姓自己干就行了,国家只管即便少干预。
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的儒术,已经是董仲舒做了重大改革的儒术,统治者要积极主动,有所作为的思想被突出强调。汉盐铁论便是一份朝庭主要干部和社会贤达之间就如何发展经济展开辩论的漫谈会记录。这该当是把经世济民作为王朝统治主要事情突出出来的开始。无论是漫谈会本身还是会议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结论,都可以阐明为什么汉代之后中国能够以一骑绝尘的姿态领先天下。前辈的思想,可能是永久引领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扯得太远了,再扯回来。有大臣建议鲁侯尽快成婚,公子翚说:“我听说齐侯有爱女文姜,数次向郑世子忽提婚被拒,主公可以去求娶。”桓公答应,派公子翚去齐国求婚。齐侯说女儿正在病中,请鲁侯先等一等。
宫人把这事儿见告了文姜。文姜的病本是因男女情事而引发的相思病,听说鲁侯派人前来求婚,觉得大龄剩女的日子有望闭幕,心情稍觉惬意,病体逐渐康复。
齐、鲁、郑与宋会盟确认宋庄公国君地位的时候,鲁侯再次向齐侯求婚,齐侯请鲁侯再等一年。鲁桓公三年,鲁侯约齐侯会盟,齐侯对鲁侯的殷勤深为冲动,答应了鲁侯的要求。鲁侯当即献上彩礼,齐侯大喜,约定玄月亲自送爱女到鲁国与鲁侯成婚,鲁侯到时候派公子翚去齐国迎亲。
诸儿听说齐侯许亲之事,旧情复萌,派人给文姜送了一束花,里面夹了一首诗。本日求爱送花,也每每夹一个小纸片,这个手段是否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就不清楚了。
诗的大意说:桃花好美啊,在家里盛开的时候没有摘,飘落之后就变成草了。后悔啊后悔。
文姜看了之后,明白诸儿的心思,回了一首诗,大意是:桃花有灵,今春不折,不是还有明年春天吗?别忘啊别忘。反正两个的人的诗便是骚得弗成的那种吧。所往后人以此为耻,正儿八经作诗的时候,就要写离骚。
诸儿读了文姜的诗,知道文姜还有心于自己,更加思慕。
韶光不长,鲁国公子翚来齐国迎亲。
诸儿听说,去见齐侯:“齐、鲁世代友好,现在又结成婚姻,鲁侯虽未亲迎,我们却必须亲人去送。父亲有国事要处理,我乐意代替父亲去送亲。”
齐侯犹豫:“我已经答应鲁侯亲自去送,不好失落信于人吧?”正说着,有人来报,说是鲁侯已经率车驾到了驾邑,专门期待迎亲。
齐侯说道:“鲁国果真是礼仪之邦,在半道迎亲,这是怕我再到鲁国首都过于劳累。我更要自己去送亲了,不然有失落礼数。”诸儿只好退下。
文姜听说,心中若有所失落。婚期附近,文姜即将动身,到东宫告别诸儿。因诸儿夫人在侧,加之有齐侯安排的监视人等,两人四目相对,心里千言万语说不出来。文姜离开东宫的时候,诸儿趁别人不把稳,溜到文姜车旁,悄悄说道:“别忘了相互赠诗之事。”文姜回答道:“往后有相见的机会。”
齐侯把文姜送到驾邑,与鲁侯相见。双方叙礼完毕,鲁侯设宴接待齐侯,对所有随从都有丰硕赏赐。齐侯告辞归国。鲁侯带文姜返国成婚。一来因文姜来自大国齐国,二来文姜貌美,鲁侯特殊宠爱敬仰。成婚后带文姜祭拜宗庙。鲁国大夫和宗室的夫人都来拜见国君夫人。齐侯派弟弟夷仲年代替自己去鲁国看望文姜。齐、鲁两国更加亲密。
再说周桓王因郑伯伪装王命伐宋,心中怒极,免除郑伯卿士之位,只留虢公林父辅政。此时忌父已去世,林父继任为虢公。郑伯听说,心里怨恨周王攫取自己权力,持续五年不到王室朝见。
一日周王升殿,桓王说道:“郑国寤生太过无礼,必须惩处,不然往后大家都要效仿他,那样的话,军队就不好带了。我亲统六军,讨伐郑国,宣告寤生罪状。”
虢公劝道:“郑国历代对周王室都有大功,现在夺了他的权力,以是不来朝见。该当先下诏征他入朝,大王没有必要亲自讨伐,以免轻渎天威。”
桓王怒气不止:“寤生陵暴我,已经不止一次。我与寤生势不两立。”随后召蔡、卫、陈三国一起出师伐郑。
此时,陈国国君鲍刚去世,鲍的弟弟公子佗弑太子免自主为君。陈国百姓不服,纷纭逃散。陈、郑关系本来密切,但佗刚刚弑太子自主,就接到周王使者来使征兵,不敢不从,只得命令大夫伯爰诸为将,带兵跟随伐郑。蔡、卫两国也都派兵出征。
桓王让虢公率领右军,蔡、卫两国军队跟随右军;让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国军队跟随左军。桓王自己率领中军,旁边策应。
郑伯听说王师来伐,调集群臣问计,群臣都不敢出声。打别人可以,这次是打王师,那时候这事儿的性子相称于儿子打爹,自周王朝建立,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郑伯要第一次吃螃蟹,也让群臣第一次吃螃蟹。再说,为儿子打爹出谋划策,帮兵助阵,这话不好说。说得不好,郑伯来一句,好小子,你们本日帮我打周王,往后是不是帮别人打我?脑袋都保不住。
祭足一看要冷场,赶紧向前,多少回应一声,给主公一个别面:“这个嘛,主公啊,天子亲自带兵来伐,责备主公没有朝见,光明正大,这仗不好打。不如派人去赔礼,天子一高兴,再规复你在朝中的职位。这不是转祸为福吗?”
郑伯本来最听信祭足的,一百回至少听九十九回,没想到这次转了性,发了驴脾气:“我呸!
我呸呸呸!
祭足你是我郑国著名老臣,一向见识远大,足智多谋,这次弄的什么玩意儿?天子夺我朝中职位不说,还派兵讨伐我,我家三代勤王大功都不管了。这次要不教训教训他,我们的宗庙都保不住了。”
这里有个事儿得交代一下。那个时期,姓比较乱,一样平常同姓,往上查不了多少代,便是一家。不同姓的,往上查,也不一定不是一家。有人以封地为姓,有人以字为姓,有人以氏为姓,还有人以官职为姓。反正姓原来的姓,只要烦了,就随便找一个换了。孔子的孔姓,便是祖上木金父逃到鲁国后,以字为姓。
按史记所载,周代第一代文王姬昌是后稷的后代。后稷今后N代,有个人叫古公亶父,他是姬昌的爷爷。古公亶父原来该当在宁夏甘肃一带居住,是部落首领,由于少数民族常常打他们,他们就迁到歧丰一带,一看这地方不错,就住了下来。什么时候开始姓姬的,史记里没说。史记里这些东西都是司马迁听说的,连司马迁都没听说的事儿,我更没听说过。
周初分封时,姬姓的占多数,异姓的占少数。大的诸侯国里边,宋国是商的后裔,殷姓;齐国封给大元勋姜子牙,姜姓。秦是附庸,到了平王东迁之后,因功封伯,才与诸侯国取得名义上的同等地位,嬴姓。楚本是蛮夷之地,宣王征服后列入诸侯,芈姓。
郑国与天子同姓,都是姬姓。郑国初封时,本来很小。到了郑武公,趁周王室东迁朝政混乱之机,吞并东虢和郐,边陲才有所扩大,不过比起秦、齐、楚、晋等大国还是小得多,只是郑庄公很猛,以是这个时候国势很强。
同姓一旦宗庙分开,宗庙为一处的,成为一拨。大家都把宗庙看得很重。周公制礼之后,众人对宗庙看得更重。宗庙与天子哪一个更有威信,因周公制礼时没有明确规定,后来也没有威信阐明,所以是一个很有争议问题。真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则的形成,是秦划郡县往后的事儿。以是说,当时郑庄公拿宗庙对抗天子,该当说还是理直气壮的。
众大臣看郑伯主张已定,也就没了顾忌,纷纭献策。高渠弥说道:“陈、郑关系向来要好,陈出兵属于不得已。蔡、卫是郑的夙仇,必出去世力。周王年夜怒亲征,王师士气高昂,不能硬拼。不如凭坚固守。”
公子元反对:“正好相反。以臣抗君,先输了理。韶光长了,我们的军队民气不稳,随意马虎被人所乘,造成内乱。还是速战速决为好。王师分为三军,我们也分玉成军,用左军抵挡其右军,用右军抵挡其左军,主公亲率一军抵挡天子。陈国本来与我们要好,再加上公子佗弑君自主,民气不稳,军队是攒鸡毛凑掸子,毫无战斗力。我们用右军攻击陈国军队,一定一触即溃。用左军攻击蔡、卫,蔡、卫听说陈国溃败,也一定溃败。然后旁边合军与主公率领的中军一起夹击周王的中军,一定大胜。”
郑伯夸奖道:“你料敌如指掌,真是公子吕再生啊。”
正在商量之时,有人来报,王师已经到了葛地。郑伯命令曼伯率领右军,祭足率领左军,自己率领中军,在军中建起“蝥弧”大旗。
祭足说:“这个大旗上有四个大字“奉天讨罪”,是当时伪装王命伐宋和许的时候用的,它用来伐诸侯可以,用来伐周王弗成。奉王命讨王,这算是什么玩意儿?”
郑伯恍然大悟:“这我倒是没想到。”命人放在仓库,往后不再用了,想打谁就打谁,货真价实,不再搞假冒伪劣那一套了。
高渠弥说:“我看王师军队严整,天子很懂兵法。这一仗不好打。我们用鱼丽阵吧。”
郑伯问道:“鱼丽阵什么样子?”
高渠弥答道:“二十五辆兵车在前,二十五个战车兵在后随着。战车上的士兵每伤一个人,后面随着的战车兵就出一个人补充,只准提高,不准退却撤退。这个阵法极其紧密坚实,不随意马虎被击破。”郑伯说:“好,就这么办。”
郑军到了葛地附近,扎下营寨。周王一听郑伯不仅不立时认罪求饶,还敢引兵来抗王师,更加愤怒,当时就要亲自领兵出战,被虢公劝住。
第二天,双方各自排好阵势,郑伯传令,旁边两军不要轻易出动,看中军大旗挥舞,再一起进攻。
桓王本来窝了一肚子气,头一天晚上打了一整夜的腹稿,准备战阵之上叫郑伯答话,先把郑伯责骂一通,声讨他不臣的罪过,出一出胸中恶气,同时挫动郑军锐气。没想到双方摆好阵势半天,郑营那面没有动静,郑伯没有出来,也没人前来寻衅。
桓王花了一晚上功夫打好的抑扬抑扬、趾高气扬的腹稿,半点没用上,不由得有些灰心。桓王只好派人寻衅,郑营只是守住阵势,并无人应战。
就这样一贯相持到中午时分,郑伯料定王师已经懈怠,让暇叔盈挥舞大旗,只见郑军旁边两军鼓声如雷,将士大家奋勇,个个争先,曼伯一马当先,率兵直冲陈国军队。陈国军队本来全无斗志,等了半天,一个个都要睡着了。忽然听到鼓声大作,一队郑兵如狼似虎杀来,顿时扔下兵器乱逃,把周公黑肩率领的周军冲了一个乱七八糟。黑肩吆喝不住,只得败逃。
另一壁,祭足率军朝蔡、卫军队杀去,两国军队抵挡不住,纷纭败退。右军大将虢公仗剑立在车上,大声命令:“乱动者斩。”右军没乱,祭足害怕伤亡过大,也没敢过分逼近。周的右军没有损伤一兵一卒,逐步退去。
桓王听到鼓声响起,知道郑军发动进攻,立即指挥军兵,准备和郑军厮杀,创造自己军兵不对头,一个个交头接耳。原来中军军兵已经知道旁边二军都败北了,全没了斗志。正在此时,郑军中军杀到,旁边二军得胜后也集中过来,三军合兵一齐杀向周王的中军,切实其实像砍瓜切菜一样平常。桓王只好敕令撤退,自己断后,且战且退。
郑将祝聃远了望见绣盖之下有一人,想是周王,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周王左肩。幸好两人间隔很远,周王战甲又厚,仅是命中,入肉不深。祝聃催车急进,要来擒拿周王,虢公赶来,截住祝聃,斗在一处,救下周王。原繁、曼伯也凌驾来,眼看周王和虢公危险,却听到郑中军鸣金,三将不敢再战,收军回到中军大帐。
周王带兵退三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也赶了过来,向周王告状:“陈国人不肯着力,以是才败北。”周王说:“怪我用人不明。”
祝聃见到郑伯,问到:“我已经命中周王肩头,正要生擒那厮,为什么鸣金?”
郑伯说:“本次开战,都是由于天子处事不公,道理不明,以怨报德。天子来伐,应战实在是不得已,仗大家皆出去世力,现在保住了宗庙社稷,已经是万幸,还敢想别的吗?依你所说,把周王抓来又能若何?如何处置?就算命中天子,也不应该,倘若天子伤重去世了,我不就成了弑君犯人了吗?”
祭足说道:“主公说得对。如今我们军威已立,周王该当不敢再有其他企图。我们该当派人前去慰问,稍示殷勤,并奉告侵害周王并非本意。”
郑伯对祭足说:“这事非你前去不可,别人干不了这个活儿。”嘱咐祭足带上牛羊粮草等劳军礼物,连夜前往周营。
祭足到了周营门外,连连磕头,口称“去世罪之臣寤生,为保宗庙不毁,社稷不灭,带兵自卫,没想到对下属约束不严,搪突王驾,寤生不胜惶恐之至。现派下臣祭足,待罪辕门,敬问天子安好。一点儿劳军物资,不怕猥琐,献给大王,聊充军用。”
周王红着脸,什么也没说。虢公代为答道:“寤生既已知罪,可以宽恕,来使谢恩吧。”祭足磕头退出,到周军各营分别问安。
桓王兵败回周,心中怒火难消,打算传檄再次伐郑。虢公劝道:“这次伐郑,便是由于准备不敷,轻率出师。如果传檄四方,即是自曝己丑。再说诸侯中除陈、蔡、卫之外,都是郑伯一党。征兵征不到,白白惹郑人嘲笑。郑伯既然已经派祭足劳军赔礼,我们就借这个台阶下来,赦免郑的罪过,让郑悔过悛改吧。”桓王沉默,自此不再提伐郑的事儿。
却说蔡侯因派兵从征伐郑,率军将领在军中听说了陈国公子佗弑太子篡位的事儿,返国后报告蔡侯,说是陈国百姓不服。蔡侯决定派兵去打击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