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升和他的《农耕文田》
作者 | 张玉奎
2023年末,传来,高学升老师要出书了,我很高兴,由衷地祝贺他老人家。高学升老师进入2024年就八十五岁高龄,老年出书,将自己多年的创作集结出版,意义非凡。这是他的名誉,也是我们广大文友值得庆贺的一件圈内大事。
高学升老师临朐五井镇下五井西村落人,生平务农,在这个拥有五六千口人的大村落落当过多年司帐,生产队司帐和大队司帐都干过,有着极好的人缘,口碑非常好。文化程度不高,却自学成才,尤擅诗词楹联;散文写得不错,措辞凝练,从不拖泥带水,风格简洁,阐述明了。他为我县几百名、乃至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写过嵌名联,无不令人称妙。这是一份独到的天才艺术,广受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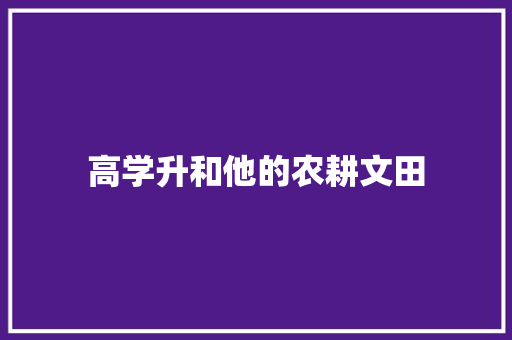
高老师虽年事已高,身体很好,精神很好,只是眼睛弗成了,看一米远近的人脸都视觉模糊,读笔墨非常吃力,常常依赖放大镜。他依然坚守文学的爱好,不离不弃,时有著作揭橥,有着倔强的毅力。我很喜好他的作品,每篇必读,留言处写下自己的感想。
高老师是精良的,教诲子女也是精良的,四个孩子,教诲的都非常成功,有在国外定居的,是个令人倾慕的家庭。孩子们都孝顺,在出书这件大事上,无不大力支持。无论生活上,还是个人还好上,高老师的生活环境都非常宽松,非常自由,老年幸福。
高老师喜结文友,与我们中很多人保持着良好而长久的关系。高老师很好客,三年前我与国承善,在苏洋总编的带领下拜访高老师,受到极为激情亲切的接待,五井镇上、五井村落落里所有文化圈的名人险些都请到了,济济一堂,陪着我们,场面实在是隆重。也正是在这次礼遇中,我结识了同是下五井西村落的王传禄老师。那日中午高老师选择了莲花山一处新开的酒店,别具一格,蒙古包里设宴,且把我们推向了上坐,至今自感才不配为,每每回顾起来,羞愧不安。
高老师的嵌名联公认的好,无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逐一写进各位文友的心里去,便是有这份天才,众人无不佩服。请看几例,如写冯恩昌:恩情于人福寿永,道德处世业家昌。骈邑散人:骈邑地灵英精彩,散人德厚国医扬。张远:伸开双翼高天遨,风顺一帆远海航。杨道明:奔锦绣辉煌大道,效光明磊落贤人。诚信善良人守道;谦逊谨慎自知明。许法忠:效法贤人高风致,忠于祖国美精神。本人嵌名联:玉石斋中藏异宝,奎星楼上作佳章。我以为,高老师把我们圈子里人一个不落地写了一遍,他可真花费了精力,下上了功夫。
初次认识高老师,缘于几年前去了趟淹子岭。国承善老师驾车,拉着我和苏洋老师。不才五井西村落通到村落前的公路口,高老师和王志刚老师早早等着了。那年高老师八十一岁,还能攀登三县顶,很佩服他的体力。在王志刚老师和高学升老师鼓励下,回来我写了篇淹子岭游记,关注量还是不低的,一众文友纷纭留言揭橥读后感,言如亲临等等。
2024年元旦,我们去淹子岭,首先到了高学升老师的家里,恰好他在家,家里不少人,我们都不认识,预测是他的朋友、亲戚,或许街坊邻居。喝了两杯茶水,坐了一坐就走。高老师把他的《农耕文田》搬出一大摞,给我和国承善一人一本,逐一揭开扉页,提笔写下赠人存念字样,署上高老宝号,出具年月日。我第一韶光揭开看了看,老作家冯益汉师长西席写的序,朴实诚挚,文笔恳切。
此书370页,附有后记,声明了出版此书得到诸多朋侪的帮助,得到子女们的大力支持如斯,声明自己年迈眼花,难免涌现错讹,诚恳得到批评示正。谦逊诚挚生平好学,是高老师的实质,在这后记中亦可窥见一斑。
《农耕文田》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楹联拾趣、诗词吟诵和文章随笔,每一部分都融进高老师大量的心血和执著的勤奋。八十多岁的人了,少年时没有上过多少学,自学成才,诗文俱佳,多才多艺,勤勤恳恳奋斗几十年,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崇高空想,为后人留下影像,其实不易,其实可贺!
高学升老师记性很好,惊人的影象力令人佩服。八十多岁高龄的人了,对付小时候学过的教材内容,至今仍能背诵,比如在他的《初上小学时的回顾》一章里,这样写道:
第一课:羊
第二课:大羊,小羊。大羊大,小羊小。
第三课: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
第四课: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
第五课:小狗咬小羊,小羊叫;小狗追小羊,小羊逃。
第六课:小羊小羊,不用逃,小狗咬你,你用角抵。
第七课:小羊用角抵小狗,抵抵抵,小狗跌一跤,小羊笑。
第八课:小青小青,起来起来,起来上学去。
第九课:老师早,老师好……
一本小学课文,直到末了一课,高老师险些全都记得。其间有一课是:“小朋友,你有一个好朋友,摸摸身上有没有,摸不着么?便是你的一双手。”还有一课:“石山高,石山低,石山腰里雪花飞。”末了一课:“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一个钉,两个钉,数来数去数不清。”
亲爱的读者们,这是何等的影象力呢?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清晰记得当年初上小学时的教材内容,而且险些全部背诵下来,佩服之余,您不感到吃惊吗?正是高老师的良好影象,让我们理解到半个多世纪前的小学课文,是这样清新明了,简洁而富有活气。
高老师一见我,目光弗成一时认不出来,湊近了,再凑近了,一米以内的间隔,仔细瞧着我的脸,而后恍然大悟,连声说:“张老师,张老师!
”他看我的样子,直让我觉得他继认不出来。从他脸上的表情,我预测出认知的程度,直到他笑颜满面,我知道他完备认出来了。几年不见,他对我还有清晰的印象,看到就能把我认出来。
高老师搬出来的那一摞书,第一本给我签上名,第二本国承善的,第三本马玉宝的,第四本张兆新的,他知道我们四个都是临朐东北乡里人,嘱托回去捎给他们。
厚重的一本书啊,内容广泛,如《抗日春联别样红》、《临朐民谣》、《临朐农谚》、《临朐气候谚语》、《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履行后的下五井村落》、《当年八路军驻村落发生的一件事》、《忆下五井村落京剧子弟班》、《回顾我村落反“细菌战”时的见闻》,一系列篇目,看一眼就知道都是史实记录,都是知识记录,可载入史册,非常宝贵。这是一今年夜气的书,一本有代价的书,一本好书,是一个诚挚而又负责地忠于史实的老作者聪慧的结晶,手捧沉甸甸的。
张玉奎,临朐东城人,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