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组诗,组诗便是由于受格律的制约,不能尽兴的内容,须要扩充,墨客就会多写几章,少则两三首,多则二十都城不止。
杜甫的《秋兴》这一组诗写了八章,以是也题《秋兴八首》。
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杜甫《秋兴八首》之一
诗歌创作的基本手腕是“兴、比、赋”。兴,便是有感而发;比,便是比喻的意思;赋,便是排比铺陈的意思。所有的诗歌创作手腕都逃不脱这三种手腕。《秋兴八首》这一组诗,三种手腕都有。由于写于秋日,以是也是因秋有感而发的诗作。
你的提问说第一首诗前两联“因秋托兴”,后两联“触景生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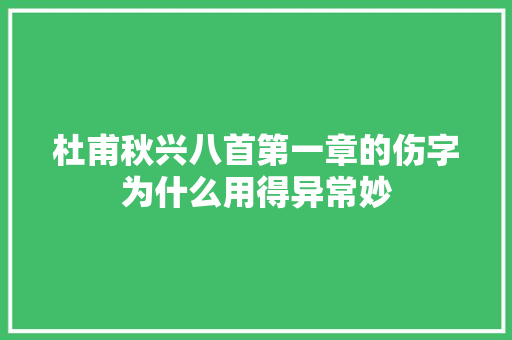
格律诗有严格的构造。不是按前两联和后两联划分构造的,因此,绝对不能这样划分构造。
律诗共八句四联,两句为一联。第一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第四联叫“尾联”。
这四联的构造关系是:起、承、转、合。
首联叫开头,也叫“起”,颔联和颈联叫展开,是“承和转”,尾联叫扫尾,是“合”,这个构造关系是不能搅散的。
以是,你说的前两联,该当是前两句。前两联叫“上半阕”,后两联叫“下半阕”。
但是这首诗也不能用上半阕和下半阕来划分。由于这是一首完全的诗,他的文章构造是三个部分。即:开头、展开和结尾。
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一首诗,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起手,是触景伤情。
“玉露”便是秋日的露,由于很冷了,所以是玉露“凋伤”了枫树林。杜甫写诗用字非常厉害,以是,这个句子也很经典。“凋伤”二字,直接从枫树林一贯到“巫山巫峡”,境界从面前延伸到无边无涯的巫山巫峡,气候非常伟大,可谓怨而不伤。
第二联和第三联是由秋兴的“玉露”这个小境界,延伸到详细描写的和想象描写的复合,它扩大了眼界,丰富了层次,充足了思想。
以饱和的力度,分别用“兼天涌”、“接地阴”、“异日泪”、“故宅心”给予了夸年夜的想象描写,令读者浮想联翩。
杜甫在“凋伤”的枫树林中,给我们平添的这些江间浪,塞上云,丛菊泪和孤舟心,也让我们为“兼天而涌”、“接地而阴”、“异日之泪”、“故宅之心”而唏嘘感叹,这便是抒怀的色彩。
以上三联,由第一句的起,到第二句的承,第三句的转,把我们从近景“玉露”,引向穿越时空的“丛菊两开”和“异日之泪”的“同伤”之境。它点出了杜甫,已经两年没有安宁之日了!
本日,也是飘摇不定的心。
我们知道,杜甫是永泰元年(764)的四月,因他的支持者严武溘然暴亡,而引起蜀中军阀混战,仓惶离开居住了五年的成都的。
然后杜甫自己买了一条船,飘飘摇摇一年,经由忠县、云安等地,才来到夔州暂时安稳下来的。
杜甫之以是能够流寓于夔州,是由于夔州的军政首领,夔州兵马使叫柏茂林,他曾经是支持严武的一位下属部将,以是,对杜甫还是非常友好的。杜甫在夔州也居住了三年呢!
《秋兴八首》是杜甫来到夔州第一年的秋日写的。当时,他刚刚安顿下来出息未卜,一年多来,战乱未已,朋友凋零,他颠颠扑扑,来到夔州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逢秋必悲的墨客,更随意马虎多愁善感,写下自己心中的悲愁。
在《秋兴八首》的第一章,他从面前想到了两年以来自己的弯曲之路,和孤独无助的悲惨。
但是在尾联,还是回到了“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的面前,这两句诗中的“寒衣”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景。虽然墨客无法看到“处处”,但是,从一处可以遐想到处处,这是比较现实而合理的想象。由于诗中写到他在白帝城听见了砧石上杵衣的声音。
这两句诗又回到了“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现实情景之中。诗中的寒衣处处。白帝城高。与枫树林,巫山巫峡。都在同一时空。以是,这便是“合”,诗歌创作起承转合的合,便是我们本日讲的呼应,要首尾相呼应。
以是,我们不能把前两联诗和后两联诗,看作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从诗歌的艺术创作手段上来讲,用的是起、承、转、合。从文章的构造来讲是开头、展开和结尾三个部分。
开头是首联,展开是颔联和颈联两联,结尾是尾联一联。
我们剖析诗歌创作的构造,要把他的创作手腕和文章的内容构造差异来看。
《秋兴八首》第一首的创作方法,起、承、转、合的格式没有任何变革。第一联因秋伤情。这在第一句“玉露凋伤枫树林”中就已经直接点出“伤”了,这一个“伤”字,就给全诗定下了基调,也给其它的七首诗定下了基调。以是,第一句是因秋伤情。第二联和第三联是这种伤情的展开和推进,它衬托和丰富了伤情的情绪身分和意境的氛围,而诗歌的末了一联,通过家家户户都在“催刀尺”和“急暮砧”的细节,把这种悲情推向高潮。令人首尾之间,荡气回肠于秋寒之伤。
虽然尾联只有两句十四个个字,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毫无空洞之感。例如“寒衣处处”的“催刀尺”和“白帝城高”的“急暮砧”都写的非常生动,字字有神。它描写秋日到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过冬的衣服,韶光有点紧,以是有时不待我的催逼之感。天虽然晚了,但是必须把衣服洗干净,早点晾晒。
这两句伤秋的诗句,写的非常有情绪和痛点,它远远超过了从大笔淋漓的伤景铺陈的虚写,到对伤人的实写的痛点上。把“玉露凋伤”于“枫林”转移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痛点上了。
这正是诗歌起、承、转、合一样平常技法和大开大合的思想境界相结合的艺术手腕的统一。
杜甫诗歌的境界之大,就在于他把个人的悲和公民的悲,把韶光的悲和命运的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一幅伤秋的图景。
下面我们再看看《秋兴八首》第一首的原文:
玉露凋伤枫树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异日泪,
寒衣处处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