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庭芳,词牌名,别号“锁阳台” “满庭霜” “潇湘夜雨” “话桐乡” “满庭花” 等。以晏几道《满庭芳·南苑吹花》为正体,双调九十五字,前后段各十句、四平韵。另有双调九十五字,前段十句四平韵,后段十一句五平韵;双调九十三字,前段十句四平韵,后段十一句五平韵等变体。代表作品有苏轼《满庭芳·蜗角浮名》、秦不雅观《满庭芳·山抹微云》等。
《满庭芳·南苑吹花》——宋代· 晏几道
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故宅欢事重重。凭阑秋思,闲记旧相逢。几处歌云梦雨,可怜便、汉水西东。别来久,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
年光还少味,开残槛菊,落尽溪桐。漫留得,尊前淡月西风。此恨谁堪共说,清愁付、绿羽觞中。佳期在,归时待把,喷鼻香袖看啼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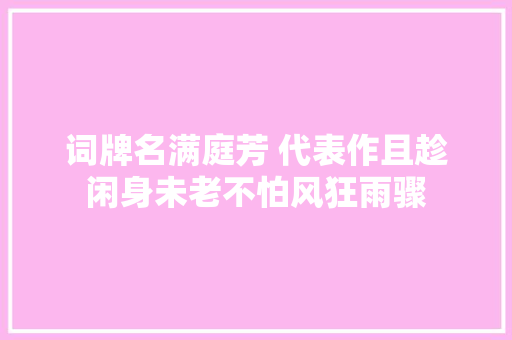
此词是晏几道为一位歌楼歌女而作,是一首回顾之作,详细创作韶光不详。
此词是一篇怀远人之作,开片三句,写凭栏遥望所回顾起的往事:“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故宅”里的各类欢娱的事。“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是一个对句,对的及其工致。
凭栏遥望,不禁回顾起往昔的欢快,由此想到现在:往昔欢聚的那些人,现在都如“流水”一样各自“东西”,由于分别得久了,感情逐渐的淡漠了,由此引出“未有”“锦字系鸿雁”。
过片思远人的人,现在的生活情景: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年光少味”与前片的“欢事重重”相对应。“开残槛菊,落尽溪桐”写尽了深秋,花败叶落的悲惨景象,表露出看到这幅秋天景色的人此时的心情。“开残槛菊,落尽溪桐”,是一对句,它与前面的“南苑吹花,西楼题叶”,遥相呼应。想当初是“欢事重重”现在是“年光”“少味”,“几处歌云梦雨”现在只落得“尊前淡月西风”,没有“锦字系鸿雁”“此恨”又能“谁堪共说”。只能把满腹的离愁别恨都 “付”与“绿酒”中。正像晏几道在《阮郎归》里说的那样“愁肠待酒舒”。
怀着一腔希望,期待着佳期的到来。抱负着佳期到来时,见到日思月想的人,一定让他看“喷鼻香袖”上的“啼红”的情景。
此词由凭栏回顾开始,写到现在,由眼睛看到的萧瑟的秋天景色,写到主人的悲不自胜。期待着再次相逢。全词婉约有致,情溢言外,余味无穷。
《满庭芳·蜗角浮名》——宋代· 苏轼
蜗角浮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尽放我 一作:须放我)
斟酌。能几许,忧闷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去世,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这首《满庭芳》词的详细创作韶光难以确证,但从词中表现的内容和抒发的感情看,须是苏轼受到重大挫折后,大致可断为写于贬于黄州之后,当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2)之后几年内所作。有人认为作于元丰五年(1084),也有人认为作于元丰七年(1086)。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怀。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落败者繁芜的内心天下,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洒脱旷达的两个性情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范例意义。
此词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展示了作者人生道路上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既愤世嫉俗又洒脱旷达的内心天下,表现了作者宠辱皆忘、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全词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怀,情理交融,肆意不羁,用语率真自然,风格旷达舒卷。
苏轼在词中善于抒写人生。他高于一样平常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抵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主要缘故原由。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绝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称这首词是一篇抒怀的人生哲理议论,应该是适可而止的。词中的议论不仅直接表现思想,也能高兴淋漓地表达感情。作者写此词时,大约是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浩瀚坎坷,因而大有退避之心。此词全篇援情入理,情理交融,现身说法,真抒胸臆,既充满饱经沧桑、愤世嫉俗的沉重哀伤,又洋溢着对付精神解脱和圣洁空想的追求与神往,表达了作者在人生抵牾的困惑中寻求超脱的出世意念,可谓一曲动听至深的生命的觉醒和呼唤。
《满庭芳·山抹微云》——宋代· 秦不雅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停息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往事,空回顾、烟霭纷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落。(万点 一作:数点)
销魂当此际,喷鼻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薄暮。
这首《满庭芳》是秦不雅观最精彩的词作之一。起拍开端“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雅俗共赏,只此一个对句,便足以流芳词史了。一个“抹”字出语新奇,别故意趣。“抹”字本意,便是用别一个颜色,掩去了原来的底色之谓。传说,唐德宗贞元时阅考卷,遇有词理不通的,他便“浓笔抹之至尾”。至于古代女流,则时时要“涂脂抹粉”亦即用脂红别色以掩素面本容之义。
按此说法,“山抹微云”,原即山掩微云。若直书“山掩微云”四个大字,那就风骚顿减,而意致全无了。词人另有“林梢一抹青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的名句。这两个“抹”字,一写林外之山痕,一写山间之云迹,手腕俱是诗中之画,画中之诗,可见作者是故意将绘画笔法写入诗词的。少游这个“抹”字上极享盛名,婿宴席前遭了冷眼时,便“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半子也!
“以至于其虽是笑谈,却也解释了当时人们对作者炼字之功的赞许。山抹微云,非写其高,概写其远。它与”天连衰草“,同是纵目天涯的意思:一个山被云遮,便勾勒出一片暮霭苍茫的境界;一个衰草连天,便点明了暮冬景致惨淡的气候。全篇情怀,皆由此八个字里而透发。
“画角”一句,点明详细韶光。古代傍晚,城楼吹角,以是报时,正如姜白石所谓“正薄暮,清角吹寒,都空城”,正写详细韶光。“停息”两句,点出赋别、饯送之本事。词笔至此,便有回顾前尘、低回往事的三句,稍稍控提,微微唱叹。妙“烟霭纷纭”四字,虚实双关,前后相顾。“纷纭”之烟霭,直承“微云”,脉络清晰,是实写;而昨日前欢,此时却忆,则也正如烟云暮霭,分明如,而又迷茫怅惘,此乃虚写。
接下来只将纵目天涯的情怀,放面前景致之间,又引出了那三句使千古读者叹为绝唱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落”。于是这三句可参看元人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捉住范例意象,巧用画笔点染,非大手不能为也。少游写此,全神理,谓天色既暮,归禽思宿,却流水孤村落,如此便将一身微官濩落,去国离群的游子之恨以“无言”之笔言说得淋漓尽致。词人此际心情十分痛楚,他不去刻画这一痛楚的心情,却将它写成了一种极美的境界,难怪令人称奇叫绝。
下片中“青楼薄幸”亦值得玩味。此是用“杜郎俊赏”的典故:杜牧之,官满十年,弃而自便,一身轻净,亦万分感慨,不屑正笔稍涉宦郴字,只借“闲情”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词意怫郁谑静。而后人不解,竟以小杜为“冶游子”。少游之感慨,又过乎牧之之感慨。
结尾“高城望断”。“望断”这两个字,总收一笔,轻轻点破题旨,此前笔墨倍添神采。而灯火薄暮,正由山林微云的傍晚到“纷纭烟霭”的渐重渐晚再到满城灯火,一步一步,层次递进,井然不紊,而惜别停杯,流连难舍之意也就尽个中了。
这首词笔法高超还韵味深长,至情至性而境界超凡,非存心体味,不能得其妙也。后,秦不雅观因此得名“山抹微云君”。
《满庭芳·归去来兮》——宋代· 苏轼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达五年之久的苏轼,接到了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安置的命令。邻里朋侪纷纭相送,苏轼作此词以示告别。
苏轼作词,故意与“花间”以来只言闺情琐事的传统相异,而尽情地把自己作为高人雅士、作为天才墨客的全体面貌、肚量胸襟与学问从作品中呈现出来。一部东坡词集,抒怀办法与技巧变革多端,因内容的须要而异。个中有一类作品,纯任性情,不假雕饰,脱口而出,无穷清新,它们在技巧和章法上看不出有多少创造发明,却专以真实动听的感情和浑然天成的构造取胜。这首留别黄州父老的词即其一例。
这首词用散文式的句子和俚俗的措辞,真切的表现了作者对黄州的留恋之情。上片抒写对蜀中故里的思念和对黄州邻里父老的惜别之情,下片进一步将宦途失落意之怀与留恋黄州之意对写,突出了作者达不雅观豪放的性情。这首词情致温厚,属辞雅逸,意象光鲜,宛转蕴藉。
东坡到黄州,原因此待罪之身来过被羁管的囚徒日子的,但颇得主座的眷顾,居民的亲近,加以由于他脾气达不雅观,思想通脱,长于自解,变苦为乐,却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他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风骚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别,必是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由此可见,这首词抒发的离情,是发自东坡内心的高度真实之情。此篇的优秀,就在“情真意切”这四个字上。尤其是高下两片的后半,不但情致温厚,属辞雅逸,而且意象光鲜,宛转蕴藉,是构成这个抒怀佳篇的两个高潮。
《满庭芳·碧水惊秋》——宋代· 秦不雅观
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洞房人静,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落,往事难猜。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谩道愁须殢(tì)酒,酒未醒、愁已先回。凭阑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
秦不雅观为官期间因政治上方向于旧党,被目为元祐党人,绍圣后贬谪。此词一说为他被流放因思恋故国所作,另一说为他晚年谪居后而作。
此词融情入景,以景语始,以景语终,在层层铺叙、描写中表达了伤离怀旧的心绪。
全词上片怀旧,以景语开篇,下片伤离,以景语结情,景语情语,丽雅工致,情韵兼胜;层层铺叙,步步切近亲近,委曲婉转,悲惨动人。从此词可以看出:少游词以“情韵兼胜”而为众人传诵。他的“情韵兼胜”的艺术风格是在景物描写中展现的。少游的词作,写景而情在个中,统统景语皆情语,长于融情入景,既显豁,又蕴藉,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功力。这首《满庭芳》,即光鲜地表示了秦词的艺术特色。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宋代· 周邦彦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干瘪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宋强焕《片玉词序》:“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为邑长于斯。”元祐癸酉,为元祐八年(1093)《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卷溧水县厅壁县令题名:“周邦彦,元佑八年仲春到任。何愈,绍圣三年(1096)三月到任。”则此词当在此三年间作于溧水。周邦彦在元祐二年(1087)外放,辗转了七年,才当上了溧水知县。官职很小,劳燕东西。在某个夏日,他游览了无想山,感慨万千,创作了这首词。
周邦彦为北宋末期词学大家。由于他深通音律,创制慢词很多,无论写景抒怀,都能刻画入微,形容尽致。章法变革多端,疏密相间,笔力奇横。王国维推尊为词中老杜,确非溢美之词。兹剖析一下他的《满庭芳》一首词,即可见一斑:
周邦彦于公元1093年(哲宗元祐八年)任溧水(今江苏溧水县)令,时年三十七岁。无想山在溧水县南十八里,山上无想寺(一名禅寂院)中有韩熙载读书堂。韩曾有赠寺僧诗云:“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由此可见无想山之幽僻。郑文焯以为无想山乃邦彦所名,非是。
周邦彦自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离开汴京,先后流宦于庐州、荆南、溧水等僻远之地,故多自伤出生之叹,这种思想在此词中也有所反响。但此词的特色是蕴藉蕴藉,词人的内心活动亦多隐约不露。例如上片细写静景,解释作者对四周景物的感想熏染细微,又似极其客不雅观,纯属欣赏;但“凭栏久”三句,以贬居江州的白居易自比,则其内心之抵牾苦痛,亦可概见。不过其表现办法却是与《琵琶行》不同。陈廷焯说:“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抑扬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解释两者风格之不同。下片笔锋一转再转,弯曲传出作者流宦他乡的苦况,他自比暂寄修椽的社燕,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但终于只能以醉眠求得内心短暂的宁静。《蓼园词选》指出:“‘且莫思’至句末,写其心之难遣也,末句妙于措辞。”这“妙于措辞”亦指蕴藉而言。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这话是对的。即如这首词就用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人的诗,而结合真景真情,炼字琢句,运化无痕,气脉不断,实难堪能名贵的佳作。
《满庭芳·小阁藏春》——宋代· 李清照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喷鼻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
从来,知韵胜,尴尬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喷鼻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骚。
此词历来被视为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刘瑜《李清照全词》认为此词当为清照南渡前的词作。陈祖美《李清照简明年表》认为这首《满庭芳》为公元1104年(宋徽宗崇宁三年)的作品。但也有学者认为此词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如谢桃坊就认为它应是作者遭到家庭变故后所作。
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佳作。
此词咏残梅,是词人当时生活、感情的真实写照。词人以残梅自比,充分显示了她孤高清傲,不同流俗的性情特色。全词意境相谐,词调低沉,风格深婉,措辞轻巧,写尽了词人生僻寂寞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深切感伤之情。
在这首咏梅词中,作者借物咏怀,暗寓了出生之感,其主不雅观抒怀色彩十分浓厚,达到了意与境谐、情景交融的程度,故难辨它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还是咏物了。它和清照那些抒写离去相思和悲苦感情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尖新,词意深婉弯曲,表情细腻,腔调低沉谐美,富于女性美的持征,最能表示其基本的艺术特色。这首《满庭芳》不仅是《漱玉词》中的佳作,也应是宋人咏物的佳作之一。
《满庭芳·红蓼花繁》——宋代· 秦不雅观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这首词应该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当时秦不雅观谪处郴州(今属湖南)。秦不雅观在宋元丰元年(1078年)落第后,曾受到世俗的讥笑。这让他感到甚为痛楚,常借助饮酒麻痹自己的心灵。此时谪处郴州,这种痛楚心情依然萦绕于其心头。
上片侧重写景,描述楚江月夜独钩的情景,犹如一幅清江月夜独钓图;下片侧重写人,写楚江月夜独醉之事,着意刻画具有光鲜个性的形象。全词如诗如画,淡素雅洁,清丽宁静,蕴藉蕴藉,耐人寻味。
全词先写景,后写人,写景则着意描写分外环境,写人则着重描写个性形象。如此层层写来,精心点染,细致描述,一个分外环境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一幅生动的楚江月夜独钓而又独饮醉卧的画面,清楚地呈现读者面前,从而使人们感想熏染到词人看似然、坦然,实际上郁积着不平和愤懑的心情。
这首词,颇受东坡文风的影响。只是,东坡可以无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沧桑孤独,可以做到“何妨吟啸且缓步”的洒脱无碍,而这些在少游的生命中,却只是一枕黄粱,鸡鸣之后,繁华酒醒,斯人不仅依旧寂寞,更无端添了些许断肠相思。如果说,东坡词超脱旷达,让民气神往之。那么,少游词则是柔婉悲惨,不知不觉中沁入人的心脾。两者各有各的好处,毕竟少游和东坡的心性,一个在云,一个在水,相隔太远。
《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宋代· 李清照
芳草池塘,绿阴庭院,晚晴寒透窗纱。玉钩金锁,管是客来唦。寂寞尊前席上,惟愁海角天涯。能留否?酴釄落尽,犹赖有梨花。
当年曾胜赏,生喷鼻香熏袖,活火分茶。纵目犹龙骄马,流水轻车。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花。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
这首词作于1138年,正值南宋初期,李清照已经是54岁。经历了宋庭南渡,亡夫之痛,李清照辗转由金华到杭州定居。
满庭芳,因唐·吴融“满庭芳草易薄暮”诗句而得名。别号《锁阳台》、《满庭霜》、《潇湘夜雨》等。有平韵、仄韵二体。平韵正体为双调九十五字,高下阕各四平韵, 或上阕四平韵,下阕五平韵。转调,据《词学概说》里说,一个词牌都有一个宫调,凡是改变原来句式或者增减字数的,称为转调。李清照这首《满庭芳》便是这样。
易安写这首词已经是54岁,也便是南宋初期(1138年),易安通过回顾当年的“胜赏”,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悲惨干瘪为难刁难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词苑千载,盛开只一女儿花。”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女词人。这与她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李清照首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
词的上半阕采取实写的手腕,“芳草池塘,绿阴庭院,晚晴寒透窗纱。”一个温馨的庭院,一缕夕阳斜照,一个孤独的老人,在这斜阳的下面隐蔽一个去国怀乡的心。后蜀·毛熙震《浣溪沙》词:“花榭喷鼻香红烟景迷,满庭芳草绿萋萋。”明·沉鲸《双珠记·家门始终》:“万古千愁人自老,春来依旧生芳草。”这里词人以芳草自喻,有忠贞贤德之意。
接下来是“玉钩金锁,管是客来唦。”可能是孤独的老人期待着有朋友的幻觉,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这妮子匆忙则甚那?管是妈妈使来唦!
”“寂寞尊前席上,惟愁海角天涯。能留否?”孔融有一句名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吾之愿也。”这也是李清照的欲望,可见李清照如今的空虚。去国怀乡,身处异域,连繁华的临安在李清照眼中也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海角天涯,留的住她的人,却留不住她的心。“酴醿落尽,犹赖有□□。”酴釄花落尽,幸亏有什么。写春去花落感伤光阴的流逝是很多词人写词手腕,李清照“犹赖”二字更显对流逝的无赖。
词的下半阕从回顾到现实的写作,“当年曾胜赏,生喷鼻香熏袖,活火分茶。□□龙骄马,流水轻车。”这是对曾经的回顾,在以前李清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朋友的集会上,那里燃着袅袅暗香,煮着茶,李清照用茶匙从煮好的茶汤中舀出分饮众人。曾经的生活是那么多美好,正由于曾经的美好反衬呈现在的寂寞。曾经的卞京,如今的临安,这种反差不仅仅是李清照的生活而是全体社会、国家的变革,对美好过去的回顾,对如今的只有讨厌。“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花。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那些狂风暴雨,世事变幻不可怕,虽然如今也一样的煮酒不雅观花。但物是人非,国家的变更,亲人的逝去,朋友与自己的渐行渐远,虽然东西还是那些东西,但人却不在。
《满庭芳·晓色云开》——宋代· 秦不雅观
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落,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豪门映柳,低按小秦筝。
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凭阑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
秦不雅观在《与李乐天简》中称自己于宋元丰二年(1079年)岁暮,自会稽回籍,“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从词中所描写的景致以及“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等用语来看,这首词极有可能便是秦不雅观在次年春天游历扬州时所作。一说作于绍圣元年(1094年),作者被贬处州后。
秦不雅观长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这首词记芜城春游感怀,写来细腻自然,悠悠情长,语尽而意不尽。此词的情调是由愉悦转为忧郁,色调从明快渐趋暗淡,词人的心情随着韶光和环境的调换而在起着变革,却又写得那样宛转蕴藉,不易琢磨,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了,“清闲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全词构造风雅,形容奥妙,措辞精练生动。景随情变,情景交融,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从构造上剖析,这首词由三条结索交织构成。第一条是韶光线索,以清晨雨过天晴开始,到薄暮的疏烟淡日结束,中间于描写景物之中点出酒空花困的午时情怀。第二条是游历所经的线索,从古台到横桥,从豪门到芜城凭栏,将一日游赏展现出来。第三条是情绪线索,从清晨出发时的逸兴满怀,到中午时分的意阑无绪,再到日暮时分独下芜城的寂寞无聊,将词人游赏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感情变革展现出来。虽然进行艺术剖析时,可以清理出这么许多条线索来,但是,由于词人熔裁得体,使三条线索浑然融为一体,不仅没有造成滞碍之嫌,反而使词风更趋婉约,词情也更有风致了。
《满庭芳·堠雪翻鸦》——清代· 纳兰性德
堠(hòu)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宵起舞,无人处、那有村落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
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此。叹纷纭蛮触,回顾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
词中提到混同江,描写的又是冬天景致,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至十仲春词人赴梭龙时。其时,纳兰性德随驾抵达吉林,来到了混同江(现称松花江)畔,这里原是一片古沙场。入关之前,女真族在统一过程中,建州、海西、野人诸部相互残杀,彼此并吞,冒死争夺,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心灵创伤。词人触景伤情,写下此词。
唐柳宗元有“满庭芳草积 ”句,唐吴融有“满庭芳草易薄暮”句,故此调名之缘有或柳诗或吴诗之不同说法。此调别号《锁阳台》、《江南好》、《话桐乡》、《满庭霜》、《转调满庭芳》、《潇湘夜雨》、《满庭花》等。有不同体格,俱为双调。本首为其一体,上、下片各十句,共九十五字。各片之第三、五、七、十句押韵,均平声韵。
此篇前景后情,以赋法铺写。其下片全为议论,虽不免质实,但气势壮不雅观,真情四射,仍是生动动听的。上片前五句景语,写古沙场的荒寒阴森,以“总堪悲”绾住。下句转进,先说有“中宵起舞”的爱国之心,但“那有村落鸡”一句折转,表明无由以报,徒增伤感。再接以金笳声声陪衬,则更令人添悲增慨。下片承前之情之景转为议论,表达了满怀哀怨和痛楚。墨客以为“古今事”都是虚无的、短暂的,古来的统统纷争,统统功业,到头来除了“剩得几行青史”,“断碣残碑”之外,余皆成空。这虽是悲观的意绪,但从中亦可窥见墨客长期积于心中的苦情。这种“苦情”,有人认为纳兰对家族被灭往事的隐恨(见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可备一说。
《满庭芳·水抱孤城》——近当代· 王国维
水抱孤城,云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白鸟悠悠自去,汀洲外、无限蒹葭。西风起,飞花如雪,冉冉去帆斜。
天涯、还忆旧,喷鼻香尘随马,明月窥车。渐秋风镜里,暗换年华。纵使长条无恙,重来处、攀折堪嗟。人何许,朱楼一角,寂寞倚残霞。
这首词是王国维于1905年离开南通去往苏州时所作。当时王国维阔别家人,独自一人在外地任教,借此词抒发自己内心的孤独。
这首长调上片写景宁静闲适,颇有“无我之境”的味道;下片回忆少年意兴引入羁旅秋风的悲哀心结尾倚栏人形象回应了前边的写景,可知前边景致皆倚栏人所见。从而勾引读者返回去品味上片的写景,创造原来上片也不是纯挚的“无我之境”,它已经在宁静淡远的景致之中隐蔽了许多悲哀和无奈。
“水抱孤城,云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这几句持续串三组意象构成了一幅闲适、安谧的图画:流水环抱孤城,遮住远方天空的浮云已经散去,柳树上栖息着三三两两的乌鸦。这三组景物分别可以让人遐想抵家乡,对远方征人的期盼和对安居无忧的神往。因此,它们看起来闲适,实际上却是引发游子羁旅之愁的起源。“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通过一个“漾”给了这幅安谧安祥的图画增长了一种动态。
“白鸟悠悠自去,汀州外,无限蒹葭”是镜头的迁徙改变,水鸟和无边无涯的芦苇也承启了下面一句。“西风起,飞花如雪”这里的飞花,显然不是春天的柳絮而是上一句的芦花,正是这芦花给全体画面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在这迢遥朦胧的水面上“冉冉”的“去帆”那便是作者对自己迢遥、朦胧的影象中某些往事的回顾。
下片开的“天涯,还忆旧”就很自然地把描写重点从景转向于情了。“喷鼻香尘随马,明月窥车”是忆旧,写的是当年元宵夜游的意兴。这一句明显是化用唐人苏味道的两句诗“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无论当年有多么欢快,可是到了“渐秋风镜里,暗换年华”的时候,人的意兴也就随之起了很大弯化,“纵使长条无恙,重来处,攀折堪嗟”便是说的这种变革。“朱楼一角,寂寞倚残霞”,便是通过一个倚朱楼而望暮霞的孤独身影十分蕴藉地写出了一种往事如烟,良辰不再的悲秋感情。“人何许”人就在那悲秋的高楼上纵目了望,他已经与这寂寞景致融入到一个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