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读者一样,我的高罗佩阅读史,是从他的小说开始的。那是1984年春,刚刚来到新的城市,乱翻父亲订阅的过刊,看到了两年前在《读者文摘》(后为差异于美国著名刊物Reader's Digest中文版,更名为《读者》)上连载的《黑狐狸》。小说始终笼罩着神秘的气息,情节惊险而弯曲,笔墨似旧非旧(此乃译者手段),还配了一张洋人扮演的狄公照片,形象全不斯文,模模糊糊的反倒有些狰狞。更让我惊异的是,这样一部以唐代人物为原型的作品,作者前面赫然注明了他的国籍“荷兰”!
高罗佩,这是若何一个人?九岁的我根本无从去想象。那时,我已经对古琴有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也就一如既往地大加放肆,任其繁殖,可没几年,竟然又在古琴这一途与高罗佩不期而遇。
高罗佩作为荷兰职业外交家,生平以业余身份从事汉学研究。
直到十六年前,我读到了陈之迈师长西席的《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12月),才创造之前读过的大量先容高罗佩平生的笔墨,绝大多数都取材于此。同时,也意识到高罗佩第一手中文资料显然极其匮乏,不然那些笔墨也不至于总是大同小异,缺少细节。其时,因特网刚刚把天下连接起来,中外资讯的互换开始热络,但盘根错节,一时还轮不到高罗佩,我既然不谙外文,索性以搜集高罗佩第一手中文资料为业余之消遣,倒也有滋有味。当时的心愿,是建议大陆的出版机构出版陈之迈师长西席的《荷兰高罗佩》,免得读者们总是看辗转几手的残存。然而原书薄薄数十页,按照大陆的出版习气,难以成册,于是一搁置便是数年。
然而,世间自有深得书趣三昧的爱书人。十年前,继1998年成功策划出版了极为精美的“茗边老话”系列小书之后,沈昌文、陆灏两位师长西席又策划了一套小书“海豚书馆”,而且这次规模更大,分六色系列,操持出到百馀种。蒙陈子善、陆灏两位支持,我将《荷兰高罗佩》原书中文部分及自己搜集的第一手中文资料,汇为《高罗佩事辑》,纳入“海豚书馆·赤色系列(文艺拾遗)”,交付海豚出版社。那年正值高罗佩百年诞辰,海内开始系统翻译出版高罗佩小说、性学之外的著作,家属往来,出版社造势,余热未消。《高罗佩事辑》面世于2011年初,适逢其时,一度脱销,加印不止一次。陈之迈的文章,先容全面而笔墨可读,普通读者爱看;我花费心力辑录的资料,碰着几位学者,都说“好用”。普通读者爱看,学者以为“好用”,这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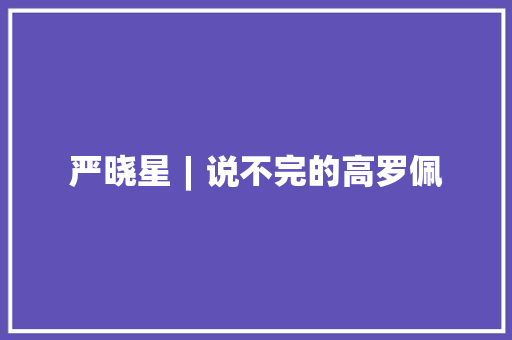
《高罗佩事辑》(海豚出版社,2011年)
如今距本书初版面世,已逾八年。高罗佩在中文天下的影响力,与从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紧张学术著作,大多已经出版了中文版,诸如《琴道》还出了两种译本;他的小说,三十多年来有多家出版社推出了多个版本,最近又将有不同的全译本整体面世。关于他的著述与活动也骤然丰富起来:研究他的专著,已出版数种;他的荷兰文传记,已推出中文版(虽然译得不尽人意);以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多处召开……西方汉学家,能在中国的学术和大众领域都收成如此多的关注的,一人而已。这八年,海内外交流密切,文献大量数码化,新材料不断呈现,对初版加以增订,也因此得以实现。
本书较之初版,篇目多出二十七篇(初版二十四篇),字数多出二万六千字(初版约七万强),整体篇幅多出三分之一,增订幅度不可谓不大。兹将增订体例,略作解释如次:
一、初版分为“荷兰高罗佩”、“史料辑录”、“友朋诗词”三辑,增订版则分为“基本文献”、“著述媒介”、“史料辑录”、“字画题跋”、“投赠诗词”五辑。
二、“字画题跋”中的相称一部分是诗词,之以是不将它们并入“投赠诗词”,一来是将字画作品单列出来,便于利用,二来是诗词与其他作品殽杂在一起,抽出另列会毁坏字画作品的完全。
三、“字画题跋”中傅芸子、傅惜华的《〈广陵散谱〉题记》,严格说来不属“字画”题跋,而是书本题跋,姑作为特例,系于此辑。
四、“字画题跋”中《〈十八琴士题诗梦师长西席遗像〉题跋》、《〈巴江录别诗字画册〉题辞》成于众人之手,环境互异,除特为赠别高罗佩而作之外,有借用古人成句者,未必全是自作(如徐文镜、徐芝荪、吴建、安世霖、张伯驹、洪陆东、仇鳌、胡庶华、冯玉祥、岳园、鹏九);有虽系自作,但自录其旧作者(如章士钊、田汉、郭沫若、沈尹默)。而无论借用或自作,无论新写或旧作,均不乏与通畅版本或作者诗集、文集偶有字词出入者(如胡庶华、苏渊雷、郭沫若)。如此各类,不一一注明。
五、极个别无法辨识的字,暂以“□”代替。
部分新增材料,得益于张立䇇、方继孝、张凌、梁基永、于鹏、谭然、宋希於、黄知凡等师友;松琦女士、王鹏师长西席分别出示他们珍藏的高罗佩照片与画作,赵自清、刘晨夫妻慨然以《琴道》初版精装本见赠,丰富了本书的图片。本书首次将《巴江录别诗字画册》中的笔墨内容完全录出,得到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高罗佩特藏室的大力支持。《〈十八琴士题诗梦师长西席遗像〉题跋》、《〈巴江录别诗字画册〉题辞》等文本的整理,若较之前更为准确,则应归功于赵鹏、王家葵师长西席。《游青云亭 赏名家墨宝》原文所录高罗佩楹联的错字得以校正,则应感谢2015年底大马朋侪黄德欣精心安排的马六甲青云亭之游,那是极其美好的影象。薛华娟帮忙录入了部分文档,亦足铭感。
不妨再谈一点私愿。从《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11年3月)可知,1964年,高罗佩写过一份“英文自传稿”,而且“在他的全体事情生涯中”,还有大量的“口袋记事本”,“每天系统地记下了去了什么地方,见到了什么人等等”。它们的史料代价极高,甚盼学者将之整理面世。此外,关于高罗佩的第一手材料,还有很多用英、荷、日文写成,辑录出来,想必也是“好用”的吧。这固非我的能力所及,但作为沾恩于高罗佩多年的读者,究竟还是满怀期待。
(此文为《高罗佩事辑》增订本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