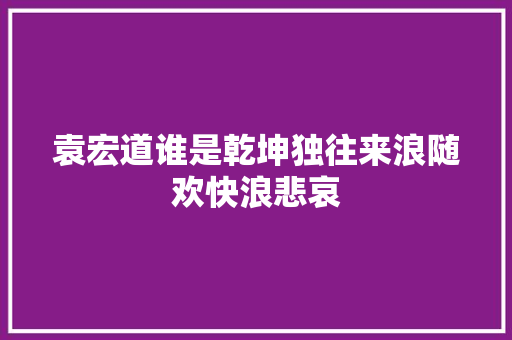明万历乙未(1595)年,朝廷任命一才子担当吴中县令。而刷爆才子朋友圈的,不是他风光上任的事情,而是他上任伊始致朋友们的书信:
"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心腹,生公说法石有长老。"
吴中人若知此书信,肯定对此君不寄厚望:呜乎哀哉,来了个“玩主”。孰料,才子上任后却励精图治,他创造衙吏办事疲塌,百姓多有怨言,立即动手整顿吏治,实行"升米公事",来办事的在县城吃一顿饭的工夫,事情就可以办完了。明史赞他“听断敏决,公庭鲜事”。办事效能提高了,衙门里自然就少事情了,此君又规复他玩主的真面孔:两年内玩遍吴中山水。但毕竟身在官场,他以为"吏道缚人",极不自由。他给朋友们写信,大吐当县令之苦水,说县长是集“奴才”“妓女”“牙婆”于一身: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
发发牢骚吐吐苦水也罢,但此君竟七次上书朝庭请辞。当时宰相申时行感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朝庭准了他的辞呈,他如脱笼之鸿,在书信中欢呼雀跃,再次刷爆朋友圈:
“败却铁网,冲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
不可言!
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这个活脱脱的宝贝姓袁名宏道,字中郎,与兄袁宗道及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风,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见,创直抒胸臆的“公安派”,开一代清新轻逸的风气。
袁宏道随性率真,天性活泼,仁山乐水。他的生平如他自己一句诗:谁是乾坤独往来,浪随欢畅浪悲哀。他推崇李贽的“童心说”,以性灵为文,以诚挚处世,不让自己脑袋成为程朱理学的赛马场,言他人之所未言,发古人之所未发:为《金瓶梅》张目;兴趣创作《瓶史》等作品。
袁宏道是从董其昌那里得到《金瓶梅》,但有残缺,读了之后爱不释手,立马写信向他要后段。
“《金瓶梅》从何处来?伏枕略不雅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袁宏道后来又把巜金瓶梅》转借给谢在杭,见谢久久未还书,急急写信催还,可见他对此书有多爱:
“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
袁宏道是肯定《金瓶梅》文学代价的第一人。此前,《金瓶梅》只在民间传读,袁宏道“云霞满纸”评语一出,《金瓶梅》大传。诸位看到这里,心中窃笑:这明末文坛领袖怎么这样,推崇“淫书”?我把袁公的人生“五快活”不雅观给你看看,你可能更是大跌眼镜: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来宾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奇。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支配,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乞食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对付前四种快活,大家都说我也想呀但条件不许可呀。可对付第五种快活实在难以苛同。一败涂地,沦为托钵人,还是快活?好你个中郎,居然说“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可静心细想,他这不同凡响的语句是不是在说生命的妙处是充满无限的未知性,对他这么一个洋溢着生命激情亲切的人来说,快乐不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在四书五经中见多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文章,在这些文章面前我们自惭形秽。袁公手执《金瓶梅》眼一斜:“别听他们扯犊子,他们和我们一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们便是喜好美食,喜好美女,喜好饮酒吹牛,喜好游山玩水秀朋友圈,爱咋咋的,怎么啦?”
图片来自禅艺会"大众号
袁公道生就这样纵情山水,及时行乐。他认为人生最难得的是个“趣”字:
“众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 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 猎古董,以为清;寓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喷鼻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色!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 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 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落小儿百姓,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
追求“趣”就要有“癖”:“众人但有殊癖,终生不易,便是绅士。”他喜好折花插瓶,写了一本巜瓶史》,巜瓶史》是写花与瓶的书,在日本得到很高的评价,日本插花艺术家望月义想说:"插花之有《瓶史》犹如礼乐有巜春秋》” ,因此日本有所谓“袁道派”的插花。袁中郎说折花插瓶是幽人韵士摒绝声色而钟于花竹的嗜好,书中讲折花插瓶有很多讲究,但总觉得讲的是花与瓶搭配的“自然”之美。聪明绝顶又任性诚挚的袁中郎硬是“玩”出了学问,真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尤为夭。周国平师长西席说,袁中郎是个充满生命激情亲切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彷佛不要命似的。爱山水,便说落雁峰"可值百去世";爱朋友,便叹"以友为性命";读书读到会心处,便"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站在烟波浩淼的长江边上,慢步在“树之森森”的古公安大地上,思慕中郎的洒脱人生,耳衅又响起他“胸臆流出”的《偶成》:
谁是乾坤独往来,浪随欢畅浪悲哀。
世情到口居然俗,狂语何人了不猜。
彭泽辞官非为酒,漆园曳尾岂无才。
百年倏忽如弹指,昨日庭花烂熳开。
参阅《瓶史》、《袁宏道集》和袁行霈师长西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