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数都是酒鬼。
刘伶一醉三年,大梦不醒,现实生活中的不快意被寄托在了酒这个奇妙的事物上,醉生梦去世多好,醒来看着晋王朝的阴郁,那种痛楚比去世愈甚;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师长西席,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哪有什么\公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定命复奚疑“的豁达。
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酒总归是苦涩的。但是沙场上的酒,则会一扫之前的小家子气,变得苍凉悲壮起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立时催。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在沙场上及时行乐也没有什么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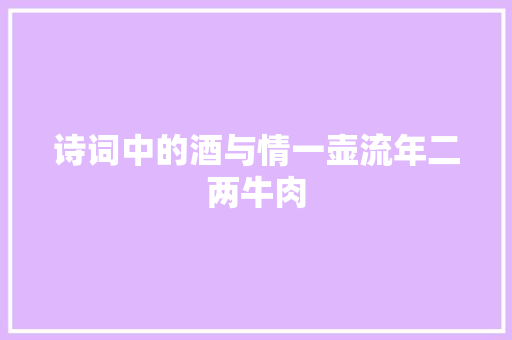
朋友聚会须要酒,流觞曲水的兰亭集,亲人聚会也须要酒,春夜宴桃花园从弟,所有的聚会都是无酒不欢的,当然有了酒也未必愉快,狂欢只是一群人的孤单罢了。
苏东坡倒是把酒喝出了新境界,纵然老了也依旧英气干云,他唱“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比较于同时期的柳永不知赶过了多少格调,柳永最洒脱的一句话大概便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大多数时候都是沉浸在温顺乡里,在万花丛中乐不思蜀,偶尔感慨一下他的小别离“都门帐饮无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柳七的境界乃至还不如“三杯两盏淡酒”的李清照来得让人怜惜。
纵然到了明清之际,诗词开始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便是小说,《水浒传》中,大碗饮酒,大口吃肉,成了绿林豪杰的标配。
酒,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大放异彩,成了人们借以忘忧的存在,可文以载志,那些隐蔽在酒的背后、入木三分的苦涩诗句,一句句都是对生活的神往。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比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看似荒诞不经,疯言疯语,可是谁也别忘了,酒后才吐真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篇里,如此多的酒,大概便是这个缘故原由了吧。
一壶流年,二两牛肉,梦里青稞未熟,醒来已是黄粱熟透······
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