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女
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车。
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华。
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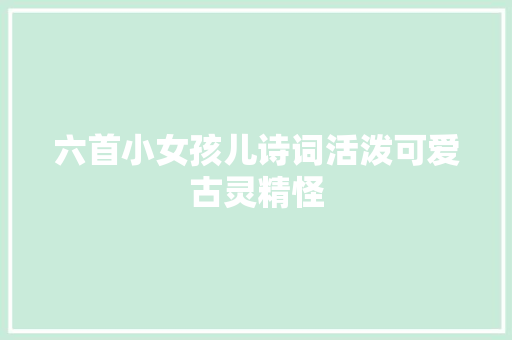
刚刚到了呀呀学语的年纪,一晚上都不肯睡觉,要玩她的小车车。墨客无奈被她哭闹折腾了一晚上,后来才创造,她是由于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色的花朵。
大才子是相称有耐心,花了一晚上的功夫,终于知道女儿的哭闹是由于衣服上少了一朵金花,这得是多么疼爱女儿的父亲啊!
绝大多数父母,对女儿的疼爱,顶多是溢于言表。但唐代墨客施肩吾则远远不止于此,他以为该当溢于诗表才行。于是,他写下了如下的小诗:
幼女词
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
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月牙。
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月牙
六岁的小女孩儿,一片天真烂漫,根本不知道巧与拙的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乞巧。但可爱的是,她也在七夕节之夜,堂前学人拜月牙。
毫无疑问,小孩的模拟能力强,但小女孩儿,天生不会模拟打打杀杀,而是模拟拜月乞巧,真是太可爱啦!
再稍大一些的女孩儿,十分乖巧可爱,会试着帮家里干点活了。如果是田舍的女孩,放牛则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唐代墨客于鹄就写诗描写这类场景:
巴女谣
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
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荷叶和菱叶密密麻麻,挤满了江边,女孩骑着牛,牛清闲地吃着草,女孩唱着旋律幽美确当地竹枝歌。不久,天快要黑了,但女孩也不愁记不记得回家的路,由于我知道我家门前有一棵芭蕉高高地挺出了木槿竹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天色逐渐晚了,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还是一个劲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听任牛儿不紧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敦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入夜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
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才不害怕呢!
只要瞥见伸出木槿竹篱表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便是我的家了!
就问你,天不天真?可不可爱?
4. 《蟾宫曲·寒食新野道中》,卢挚不足为奇,像上述天真烂漫的女孩,也涌如今元代词人卢挚的词中,她们高枕而卧,活泼可爱,古灵精怪:
蟾宫曲·寒食新野道中
柳濛烟梨雪参差,
犬吠柴荆,燕语茅茨。
老瓦盆边,田家翁媪,鬓发如丝。
桑柘外秋千女儿,髻双鸦斜插花枝。
转眄移时,应叹行人,立时哦诗。
桑柘外秋千女儿,髻双鸦斜插花枝
墨客来到这淡柳如烟,梨花似雪的小小村落寨时,完备被这里的春意所沉醉。虽然放慢了马蹄,但柴扉里还时时时传出犬吠,几只春燕在茅屋顶呢喃飞舞。鬓发如丝的老翁老妇们正怡然自得其乐;隔桑林望去,几个梳丫角的小姑娘正愉快地荡着秋千戏耍,这统统如此自然和谐。小姑娘们梳着两个抓髻的上面斜插着花枝,一双媚眼顾盼多情。她盯盯地看了很永劫光,可能会惊叹我这个赶路的人,在立时还在吟咏诗文。
实在,墨客在借小姑娘们的天真烂漫之心,反衬出墨客自己流连于官场,蝇营狗苟,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庸俗之心。
5. 《南乡子·画舸停桡》,欧阳炯再稍稍大一些的女孩,就一点不怕生人了,大大方方的谈天,乃至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约请客人到家里做客。五代词人欧阳炯就写词描述了这个场面:
南乡子·画舸停桡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
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
笑指芭蕉林里住。
笑指芭蕉林里住
画舫在水边稍作勾留,岸上,槿花竹篱外横着一座小竹桥,风景让人陶醉。关键是游人还有更美的风景,他正和沙滩上的少女闲聊了一阵,少女要回家,游人连忙问她住在哪里,少女笑着转头,指向芭蕉林,说,在那里。
怎么样?一个含情脉脉的少女形象是否跃然纸上!
如果说,是哪首诗词,把一个“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的少女形象描写得最到位,那一定是易安居士的这首《点绛唇·蹴罢秋千》,全词写到:
点绛唇·蹴罢秋千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顾,却把青梅嗅。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她荡完秋千,正累得不愿动弹,溘然花园里闯进来一个陌生人。“见客入来”,她感到惊诧,来不及整理衣装,急忙回避。“袜刬”,指来不及穿鞋子,仅仅穿着袜子走路。“金钗溜”,是说头发疏松,金钗下滑坠地,写匆忙惶遽时的表情。“和羞走”三字,把她此时此刻的内心感情和外部动作作了精确的描述。“和羞”者,含羞也;“走”者,狂奔也。然而更妙的是“倚门回顾,却把青梅嗅”二句。它以极博识的笔墨描述了这位少女怕见又想见、想见又不敢见的奇妙生理。末了她只好借“嗅青梅”这一细节掩饰笼罩一下自己,以便偷偷地看他几眼。
是不是一个天真纯洁、感情丰富却又自持的少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