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作于何时?
既然知道《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的“诗母”,那谁又是《古诗十九首》的“诗母”呢?与此干系的问题是:它是什么时候“生”出来的呢?
听说,猴子吃了一个喷鼻香甜的水蜜桃后,立时又伸“手”向人要另一个,它绝不会追问水蜜桃的产地,可人在吃水蜜桃之前,就要去弄清楚它产自何地(特产)?它产自何时(日期)?它产自何树(栽培)?人虽然也属于动物,但是世上最难缠的动物。
《古诗十九首》让民气醉,人们自然会固执地问:它作于何时?又作于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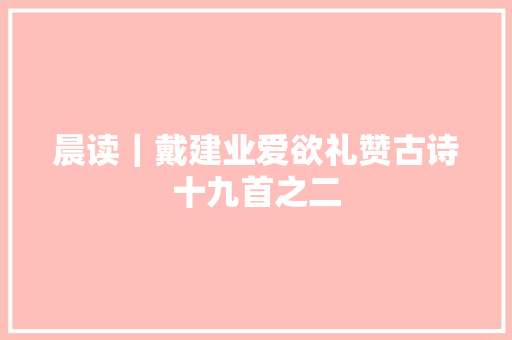
为此争吵了一千多年,可能还要一贯吵下去,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可能永久也找不到确切答案。
《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年代及其作者,在南朝时便是一本糊涂账。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将个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锺嵘在《诗品》中却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枚乘生动于西汉早期,傅毅属东汉初期,曹植和王粲又属曹魏。徐陵、刘勰和锺嵘同为梁人,对作者归属和作品年代,三人虽然没有同台吵架,但完备是各说各话,而且他们也是道听途说,“或”“旧疑”如斯,显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张。后来七嘴八舌就更多了,有的说是张衡,有的说是蔡邕。实在,西晋陆机就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把自己的仿作称为“拟古”,梁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在诗题下注得明明白白:“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古诗十九首》诗题纯属有时,刚好这些诗歌都没有标题,刚好是前代传下来的“古诗”,又刚好收录在《文选》中的只十九首,以是人们就随意把它们称为“古诗十九首”,久而久之这叫法就成了标题。往雅处说,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号交响乐,往俗处说,就像屯子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样,有多少个就叫多少,数字完备是凑巧。
既然“不知作者”,为什么冒出来那么多说法呢?越是大家都没有证据,越是大家都有胆量,反正每种说法都去世无对证,因而每种说法都无对错之分,纵然胡说也不会使自己名誉受损,更不会引起任何轇轕,于是,人手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不过,虽然不能指定它们作于何人,也不能考出它们成于何年,但我们可以根据诗歌内容、风格和情调,大致推断它们产生于哪个历史阶段。也便是说,依据诗里诗外的“蛛丝马迹”,往返复中兴或靠近事情的原形。一贯以为自己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本日借助古人的研究成果,我恰好来小试牛刀——
由于西汉避讳极严,不避君讳属于重罪,东汉则不必避讳西汉天子。西汉第二位天子刘盈,《古诗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喷鼻香盈怀袖”,可见,这些诗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汉的作品。《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说到“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西汉建都于长安,洛阳不可能如此壮丽繁华,董卓之乱后“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那时洛阳已没有“双阙百余尺”的巍峨宫殿,显然《古诗十九首》不会写于建安期间,更不会在建安之后。东汉前期班固《咏史》诗质木僵硬,中期往后五言诗才渐趋成熟,从诗风诗艺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这种“动天地,泣鬼神”的精品,到东汉后期才可能涌现。
《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对去世的恐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那对生的留恋,“良无盘石固,浮名复何益”那对功名的舍弃,“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那对爱情的器重,“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那对爱欲切实其实定,还有“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那及时行乐,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二者在韶光上先后相接,在代价取向与情绪体验上又一脉相承,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几十年或十几年,绝大多数诗歌作于汉灵帝与汉献帝之间。
它们并非写于一人,也非写于一地,又非写于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