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在苏州名妓朱弱生家,见了一个妹子朱小娟。那妹子轻烟一缕入眉生,眼角溜波明。鬓蝉云深,靥含霞浅,唇着些猩。把个尔陈的心也相走了。
尔陈对弱生道:“西施涌现了,若不配我范少伯,对了吴王也枉了这生平。”赖住不肯,要斟酌入马。弱生道:“和尚带网子,早哩。他还没有梳拢。”余尔陈道:“任你要多少银子使费,我今日就梳拢他。”弱生道:“好急性子。这还要择日过礼,岂可如此唐突?”
这余尔陈等的心急,弱生早看在了眼里,势要敲得他一笔出来。遂说道:“你只见了我家小娟外面,还不知道她的内材。性情极温顺,措辞极俊雅,识得字,也会写字,是一个不戴儒巾的女中秀才。不知你有什么福分,才配得她。”余尔陈道:“我这月老祠(媒人)不弱,也要凑得来,说得凡是无钱弗成。”
这痴心人梦里都在小娟身上,那里还顾得什么钱财。能用一两银,断不用五钱;娼家要两件,断不敢出一件。哪里知道,这些娼家:洋洋如巨海,精卫不能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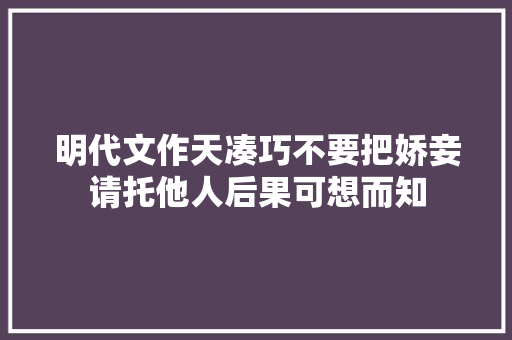
捱到那日,尔陈打扮得似一个齐齐楚楚的潘安仁。日高还未起来,他便来在了娼家楼牌上,吃些小酒,着着棋,打几次双陆,便是一日。总算不负有心人,得以与小娟相见。那小娟又喜弄些文墨,余尔陈便请教他撇几笔兰,又指示令她作几句歪诗,日子尽混帐得过。
一月有余,龟子斟酌给小娟寻一夫婿。余尔陈甚是恼怒,予了她些银子混过去,倒是小娟道:“这样也不是你的日子,也不是我的日子。他这样人家,银子填不满。你若有心,挈得我一同出去,便做小伏侍到底,我所甘心。”
余尔陈如梦初醒,便央弱生对老鸨说道要娶她。老鸨说道:“咱家坐下千来两债要还,逐日用度也须得两数银子,都靠着她。把她嫁了人,将什么还债?将什么过活?”尔陈又央弱生说:“或是三百五百,或是一千八百,凭她出一个价,我措置与他。”龟子道:“不卖是不卖,莫说五百,便是一千,我也断不与他的。”
这小娟只是倒在余尔陈怀里,哭将起来。余尔陈好生过意不去,想道:“我如今囊箧将空,家中没有寄来。三五百金,还须借贷。他如今竟不肯放一个嫁字口风与我,怎处?”
那便老鸨见余尔陈脱手慢,料他必是拿不出,于是便在小娟面前,红着脸儿发话道:“你自小儿吃穿,拜教你吹弹,也不知费尽了我多少心机,多少钱钞。我这般人家,说不得一夫一妇,嫁是不嫁的,莫要捱过了日子,两相延误了。”
余尔陈也涎涎的不好过,私下与小娟计议道:“我在此拿不出钱,不若回去,筹得了千金,再找上一个有势力豪侠,定要赎你回去。”小娟道:“你手底无钱,赎我也难。不若你先回去,再图谋罢。你去之后,我断不肯再抱琵琶;拼得打骂,我立心以去世自誓。他无或奈何,放我有之。”余尔陈道:“小娟与我作合,全恃贤姐。我此行当立致千金以赎小娟。”只是小娟含凄饮咽,好生不胜。那老鸨见余尔陈去了,不胜之喜。
余尔陈到家,极口称道小娟才德,所以为她流连,其妻极是贤惠的,并不阻挡,但千金也不是夙夜迟早有的。这边小娟并不肯相见客人,道:“我与余郎相约,并不从人。”鸨儿大怒道:“我家里要吃要用,怎并不从人?我今偏要你从人,看你硬得我过么?”那小娟只是闭门。
龟子恼道:“许你嫁一千两,决不九百九十九两放你出门。不许嫁,不怕你生了翅飞去。你道从良好么?从了良,撞了个狠大娘,教你在灶脚跟前,粗衣淡饭,老公不得近身,还要打折你的筋哩!
”先是骂,骂不肯,领几个子弟们进来,毒打上几场,小娟也就悬起梁来。这番,鸨儿更恼了,道:“你假如舍得去世,我也就舍得埋!
”心里却有了放她的主张。
余尔陈在家里设处,也将近就了绪。忽然那一日,小娟央篦头的王小九寄一字来,尔陈拆开,只见上写着行行往事。诉说昔日之情,及眼下受辱之事,那纸上泪珠点点痕迹犹在。
余尔陈也不暇寻势力之人,买下一条船星夜赶奔而来。正待拢船之际,只见先有一支座船靠岸,问了才知道,原来是他的社友江公子,刚打北京省亲回来。二人见了满心欢畅,江公子问余尔陈比来景况,因何在此。余尔陈便搭上道:“此间有一朱家小娟,小弟闻她色艺双绝,用三百金梳拢。她果真清而不寒,艳而不俗。”江公子道:“天下有这等美人?”余尔陈道:“这犹自可。更有妙处,他性情极温顺,能曲意承顺。若待颐指气使,也不灵变了。”
这一铺排,江公子更是好奇,遂说道:“既然这等美好,兄怎不娶了他?”余尔陈道:“小弟愿娶,她也愿嫁,有成约了。”江以子道:“果真么?”余尔陈道:“千真万真。小弟因到家下措置银子,为她赎身,奈何鸨儿逼她接客,她又不从,备受凌辱。她有字来。”遂即取出书与江公子看。
江公子道:“是她真笔么?”余尔陈道:“是。小弟与她相好两个月,笔锋、口气久已熟之。只是龟子可恶非常,小弟已具了千金,只是不谙事件,恐怕为他所欺,以是还须寻个能压伏得住的人才妙。”江公子道:“小弟如何?”余尔陈道:“恐不好劳台兄,囗制此龟便是胜券在握了。”
时座中有一个人,是江公子的表弟萧集生,陪堂惠瞻泉,也笑将起来。江公子道:“兄不必忧虑,小弟为兄作一古押衙。”余尔陈道:“若果真兄肯垂手,小弟宁愿将千金就送到兄处,凭台兄主持。”余尔陈得他承认,遂先去赶到朱家,与小娟通个喜信,道:“银子我已竟足了千金,还央我一个嫡亲江公子来管,乌龟不怕不允从了。你且耐心,只在一二白天停妥。”小娟遂不留他。
乌龟也晓得他定要来娶小娟,也不招徕他。余尔陈叫下一只大酒船,宴请江公子等人。次早,余尔陈将千金央萧集生,转送与江公子道:“有不敷的时候,小弟补上。”江公子道:“以小弟之力,自然随意马虎集事,料那龟子也断不敢多事。兄可移舟至石灰桥畔,到晚间弟自然护送如夫人至舟。”余尔陈道:“如此,小弟自然厚报兄德。”江公子道:“小弟原是爱怜佳人才子,出心愿为之作合,岂图报哉!
”
余尔陈又拿了二十两银子,予了江公子心腹管家极会作威福的人,许他事成了再更加酬谢。惠瞻泉、萧集生前有折席,如今折程,要他做帮衬。集生不收,瞻泉自笑纳了。他自己的船移在石灰桥边专待。
这边江公子,差上两个管家去叫乌龟。乌龟一到,这江公子大发雷霆之怒,道:“你这奴才,怎么哄骗余相公,赚他千金,又骗他五百多的聘金,还不与他女儿吗?”乌龟道:“小人怎敢?余相公为梳栊小人女儿,曾费过四十两。及至后来,余相公说把五百两要小人女儿,小人性便是一千两,也不肯卖。何曾见他五百来?”
江公子道:“这奴才什么人物,开口就说一千,明是诈他。如今我要这女子,抬来看,若生得好,与你三百两,要不肯,余相公替我老爷带去的俸资一千两被你骗去,定将你送到县家追罚,把你女儿官卖抵债,叫你人财两失落。”
乌龟道:“天理良心。余相公消费得百十两,也是理所应该的。相公说要我家女儿,小人实是一家所靠,与不得哩!
”江公子叫掌嘴,小厮过来几个大巴掌,叫写贴送到理刑厅去。那惠瞻泉便过来打合道:“你这厮好不会说话,你该说养活女儿一场,三百两不勾,求再添些,假如到官去,官肯为你么?”乌龟道:“这女子实是一家所靠,求相公方便些。”惠瞻泉与管家说:“给他六百两。”五百两乌龟得手,一百两管家与惠瞻泉。当面立下了一张卖到江处文契,即刻抬人。这小娟却也喜孜孜的上了轿来。
这厢余尔陈整衾绸,焚完水,笔床茶一,只待西子作五湖游。忽见一个人急急忙忙的赶到,道:“江相公拜上余相公,龟子被相公拿来打急了,投水去世了。公子怕有口舌,清闲收拾,叫相公作急先回。”余尔陈听了,果真连忙作速开船。不知朱小娟已竟自到了江相公的船上了。
实指看见余尔陈,至走入官舱,不见余尔陈,却见一个:朱色履,姿罗衫,短须猬桀带微黄的男子。小娟一见,便知道是江公子。上前道了一个万福。江公子笑道:“果真一个年夜大好人。”便一把绾住了手道:“小娟,你知道么?余尔陈因措办不出千金来,今已将你让与我了。”小娟急忙作色,把身子让开道:“岂有此理!
他昨日面言,以千金托公子娶我,不要取笑。”
公子道:“岂是取笑?那龟子的左券,都写到江处了。”小娟道:“这不过是借意。”公子道:“娶妾可是借得的?你看我声誉人品,与究酸远甚。”小娟道:“贱妾誓奉余郎巾栉,贫富原所不论。”公子道:“余生自已弃了你,你何必还恋他?”小娟道:“断无此事。公子,负友之托不义,夺人之配不仁。小娟此身以去世自誓,再不他适。”
公子不再搭话,只是把身子逼将过去,小娟用手猛力一推,一个逼到东边,一个避到西边,团团似元宵走马玩灯的一样。小娟大叫道:“江公子威逼去世人!
”推出舱门,却待去投水,刚巧萧集生、惠瞻泉正在舱门以外,急拦得住,拥入舱中。
惠瞻泉道:“公子,五字经欠念得熟,这势力只可使在那乌龟身上去。”萧集生道:“罢,以义始,以义终罢。”江公子也恼道:“我不怕她七碗跳到八碗里去!
”扰了半夜,因怕她叫喊投水,只得各自打个铺。
却说那余尔陈到了家,无日不差人打听。知道江公子已到了,着人问信,遇着船上伏侍的小厮书童,问他:“乌龟投水去世,怎么了?”书童道:“乌龟是识水的,会去世?”又问道:“小娟可讨得手么?”书童道:“得手了,又不得到手。”余尔陈好生鹄突,忙去见江公子,江公子在庄上;见萧集生,萧集生拜客不在家;见惠瞻泉,惠瞻泉正待出门。
惠瞻泉回答对他说:“所托之事,学生已尽费调解。但老江有自为的意思,那小娟倒是很钟情于兄。如今在他的庄上,兄可速去见老江,但不可说是我露的。”此时,江公子哄着小娟,说前日预备的赎身银,是江公子的。还把她带在了自己的庄上,一座得月楼里,令庄婆伺候。
余尔陈持续走了两日,恰好遇着江公子拜客回来。坐定,江公子道:“前日为兄费尽了多少调解。”余尔陈就侵一句道:“借兄之大力,小娟已在贵庄上。我今日特来相谢,领回小娟去。”江公子听了愕然,道:“正是有些难说!
当日立文契的时候,说好为兄出色?写了江处的文契。若是今日还兄,是小弟经办;只是一时见财起意,小弟就收用了,容改日再奉还罢。”
余尔陈道:“兄怎么这样?兄以豪侠自许,小弟遂以千金相托,此乃负话了。”江公子道:“兄去寻一个千金分上,待小弟发一封家父书,其物兄得,就不相负。”余尔陈道:“我不要千金,我只要此女。”
江公子道:“这却断断不可得的。辟如兄拿千金要她,她不能来,请教贤兄,若是兄应得的妾,小弟何苦来白出此憨力?”余尔陈道:“此女贞心,断断不肯从你。”江公子道:“这不须兄忧虑。俗话说得好,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余尔陈道:“兄假如再坚执,我就遗书令尊,出贴相揭了。”江公子道:“这却不妨。兄若慨然,银子还可以得;若不然,人财就两失落了。”余尔陈气得面孔通红。他是一拱,道:“小弟要与小娟少叙,不得作陪了。”
余尔陈不平得紧,果去见告乡绅,他的亲友。这江公子也是丑驴有名的。众人不过混帐说几句好看的话,谁肯去管闲事?众人也渐把他做痴物厌物不理。但屡次去访小娟,终不肯相从,他越的不能舍了。
那一日,在路上遇着萧集生,说江公子负心,又说小娟不肯失落节,至于泪下。萧集生怜他,道:“你原不识人,你看这干人,他肯为人么?若是小娟矢去世守身,三日以内,当令连城复还。”余尔陈道:“兄若果这般伸手,小弟就当面拜跪了。”言罢,就倒身跪将下去。萧集生道:“兄何故为一妇人,至于如此?兄暂且忍心耐意,弟自然为兄力争之。”
越日,江公子的内人因母亲寿日,乘轿出门。却见一个小厮,怀中微露一个封筒,探头探脑,走近轿前,又缩了回去。问是夏相公家的小厮,有字与相公。叫取来看,道:“分付面送的。”江娘娘叫:“取将过来。”小厮来夺的时候,已竟是送到江娘娘面前了。
江娘子见其古怪,料知必有原故,忙将封筒拆开不雅观看,原是一幅花笺,上写着:足下自灵岩来,挈有美人。余即之镜终破,而江郎之魇觉矣。得月楼头,清辉与艳色相映,不令人妒杀乎?明晚一觞相庆,幸虑狂朋酣饮,娱我良宵也。弟名不具。
这娘子也是极有才略的,见了这字,道:“他在苏州娶了一个女子来了。‘余即之镜破’是有夫之妇,‘得月楼头’是瞒我藏在庄上。我且拜了寿,再作区处。”才拜的寿完,饰辞心疼得紧,要作速回去,姐妹们也留不住他。还叫不要与公子知道,胆怯动他。只令文童随来,这是京中随回来小厮。出得门道:“想是连日忧郁缘故,且到庄上去,消散一消散。”文童在轿后,心里突突的似舂凹谷。一到庄前,庄婆惊的尿滚屁流。那娘娘下得轿,竟上月楼来,见一个妇人在楼上:
泪界残妆着露花,鬓云慵绾得欹斜。
玉腮斜托劳纤指,思绕巫山第几涯。
管庄婆道:“娘娘来。”这妇人忙起身向前道:“娘娘万福。”这江娘娘看他举止端雅,虽颜色愁惨,容华自是出众。使问:“你是谁家妇女?”妇人性:“小娟朱氏,秀士余尔陈配妾。”娘子道:“余尔陈不是我相公的好友?”小娟将前事逐一道出。
娘娘道:“这情果是真的么?”小娟道:“娘娘跟前,妾怎敢相欺?”娘娘便叫文童,文童惊的面如死灰,战抖抖的做声不出。娘娘道:“这不干你的事,不难为你,你自管直说。”
文童道:“前在苏州,有一个余相公来拜,说要讨这小娟为妾,那乌龟不肯,要相公出来为。第二日,送一千银子与相公。相公叫乌龟来要买他,只用得六百银,讨了这妇子在舡中。相公曾要合她同宿,她坚执不肯,后送到这里。”
又问庄婆:“他两下曾相好么?”庄婆道:“相公倒是常来,来时必定吵闹,相公从此恼了去,想是未曾好。”娘娘便叫过文童来:“你快去请余相公,去请了来,我好问个明白。”文童道:“小的不认得。”娘娘道:“你若不去,来迟打去世!
”文童只得去了。娘娘叫小娟坐下,道:“我家也有几个妾,不是不能容你。但你是朋友之妾,岂可强占?你可检点奁妆,待余郎到,你随去。”江娘娘也去看公子囊橐,果是一张六百两身契,那四百两封识宛然。
这边余尔陈在家期待萧集生的好信息,却见文童飞来道:“相公在庄上相请。”余尔陈道:“想必是集生劝得转意了。”忙叫了一乘轿,二个家人奔将来。到庄中不见江公子,却见小娟,两个喜不自胜。小娟道:“幸得江娘娘开恩,今我随你同去。可叫乘轿,两个人来取嫁奁。”余尔陈道:“轿与人俱在此,可作速谢了娘娘,迟恐有变。”小娟便折身来谢娘娘,娘娘道:“似你这样人品,我綦重你,但强留了在此,于理不可。”便把文契与了他,把这四百两银子也赠他拿出来。
余尔陈道:“我当日原拼千金娶你,这四百两是他出憨力省的,若取去,结怨必深。”再不可收。把肩舆让与小娟,自己随后。两个家人挑着小娟铺陈,四个花梨木箱,原也是余尔陈办的。江娘娘又叫文童:“送余相公家,回话我才回家。”这也是江娘子严密处,怕路上遇着江家人,或至留难生事,说个娘娘差送,自不敢动了。
余尔陈到家,引小娟参拜了大娘,取二两银子赠了文童。两个叙不尽离去相思之苦,赚掇凌逼之恨。只不知何以江娘子出来,使他夫妇完娶。那边江娘子毕竟等了文童回报,然后回家。
江公子到酒散回来,文童把这事逐一说知。江公子闻听大惊,要追也追不及了。文童说的,做出这事,要问娘子。这娘子是个极会讲道学话的女子,江公子哪里赶去寻问。心上道:“早知如此,不如先前依了萧集生,义始义终,还能得个豪侠的名色。如今:曲栏寂寂画楼空,檐马叮当啸晚风。帘畔美男何处去,一轮明月自庭中。”
越日,余尔陈去见萧集生,道:“幸得江娘子到庄中,小妾诉出强夺之事,竟得送归。”萧集生点头付之微笑。不知这全是萧集生揣定江娘子性情,这缄儿全是他弄的。
这可见江公子一团假义气,全是为己,那是为人?到不如萧集生不动声色之中,竟为余尔陈完了这事,全不露出,全不居功。这便是真豪侠,断不在嘴上。
译自《天凑巧》第一回:假侠夫千金空托 真义士一缄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