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尔逊就笃信扶乩,缘故原由是有一次他曾经亲目睹到乩盘上写出了一首古代希伯来文诗词,这绝非江湖术士的学问可以假造;而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家族也常常在自己家里组织扶乩会,听说有一次达尔文还参加了。达尔文的好朋友、同为著名生物学家的赫胥黎对扶乩的崇奉在有无之间,以是抱着“因以存之,莫敢废之”的态度频繁的出席各种扶乩活动。而达尔文的生平之敌,另一位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则是对扶乩笃信不疑。
据徐珂于《清稗类抄》中记载,晚清时扶乩的办法是:
“术士以朱盘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悬锥其端,旁边以两人扶之,焚符,神降,以决休咎。即书字于沙中,曰扶乩,与古俗卜紫姑相类。一曰扶箕,则以箕代盘也。”
也就说,扶乩须要准备一个朱红漆盘,盘中盛有白色细沙。如果没有细沙,则代以灰土。将一支乩笔固定在一个筲箕或竹、铁圈,。扶乩的时候,旁边各一位人执筲箕的一端一直地在沙盘上写字,并祈祷神灵的降临。同时乩人所书笔墨,会由阁下的术士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后以为神谕(扶乩的反对者们戳穿所谓的神谕都是由术士将事先编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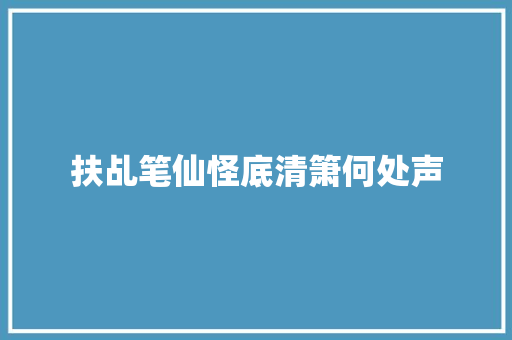
扶乩的起源是一个十分悲惨的传说。据南朝刘敬叔《异苑》卷五记载,这种崇奉最早是为了安抚一个命运悲惨的少女。此后随着韶光的流逝,人们又在这个传说上增长了更多的细节。到了宋代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完全的故事,并引起了苏东坡的同情,他为此写了一篇《子姑神记》,个中阐述道:
“元丰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师来黄州。二月朔至郡……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复降于郭氏。”予往不雅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
之后,紫姑神又向苏东坡“以箸画字”,讲述了自己的出生:紫姑神是寿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是一位有文化的女性,后来嫁与伶人为妻。唐垂拱中,寿阳刺史(李景)垂涎于何丽卿的才色,将其夫害去世,并将何丽卿霸占。受到冷落的寿阳刺史夫人迁怒于何丽卿,将这名无辜的少女杀去世在厕中。并且何丽卿还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也便是说紫姑神不止一位,而是有很多。但是何丽卿是个中非常卓越的。
实在,苏东坡师长西席笔下的这位紫姑神便是他自己,由于两人都是遭遇坎坷但仍容能够善意的对待着这个充满恶意的天下。乃至苏东坡还概括了何丽卿非凡的文学成绩、品味:
“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革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
这完备是苏东坡对自己前半生文学造诣的役夫自道。
一位德鲁伊教祭司在举行仪式。
旧时各地皆有“迎紫姑”崇奉。迎请的办法也大多是充满了德鲁伊式的诡异审美和窒息感。《异苑》、《齐谐记》皆称:“于正月十五昼夜,作其形,衣以败衣,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稽神录》云:“正月望夜,江左风尚,取饭箕,衣之衣服,插著为嘴,使画粉盘以卜。”《游宦纪闻》云:“请紫姑,以著插筲箕,布灰桌上画之。”而明末刘侗在《帝城景物略》详细的记载了明朝华北地区对紫姑神的敬拜活动:
“望前后夜,妇女束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即紫姑),两童女掖之,祀以马粪,打鼓歌马粪芗歌”。
关于紫姑神崇奉的起源、为何会与扶乩挂上关系?这种考据到了宋代已是众说纷纭了。但总得来说,紫姑是厕神,实际上是类似灶神、井神一样,都是家庭的守护神或者居住在家庭中的神灵,以是“县官不如现管”,紫姑神更易于“感应”,以是古人在扶乩时大多乞灵于斯。
往远了扯,紫姑神的起源可能和汉代对阴神玉女,也便是道家六丁的崇奉有关。
葛仙翁说六阴玉女(即六丁玉女)易于感通,可以占验。而道家经书中也说沐浴时可以呼召六丁,可知六丁玉女很随意马虎感应,可以通过用法术招摄过来占验。
关于六丁玉女与厕神的关系,可以看务成子表明的《黄庭外景经》。除六丁玉女之外,尚有十二地支玉女,即张天师在蜀中盐井所见的十二位女神。在被张天师度化之前这些女神有邪恶的一壁,比如蜀人常常以美少年作为敬拜,去献给玉女做丈夫。而这些特色都意味着最初关于六丁玉女的崇奉都属于阴神——也便是鬼仙的崇奉。
安倍明朗有一句名言:‘’人,太须要一位神了。
当然,更有人指出紫姑便是惨去世于厕中的汉戚夫人。但不管版本有多少,到了唐宋之时,紫姑神的降神仪式已经和近代的扶乩基本上完备相同。
明清之际,社会日趋成熟,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加繁芜,而上流社会尤其如此。为了有一个更安全的倾诉工具,平日敬鬼神而远之的士大夫阶层也纷纭开始以扶乩的办法隐晦的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而此时显灵的鬼神也不再只有一个紫姑。而是上到天尊佛祖下至孤魂游鬼无所不有。比如《明史·蓝道行传》就曾经记载:方士蓝道行(也是阳明心学的学者)以扶乩术得幸于明世宗,为了救天下于涂炭,搞垮权奸严嵩,蓝道行假托乩仙之言揭破了严嵩的恶行,导致了明世宗与严嵩之间开始涌现缝隙。之后严嵩与方士田玉勾结,也以假托乩仙之言诬陷蓝道行欺君,蓝道行因此被斩。此时一贯藏在幕后的徐阶向明世宗指出了扶乩危害:
“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落,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
于是明世宗又诛田玉等。此时扶乩已经和事关天下兴亡的政治斗争挂上了钩,无关乎当时的士大夫无论愚贤正邪都乐此不疲的沉溺于个中。
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乾隆帝统治下的大清皇朝就像一枚熟透的果子挂在枝头,虽然光鲜无比,但是却早已散发出糜烂的气息。岁月静好的结局毕竟谁也不敢,也不忍心去多想。既然此刻的繁华注定难以为继而未来又不知向何处去,以是全体社会弥漫着一种颓废和神秘的气氛也就不足为奇。求神、问卜、通灵、降神的活动随处可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条记》虽说在文学史的评价之上远不如早一个世代的《聊斋志异》,但是透过一个又一个或哀愁或荒诞的怪谈背后,众人更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绝望。个中以扶乩为主的故事多达四十三则之多。
但是纪晓岚本人却对扶乩保持这一种不敷与外人性的态度。他首先不承认真仙真佛会在乩坛上显灵,之后更进一步指出很多降神诗文都是术士自己的手笔,乃至是剽窃他人的作品。不过纪晓岚却没有彻底的否定扶乩的“真实性”。
由于在一个祸从口出的社会中,唯一不会祸从口出的只能是那些非人类的存在。时期的禁忌在鬼神身份的掩饰笼罩中被暂时放下,而在这个次元中,从国法律令到人情往来都变得可以商量。这对付当时的文人来说无异于是一处桃花源。
康乾盛世,实在也不过是一家之言。
书中这个故事尤其令人不能忘怀:
“多小山言,尝于景州见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摇撼良久,书一诗曰:薄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知为缢鬼,姑问姓名,又书曰:妾系本吴门,家侨楚泽。偶业缘之相凑,宛转通词;讵好梦之未成,仓皇就去世。律以圣贤之礼,君子应讥;谅其儿女之情,秀士或悯。聊抒哀怨,莫问姓名。此才不减李清照,圣贤儿女一联自评亦确也。”
降神的是一个吊去世鬼,丧失落了爱情和性命,乃至也不敢奢望同情。
一个冰雪聪明的人物,一段永藏心底的秘密。
人生凄凉和执着,真实而渺茫。
如今,扶乩虽然依旧随处可见,但已不复当初的人文和风雅。这便是为什么现在的“笔仙”,再也见不到那些或声名赫赫,或默默无闻但无一鄙人干可人的神仙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