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华诗词杂志 本日
诗学“三命题”浅议罗 辉
所谓诗学“三命题”,是指“诗言志”(《尚书·尧典》)、“诗缘情”(陆机《文赋》)与“诗缘政”(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这三个关乎传统诗学本原的问题。个中,“诗言志”中的“言”字,一“言”中“的”,表明诗不同于文,后者主发议论,前者主抒怀志,解释诗是用来话志向、抒怀抱的一种特殊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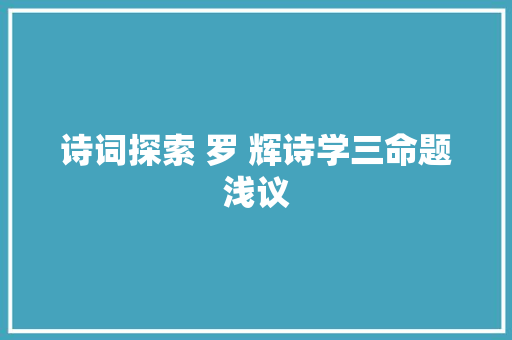
在汉字中,“志”与“情”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从广义上讲,“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正义》)从狭义上讲,“志”与“情”亦有细微差别。在《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下同)的“字源”与“释义”中,“志”的“字源”为:“在小篆中志是形声字,心为形,之为声,一说,之兼表义,表示去、往与心合起来为心意所向的意思。后来讹写作士,这个字遂写作志。志的本义是意念。”“志”的“释义”为“志愿、志向”。曹植《杂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彭端淑《为学》:“人之立志。”此外,还有“影象”、“记录”等意义。“但是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朱自清《诗言志辨》)“情”的“字源”为:“情是形声字,‘(心旁)’为形,青为声。情的本义指‘人的阴气有欲者’,即指人的喜怒哀乐等生理状态。”“情”的“释义”为:一是“感情,感情。”如《荀子·正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之情。”又如白居易《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二是“爱情。”如白居易《长恨歌》:“惟将旧物表深情。”三是“实情,情形,情态”。如《论语·子张》:“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四是“志向,意志”。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显然,“志”与“情”两字的“字源”与“释义”见告我们,一是立足于“诗言志”,“情”亦有“志向、意志”之义,以是说,“诗言志”亦是“诗言情”。二是从“志向”释义上理解“志”与“情”,两者都表示为追求“理性”目标,诗的题材无不与“大我”,即时期、国家、民族、社稷等方面有关,诗的代价取向直接关乎政治。“志”与“情”两字“释义”中的举例,就充分解释了这一点。三是“情”字的“含义”比“志”更宽泛,除“志向”以外,还有“感情、感情”与“爱情”等含义,这些方面直接表现为个人的好恶喜怒哀乐“六情”,更表示为“个性”与“感性”特色。四是从《古代汉语字典》在“志”“情”两字“释义”的举例“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与“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可以看出,哪怕两者都有“志向”义,但在“理性”与“感性”方面,仍有程度高低之别。朱自清认为,两处见于《论语》的“言志”这个词组,“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正是发抒怀抱”(同上)。联系上述例句,言“志”情系“大我”,多关乎“治国”;言“情”,哪怕是言“志向”义,却多关“修身”,牵扯“个人”的内容相对更多一些。也便是说“志”的“理性”常高于“感性”,“情”的“感性”常高于“理性”。笔者认为,深刻理解上述几个方面,对全面理解与把握“诗言志”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诗缘情”与“诗缘政”。从字面上讲,两者中的“缘”字,亦是一字举“要”,表明两者都有别于“诗言志”中的“言”字。按照《古代汉语字典》的“释义”,“缘”的字义,除本义为“边缘”外,还引申为其他字义:一是“沿着、顺着”。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二是“攀援”。如《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三是“分缘,缘分,机会”。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下官奉义务,言谈大有缘。”四是“由于,由于”。如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根据“缘”字之义,解释“诗缘情”与“诗缘政”的内涵是讲写诗的动因问题。人们常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缘”字就回答了为什么要“发言”以及如何“发言”这两个问题。对“诗缘情”来说,解释诗因情而造,循情而发,沿情而上,其题材紧张涉及“个人”,表达诗者的好恶喜怒哀乐“六情”。对“诗缘政”来说,解释诗关政而作,循政而言,因政而兴,其题材直接关乎“大我”,是“个人”的“大我”追求,是“理性”的“感性”显现。
纵不雅观中华诗论,对付“诗言志”、“诗缘情”、“诗缘政”这三个诗学命题,只有前两个命题常被人言及,而“诗缘政”这一命题却长期被人遗忘。便是一些论及“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研究者,却是将它们对立起来。例如,斐斐《诗缘情辨》就认为:“大率而言,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并认为“我国古代诗论的主流不是言志论,而是缘情论”。笔者认为,若是用辩证的不雅观点看待诗学“三命题”,则完备可以将三者统一起来进行新的诠释。首先,言志论代表了儒家的诗学思想,一贯是中华诗学的主轴;但“言志”并不用除“言情”。“‘志’(理性不雅观念)必须表现为‘情’;反过来说,‘情’的抒发也一定具有某种‘志’的含义(虽然每每说不清楚),‘志’与‘情’在诗里原是一个东西”。(《诗缘情辨》)其次,从语境的角度看,随着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繁荣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诗由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养的工具一跃成为展现个体精神风貌,表示自我风采的行为办法,乃至是个体本真生存的展示”。(《孟庆雷《钟嵘〈诗品〉的观点内涵与文化秘闻》)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便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提出的。只管斐斐《诗缘情辨》认为:“缘情论既是脱胎于言志论,又是对它的否定”;但是,鉴于“情”与“志”的关联性以及“言”与“缘”字义上的差异,可以说“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之间不存在“否定”的问题。这是由于若是考虑到“情”亦有“志向”之义,以是“言志”亦不否定“言情”,同样“缘情”亦不否定“缘志”。再次,若是结合“诗缘政”一同来解读“诗言志”与“诗缘情”,三者之间的联系便更加清晰明了。从诗的题材来讲,自必有“个人”与“大我”之分,如果是“个人”题材,便是言“个人”之“情志”;如果是“大我”题材,便是言“大我”之“情志”。结合陆机与孔颖达分别提出“诗缘情”与“诗缘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言“个人”之志,自必“缘情”,言“大我”之志,一定“缘政”。《说苑·贵德》云:“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这里,“思”、“积”、“流”、“发”四字,恰好表示了“诗缘情”与“诗缘政”中“缘”字的深刻内涵。这是由于,无论是“诗缘情”,还是“诗缘政”,个中的一个“缘”字,都解释无论是“个人”题材,还是“大我”题材,“诗”都是“沿着”“思”、“积”、“流”、“发”四字路径,将蕴藏在心中之“志”,终极“发言为诗”。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古往今来,不同时期的墨客及其诗作,只管各有不同的特色,但一定会留下时期的烙印。只要我们存心系统阅读历代著名墨客的诗作,就可以创造“诗言志”、“诗缘情”、“诗缘政”这三个诗学命题是永恒的。本日,与时俱进地解读之,对办理旧体诗的当代性问题,促进传统诗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辅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