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1263年前的秋末初冬时节,伟大的现实主义墨客杜甫,携带一家人行走在秦州(本日水)至同谷(今陇南成县)的路上,在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困难行程中,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手腕,按照所经历的时空顺序写下了《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游记十二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两组大型组诗,还有四首五言古诗《万丈潭》、《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发同谷县》、《木皮岭》,共计二十三首诗歌。个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七言古诗的代表之作,这二十三首诗整体上是对杜甫诗歌风格的传承和发展,是墨客生平主要的作品部分之一,具有新的延续和亮点。
一、杜甫在陇南的诗歌是对现实主义诗史的继续和发展苦难的时期,造就了杜甫,使他成为一个精彩的爱国墨客,一个卓越的政治墨客,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墨客。
杜甫的诗歌一向享有“诗史”的称誉。例如宋代的胡宗愈就曾经说过:“师长西席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如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可以说,杜甫因此历史见证人的身份,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实际的感想熏染,反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生活写照。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墨客,他的诗歌不仅该当看作是他个人生平的传记,而且,也是八世纪中叶唐朝的可靠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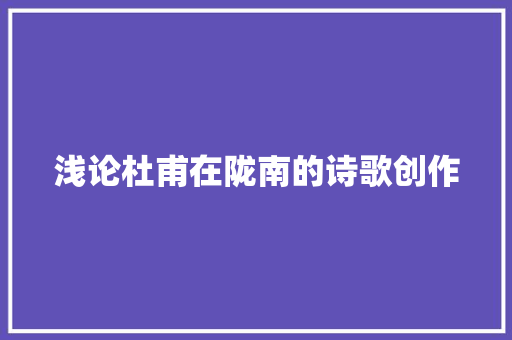
李子德认为杜甫在陇南的两组游记诗《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游记)》、《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也是诗史:“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 。
杜甫在陇南的现实主义诗歌是墨客中期和晚期作品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主要部分,前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虔诚批驳,后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最辉煌的造诣,紧张就在于它虔诚地反响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兴衰史。而在陇南的诗作,这种反响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的方向更为突出。
比如《龙门阵》中“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深切同情远在他乡戍边的人,夜晚在山中哭泣,战役给公民带来了生产和经济上的毁坏,也造成公民精神上的侵害,这种关心民间疾苦、反响生活的思想主题在陇南的诗作中表示的很深刻。“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一句让封建剥削和公民勤恳形成光鲜的比拟,同时又深深地同情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煮盐人。他总是把公民的遭遇和生理活动放在那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写,而且,用艺术形象和诗歌的措辞描写,以是,能够充分地显现出当时社会的阴郁,战乱的时期特色。
《铁堂峡》中“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一句,解释盗贼专横獗,各处横行,此时战役处于相持阶段,安史之乱正在平息当中,此句是对当时战况的一种真实写照。“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也是对战役现实的描写,悲壮惨淡,而且对战局充满的极度担忧之心。
他在陇南的七古忧国伤时,《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六中有“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的诗句,浦起龙说“七歌总是出生之感,何容无慨世之诗?‘龙在山湫’,君当恶运也。‘枝樛’、‘龙蛰’,兵戈森扰也。‘蝮蛇东来’,史孽寇逼也”。说的意思是“龙”指唐肃宗,“蛇”指史思明,借此来隐喻时势,忧国伤时。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中“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描写的便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亲人失落离不得相见,公民有家难回的沉痛一览无余,这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再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四有“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之句,形象光鲜地说出“江淮一带,也是兵荒马乱”的现状,以战役史实为题材,确实是七古所少有的。而此类的记述,有的是正史所没有记载的,因而,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史籍的不敷。
墨客在陇南地区创作的二十三首诗歌,沿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并继续和发展了现实主义诗史特点,为我们理解安史之乱期间大唐帝国由繁盛走向衰败,由强大走向削弱,由统一走向割剧的陇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形供应了真实的历史依据。
资料图片
二、杜甫在陇南的诗歌创作具有游记体风格“古今以杜少陵为诗史,至其长篇短章,横鹜逸出着,多在流落奔忙失落意中得之”。
杜甫在陇南的诗歌以创始的游记诗为主,是墨客呕心沥血,一步一步艰巨地走出来的。杜甫在陇南的游记体诗歌特点表现在两点。
(一)每到一地,墨客大多作诗一首来游记
杜甫发秦州后,首先向南到达本日水的暖和湾、皂郊镇一带,然后折而向西至平南镇、天水镇、礼县盐官镇,西和县的长道镇,再折而南行,经西和县境南青羊镇、八峰崖至成县西北府城村落,东向一贯到达今日的成县城区,末了寓居于城南飞龙峡凤凰台下,也便是本日的成县杜甫草堂。
杜甫从秦州至陇南比较准确的行为路线图,据考证,杜甫在陇南的诗歌和写作地点做一对照及旅行路线展示如下:天水市(《发秦州》)出发至→→暖和湾(《赤谷》)→→天水县张家峡谷(《铁堂峡》)→→甘肃礼县盐官(《盐井》)→→西和长道之祁家峡(《寒峡》)→→西和石堡五台山(《法镜寺》)→→西和石峡(《青阳峡》)→→成县纸坊大营→→府城(《龙门镇》)→→代山→→杨湾→→开元寺、大石坝→→柴坝→→不雅观音崖圣泉寺(也有一说写的是今西和县石峡乡西北八峰崖)(《石龛》)→→殿山梁(《积草岭》)→→牛星山(《泥功山》)→→顺隍河而下→→成县杜公祠(《凤凰村落》、《万丈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县》,期间寓居一月)→→吕坝梁(珍子寺)→→徽县栗川何家沟门→→山寨坡→→龙洞沟→→山神庙→→狮子崖→→关场→→老虎湾→→瓦房村落→→木莲花掌(《木皮岭》)→→黑林垭→→歇马署→→庙山→→经白水江入蜀。
杜甫在陇南生活的一个多月中,在上述路线中,险些每到一地都会写一首诗来游记的,并以行经前后为序将他所到之处的山川风貌、风土人情、自身遭遇、社会现实等逐一记入诗中,这些是墨客诗歌的创新和完全的运用,个中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最为著名。从以上的对照中可以看出,墨客在陇南的浩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诗作,基本上是每到一地作诗一首,可见这些诗作纯属游记体诗歌。再者从《发秦州》组诗标题的注明“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游记”、《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县》的标题注明“乾元二年十仲春一日自陇右赴剑南游记”中可以看出杜甫每走陇南的一个地方,在当地只要轻微有点影响和名气,墨客就写一首古诗来游记,两组大型的诗作除了总标题中有两个“发”字之外,其它的诗歌都因此地方古地名而命名。这足以解释杜甫在陇南的诗歌是游记体诗歌。而墨客留下的足迹,凭借着伟大墨客杜甫的光辉诗篇,陇南,这块祖国西部神奇的地皮,便以其雄奇而又奇丽的风采为众人所瞩目。
(二)通过游记诗来反响困苦的生活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7月,因关中大饥,杜甫丢弃了华州的官职,继而西向适秦,于7月尾8月初到达陇右秦州。“我衰更
1. 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漂流阶段
漂流阶段韶光为墨客自发秦州后至到达同谷县之间。期间,墨客的生活极为不幸,时逢深秋,风雨交加,常常饥寒交迫,一边在赶路奔波一边还要衣食住行而发愁。《铁堂峡》中曰:“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山风劲吹,云雾缥缈,石头像铁一样又黑又硬,山峡的形势很艰险,山路伸入云天,峰顶尽是积雪,墨客那一匹瘦马的骨头都要冻折了,在天寒地冻、雪窖冰天的恶劣环境中困难地前行。
墨客走到西和长道祁家峡,别是一番景象。山谷的地形变革多端,峡口的两岸是峭壁绝壁,阴雾沉沉,寒气逼人,墨客作《寒硖》一首感叹道:“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绝岸,积阴霾天寒。寒峡不可度,我实衣裳单。况当仲冬交,溯沿增波澜。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衣服软弱,寒气入骨,烟雾环抱,只有凭炊烟来探求人家,地逢绝壁,只有在水岸边野餐。
在西和县石堡法镜寺借宿时,夜晚风雨交加,处境凄苦凄凉,清晨雨过天晴,墨客拄动手杖出去探求食品,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看着寂寥的村落落,发出了这样的伤感之情“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蝉娟碧藓净,萧戚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柱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复取”。
很快墨客又到了青阳峡,青阳峡“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蹊西五里石,愤怒向我落”,道路非常艰险难行,墨客看车子的轮轴,担心轴弱而不能负重,发出了这样的低吟“昨忆逾陇板,高秋视吴岳。东笑莲花卑,北知崆峒薄”⒃。
他们艰巨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一起颠簸到了西和县石龛,却是“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狼柴虎豹挡住墨客的去路,一起上恶鬼长鸣,哀猿呜咽,实为凄凉。
2. 遭遇不幸、水深火热的同谷县寓居阶段
寓居阶段韶光为到达同谷至发同谷期间。墨客翻越积草岭,进入同谷县,攀登泥功山时,山多云雨,路途泥泞难行,那匹白色的病马变成了铁泥色,小孩子寸步难行,气喘吁吁,彷佛变成了老头目,步履太困难了,墨客告诫后来者说:“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
谁知墨客到了同谷县城,“佳主人”并没有实际去帮助他,墨客在县城做过短暂勾留,就去城东山谷名为龙峡的地方,依赖一个“山中儒生”,但这个“旧相识”也无能为力去接济他。此时生活更苦,百口险些濒临绝境。这时正是大雪封山的隆冬,由于缺食,为了觅取食品充饥,杜甫只得穿着短衣,扛着锄头,不得不冒着寒冷到深山去挖“黄独”(土芋),由于缺穿,长了冻疮,手脚迸裂,皮肉都失落去了知觉,有诗为证“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去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第二首写道:“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挖不到黄独,只好扛着长(即锄头、一种铁制的尖头挖掘工具)空空而归,唯束手待毙而已,真是悲惨之至,连邻居也为墨客的一家悲愁,“邻里为我色惆怅”。
陇南的地区地处偏远,山大沟深,道路波折,交通极为不便,而墨客还有一辆破马车伴行,“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蹊西五里石,愤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再加上是秋冬时令,天寒地冻,在如此艰险的道路上前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一起走来,墨客走的太辛劳了,除了这些衣食住行上的困苦之外,我们在其诗作里面还可以看到墨客还有其他的苦衷。
1.思念亲人的相思之苦
杜甫有四个弟弟:杜颖、杜不雅观、杜占、杜丰,只有杜占随他来到同谷,其他三个都远在河南山东,还有一个嫁韦氏的妹妹远在淮南钟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以连呼“有弟有弟”入笔,表达了对“远方”三个弟弟的无限思念。《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四“有妹有妹在钟离,外子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以呼唤“有妹有妹”开头,说她现在远在钟离,丈夫早早去世,儿女幼小无助,表达了墨客对遭际不幸的妹妹所寄予的深切思念。
2.忧国忧民的悲愤之苦
墨客在陇南的光阴,常怀忧国忧民之心,虽居无定所,也不忘水深火热的公民。墨客在途经盐官时,唱出了悲壮激越的《盐井》:“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骨骨,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斤。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磋,物理固自然”, 表达了对盐贩子轻义重得的讨厌,以及对煮盐工人辛劳劳动的怜悯。“再光复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在墨客在面对自己悲苦哀愁的生活境遇时,仍旧想到的是“兴业”和“群盗”之事,表达了墨客希望一洗雪耻、补救苍生、早日平叛安定的强烈欲望。“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竿尽,无以应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尺蒸黎”,听了这一番话,墨客沉默良久,发出了无奈的感叹:都怪玄宗天子不辨忠奸,过分宠信那胡儿,造成渔阳兵叛,直驱中原,坑害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家破人亡!
这首诗,由情及景,由景及人,集中反响了墨客杜甫纵然自己在困难困苦之中,亦念念不忘家园、关心民瘼的名贵精神。于是发出了“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的嗟叹和愤慨之词,也是怀才不遇的牢骚和不满之情。但墨客还是充满希望地说“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殷切地期盼早日平息叛乱,让公民重见天日,减轻战乱带给公民的痛楚。
在这样的生活中,墨客多么渴望有一个安定的住所,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四中有“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神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地府。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的佳句,此诗是赞颂陇南西和仇池山的名篇,也解释仇池山是墨客非常神往的地方,“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一句明显地表明墨客有隐居仇池山的意愿。可墨客没有在此长居,去过休闲安逸的生活,而是连续选择颠沛流离的漂流,在山路艰险、饥寒交迫的境遇中,连续向前走。
通过上述对诗作的简短剖析,创造墨客在陇南的诗作主题是纪实和游记,诗作内容是旅途的困苦生活和社会现实的情景再现,这完备符合游记体诗歌特点,诗作所具备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解释墨客在陇南的诗作具有游记体风格。
三、具有光鲜的个人风格资料图片
杜甫在陇南的诗作不仅具有游记体诗歌的特点,而且墨客在陇南的游记体诗歌又有光鲜的个人风格。
1.游记与叙事的有效结合。
拥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直接了当地讲远行的缘故原由便是为了衣食。他写了艰巨跋涉的焦虑,详细描写了“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寒硖不可度,我实衣裳单”、“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这些生活情形,表示了“此身免荷役,未敢辞路难”的顽强决心,并详细记叙了沿途的经历。这样,涌如今诗中的墨客自我形象,充满了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2.游记与政论的有机结合。
在困难的旅途,处饥寒之困境,他能推自己人,对防守深山的士兵表示关怀,为上高山砍箭竹的农人哀叹。《盐井》一诗,斥责奸商剥削公民;对付“歌笑轻波澜”的舟子,表示了由衷的的敬意。看到剑门天险,忧虑苏中将被强潘盘据;他乐意献出自己的心血,去喂养象征“复兴”的凤凰。这些诗不但是情景交融,而且是情景与时势政治的交融。
3.游记与写景的完美结合。
仇兆鳌指出杜甫在陇蜀道上的诗歌刻画山水穷极其妙:“蜀道山水奇绝,作平凡登临览胜语,亦犹人耳。少陵搜奇倔奥,峭刻生新,各首自辟境界”。杜甫在陇南的诗篇有正面的刻画,有侧面的陪衬,有夸年夜的形容,有浪漫的想象,紧张是如实摹写,把陇南山川描述的历历如画。即写陇南山区的险峻峭壁,也写了仇池山那样的世外桃源,有“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的清晨美景,有“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的晚秋星辰,有“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的云雾环抱。诗的意境和风格是丰富多彩的,诗的措辞也随着墨客的心情与山川的形势而变革,《发秦州》还没有进入险要的路途,措辞是平稳的;《盐井》反响民生问题,普通如话;《凤凰台》有浪漫的想象与神话,富于文采;《发同谷》写得很朴素,感慨万千。此外,与高危险要的山川形势相适应,措辞高低有序,气势急匆匆,多用仄韵,并以此为主调,突出了沉郁抑扬的风格。
杜甫在陇南之行不是一次有时的重逢,墨客饱含着激情和爱憎,在陇南短短一个多月之中,创作出二十三首不仅反响了一定客不雅观现实内容的诗作,而且蕴含着墨客对现实的思虑和理解、凝聚着炽热的感情,给陇南盖上了厚重的文化秘闻和人文特色,与陇南这块地皮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墨客在陇南的光阴极为困苦极为不幸,但在困难的旅行当中,墨客不畏艰险、一如既往的坚持着忧国忧民的信念,步步为诗,步步为史,步步游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了墨客现实主义诗史,并造诣了杜甫游记诗成功性的创始,这些正是杜甫陇南诗作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