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信贫家。”这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瓶史》中的名句,看似平凡四句话,如今读来却以为分外有趣。只因他在平凡的句子里,道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韵致,而这种韵致,在周瘦鹃师长西席的《种花志》一书中,也鲜活灵动地呈现出来。
周瘦鹃,是民国文坛上“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笔墨风格以清新、幽美见长。作为周瘦鹃的代表作品,《种花志》一书收录的近60篇植物美学方面的散文随笔,更是雅韵横流,既具有当代散文之明快、简洁的特点,又具备古典文学的蕴藉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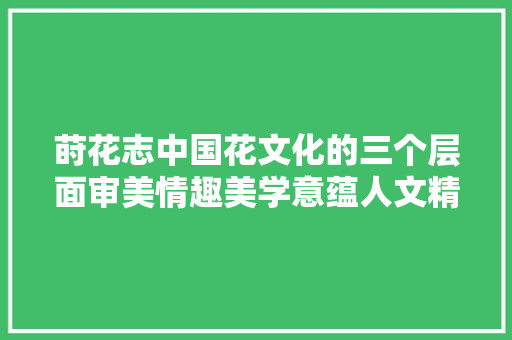
在《种花志》这本书中,花卉作为紧张的审美工具,不仅象征着自然之美,更主要的是,花卉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与人文精神绾结在一起,凸显出中国传统美学之特色。一本《种花志》反响出的是中国花文化的三个层面:审美情趣、美学意蕴,以及人文精神。
(一)中国花文化中的审美情趣
花卉是大自然的产物,是美的象征。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碰着的审美工具,便是花卉。而除了不雅观赏之外,有些花卉还可以食用,比如黄花菜;有些花卉可以入药,比如金银花;还有花卉可以制作喷鼻香料,比如玫瑰。
可见,花卉兼具不雅观赏代价与实用代价。但实在,不雅观赏性则是花木代价取向中的主要内容。
人类对自然花木的欣赏,可以追溯到由原始佃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中国花文化中的审美情趣,也正式由此而发轫。由于,正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来开始制造了大量以花草为装饰图案的器物。个中比较范例的有河姆渡文化中的刻花陶盆、仰韶文化中的彩陶花瓣纹盆,以及大汶口文化中的彩陶花瓣纹盆,这些器物均出悛改石器时期。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这种超越功利性的审美情趣也得到了进一步开拓,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花卉为主体的文化体系,这便是中国花文化,而人类对花卉的这种审美情趣,则是中国花文化得以形成的底层逻辑根本。
在对花卉的审美情趣的支配下,人们以自己独占的办法认识自然,并且通过审美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而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人们也丰富了自身的生活、塑造了自身的品性。
周瘦鹃在《种花志》等分享的一个故事,就颇具代表性。
想当年,苏州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周瘦鹃则迫于场合排场,租住在上海的一角小楼中,居住条件非常局促。偏偏在早春时节又逢大雨,这场大雨冲走了早春的一丝暖意,寒冷的景象迫使周瘦鹃瑟缩在狭小的房间内,以是他的心境非常恶劣。
就在周瘦鹃被烦闷和愁绪堵住心口的时候,他转眼一看,不经意间竟然创造室内桌上的一只花瓶内,绽开了几朵浅白淡粉的桃花。由此,周瘦鹃遐想到,即便人陷入困境之中,也要像那花草一样,以保持不懈的生命力绽放出自我的光彩。
这便是审美意趣,对人们自身品性的塑造。
(二)中国花文化表示出的美学意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精良作品,而古典文学的笔墨之美与花木之美是如此的相得益彰。以是,中国花文化表示出一种以蕴藉、内敛而紧张特色的美学意蕴。
花卉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工具,这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中认为,美与善要统一,美与真要领悟。花卉象征着美好,它被人为地授予了各类精良的品质,同时,花卉成长于自然之中,以本真的姿态示人。因而,花卉可以不经任何润色,就呈现出一番自然美感。
美学大师钱穆在《当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写道:“中国文化紧张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提要挈领中国花文化的这种美学意蕴,是通过心灵直觉体验外物。
若要欣赏中国花文化表示出的美学意蕴,那么一定要经历如下四个审美生理活动阶段。
第一阶段:内心虚静。周瘦鹃有一篇名为《我爱菊花》的散文,文中说,像古时候那些王侯将相,在自家庭院里设宴赏菊,未必能够欣赏到菊花的妙处,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这是为什么呢?由于,他们内心充满了希望和计较,既然不能沉着下来,又如何能创造花草的真正美感?可见,只有在内心沉着时,才能领略到花木的妙处。
第二阶段:生发感兴。当我们内心沉着时,就会创造花木之美,而一旦我们被这种美感所触动,就会涌现各种各样的内心感想熏染。比如说,周瘦鹃写杏花开放时,正派江南地区春雨绵绵,人们由于这阴雨景象而烦闷。可是,当人们溘然创造,院子里绽放出几朵杏花,这时心中就会顿觉隽妙可喜,不再讨厌这阴雨景象。这便是被花木的美感所触动,而产生出别样的心里感想熏染。
第三阶段:产生妙悟。以之前的审美生理活动为根本,我们在欣赏花木时,全身心投入个中,此时就能深入发掘花木之美感。进入到妙悟状态后,我们会产生一种审美直觉。比如,我们看到满园菊花盛开,不必进行剖析,凭借直觉就会感知到深秋已到。这便是一种妙悟。
第四阶段:物我相融。中国传统的审美生理活动中,格外强调物我之相融。周瘦鹃在书中的多篇文章里,就描写了他赏花时这种物我相融的心境。比如,他不雅观赏白色栀子花时,竟以为自己也跃上花枝,“一白如雪”,成为栀子花中的一朵。再比如,他不雅观赏芙蓉花,由于芙蓉生性喜水,以是,当他看到水中倒映着一丛芙蓉,便以为水影与花相映成趣,而自己也彷佛化入水中,成了水中芙蓉。
(三)与中国花文化绾结在一起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花文化中有一个征象非常有趣。从古至今,人们在潜意识中并不把花木视为自然事物看待,而是授予了花木以人格。
周瘦鹃指出:这种与中国花文化绾结在一起的人文精神,其紧张特点便是将人格寄托于花木之中,而花木的品质则寄托于人之品性。
通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也能理解到,自古以来,人品与花格便相互渗透。比如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君子的象征,而寒冬尾月盛开的梅花则是傲骨的表示。
人生之荣辱兴衰,人情之爱恨悲喜,都寄寓于花木。
如果说,中国花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花木的人格化,那么,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便在于对高尚品质的崇拜与讴歌。
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具有这样三个特点:
首先,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深受易学和老庄思想影响。古人认为,天地间只有三种生物,即人、禽兽、花木。这些都是天地的产物,从生命形式而言,都具有统一的实质。而这种生命类比的理念,实则渊源于中国易学,以及老庄思想。
易学认为,宇宙中存在同质同构的有机整体;而老庄思想则认为,万物与我为一,不论是花木还是鸟兽,虽然与人类存在等级上的差异,但究竟与人类同为天生地养,因此,万物与人类属于伯仲关系。
其次,授予花木以人格内涵,这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提出“仁爱”的理念,而孟子则进一步推己及天,认为君子该当“仁民而爱物”。世间万物,无一不笼罩在仁爱之关照中。以是,古人对待花木便犹如待人,他们尊花为朋侪、为师长,有些爱花之人,还把花木视为妻儿家人。这足可见出,待花木如待人,这是中国花文化中的一大特点。
周瘦鹃在书中就记载了为花卉过生日的故事:三五心腹朋侪,带着清淡的食品相聚一堂,一边不雅观赏庭院里的花木,一边作诗写文,为院中花木庆生。
再次,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其至高境界是人花交感。这种人花交感,实在正是民气与外物的一种相融境界。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认为,人在审美生理的高峰体验阶段,会进入到“物我两忘”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状态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领悟为一。周瘦鹃在《我为什么爱梅花》一文中记叙了他赏梅的感想熏染,他被梅花那种不畏寒冷的品性所打动,乃至,他自己都不以为冬日里的苦寒有多么难以忍受。这便是人花交感的审美境界。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花是自然界最俏丽的产物。”花木以其多姿鲜艳的形态以及浓淡不同的馨喷鼻香,点缀了自然,也点缀了人们的生活。《种花志》一书的作者周瘦鹃,则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秘闻,以及细腻清新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一则则与花木干系的故事。
作为读者,我们读到的不但是与花木有关的古典诗词,亦非与花木干系的奇闻异事。我们真正该当把握到的,是中国花文化中的审美情趣、美学意蕴,以及人文精神。毕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内涵,才使得中国花文化得以发达发展,并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