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人生,是说人生中总是充满诗意,这种人生,总是与艺术相伴,他不同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他是把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能咀嚼出诗的味道来。
毛泽东作于1947年4月的这首《五律.张冠道中》便是他诗意人生的范例代表和表示。
《五律.张冠道中》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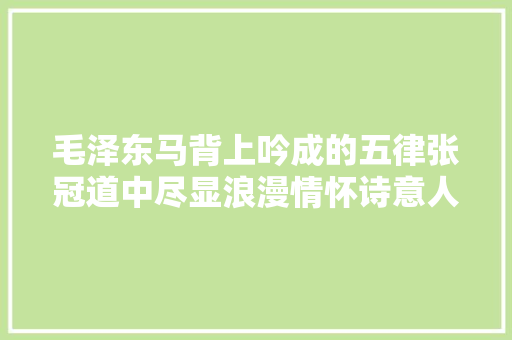
戍衣犹铁甲,男子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14万大军,大举向延安发动进攻,梦想将这一赤色根据地摧毁。面对气势汹汹敌军,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用他出色的军事指挥艺术,于18日晚率中共中心计心情关主动撤离延安,在陕北的延川、清涧、子长、靖边等县转战,同敌军奥妙周旋。
这首诗,便是写于此期间,是范例的马背上吟成的一首诗。转战陕北,这虽然是一种军事行为,但毛泽东诗心未泯,在行军途中仍捕捉诗意,把计策构想当作是艺术构思,在张冠道中吟成了这首诗。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这两句诗,点明了行军韶光是在早上,而且还有浓雾。清晨的浓雾弥漫在全体天空和大地上,战马在北风中发出阵阵的嘶鸣之声。此句描述出行军的景象环境,战马的嘶鸣衬托出行军的肃穆感。用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的范例事物,勾勒出一幅雾中行军图。
接下来的“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句,继前句的视觉和听觉描写后,又从触觉入手,描写行军状态。“露湿”,便是触觉描写,露水落在人的皮肤上,会令人产生一种湿漉漉的觉得。由于雾化为露,途中的尘土不再扬起,很难再落到人的脸上和衣服上。
征尘,在古诗中既是具象又是意象,作为意象时,多与行军和战事有关。例如杜甫在《兵车行》一诗中便有“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生动描写。人与马行走时趟起的尘埃很大,遮住了人们的视线,连咸阳桥都看不见了。《兵车行》中的尘埃,便是具象描写。
征尘,是行军途中最为范例的事物,毛泽东选取这一范例事物入诗,表示了他不雅观察的细致,更表示出他写实手腕的高妙。而“霜笼鸦不惊”句,表示的是行军的肃穆,连巢中的乌鸦都未被惊起。之以是会涌现这种行军状态,由于转战陕北,是一种无奈之举,是避开强敌锋芒的须要。广大指战员中有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的计策意图,对付主动放弃延安,不理解。因此,在行军中感情是压抑的,与常日的人欢马跃是不同的。
“戍衣犹铁甲,男子等银冰”,此句,毛泽东表达的是对艰巨行军生活的最形象的体验和描述。行军是艰巨的,更是疲倦的。行军途中,每个人都是要有负重的,包括枪支、弹药及生活必需品。特殊是在古代,将士们要身披厚重的铁甲,行军的艰巨是可想而知的。当代军队,虽无铁甲在身,但毛泽东体量将士们的艰辛,因是三月未四月初,战士们穿着厚重的棉服,长途行军,显得很笨重,就好象铁甲在身,觉得很笨重。这十分符合当时战士们的生理:越轻松越好。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男子等银冰”,是说由于天寒,战士们的眉毛与髯毛上都结满了白白的银霜,象是结了冰一样。这是毛泽东以乐不雅观的态度来看待艰巨的行军生话,正是诗意人生的形象表达。“等”,这里,即是等同的意思。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此句,是对行军途中的概括与总结,意为部队在张冠道上缓慢行进,仿佛走进了一首名为《塞上行》的古诗意境之中。《塞上行》是唐代墨客鲍溶写的一首边塞诗。诗是这样写的:
西风合时筋角坚,承露牧马水草冷。
可怜黄河九曲尽,毡馆牢落胡无影。
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塞军人的艰巨生活,凌厉的寒风中弓箭显得非常坚硬,迎着寒露放牧战马,水和草都显得很寒冷。可叹的是,在九曲黄河的尽头,只见毡房零落,却见不到胡人的影子。
唐代边塞墨客岑参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题目是《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中对行军的艰巨有许多精彩而形象的描写。例如“轮台玄月风呼啸,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形容风之大。再如“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这是形容景象的寒冷。为了强化这种寒冷的程度,诗中,岑参还有“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这一更精彩的描写。不是吗?战马身上的冰,由于奔驰发热而热气騰腾。军帐中写檄文,由于天冷,把墨水都冻得凝固了。可见边塞是多么的寒冷啊!
行军的途中,沿途的景致,令毛泽东不禁想起许多边塞诗中的佳句,自觉不自觉地便进入诗中的意境,因此,才会有“恍若塞上行”的艺术觉得。
战役是残酷的,行军是艰巨的。但是,这不能阻挡毛泽东诗兴的迸发,由于他实质上是个墨客。他以一颗诗心来看待生活中的统统,映入他眼帘中的都是诗的意象,包括行军打仗。这便是毛泽东的诗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