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嵲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农历正月十二,春雨淅沥,柳色初新。地处武当山下的房州古城,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中,一个恐怖的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金兵就要到了。
几个月前,这群身穿奇装异服、骑着高头大马的女真人攻陷卞京,劫走徽宗、钦宗父子,掳走数千后宫佳丽和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北宋灭亡,这正是岳飞喟然长叹的“靖康耻”。
但此时兵锋日盛的“岳家军”,也未能阻住金万户楚尼赫部西进之马蹄。建炎二年正月初三,金兵陷邓州;正月十一,再陷均州;正月十二日傍晚,房州城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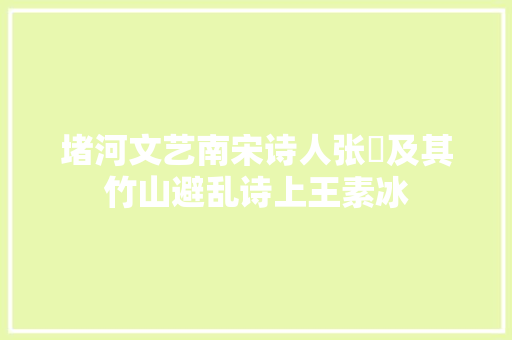
南宋·赵黻·江山万里图(局部)
三十二岁的房州法律参军张嵲的官舍里,正坐着一屋子青年才俊,为首的是从均州逃难来的大墨客陈与义,还有竹山知县夏致宏及落难的青年墨客孙信道,正是诗意阑珊的光阴,金人攻城的炮火响了。
兵荒马乱中,人流如野蜂般奔城南大山逃去。陈与义在其长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中,记述了这次逃难“铁马背后驰”、“脱命真毫厘”的惊险与艰辛,及回谷张姓老人“呼酒软客脚,菜本濯玉肌”的淳厚与友善。
从此,张嵲及其诗友们“且逃且吟”的生涯开始了,文史学家把这种“凶险的诗意进程”雅称为“南渡”。其后,陈与义一起南奔,经湖南、广东、福建,终于绍兴元年(1131年)秋抵达临安,成为天子近臣。张嵲则携母西逃,于是年秋抵至竹山,亡命之余,在庸城西山开荒种地,开始四年山中避乱的生活。
熊焜:南门早市
一
初识“张嵲”,是在《竹山县志》中。历届古志“艺文卷”,均录有《岁寒堂记》和《微王山铭》,作者署为“张嵲”,文末释云“宋代文学家”。二篇文辞古雅,绝非平凡文士能为。然作于何年?微王山在何地?皆不甚其详。
再次关于注到张嵲,则是由于南宋大墨客陈与义,有些爱屋及乌的意味。
某个期间,我迷恋于宋诗的风骚蕴籍。南宋诸家,独钟有“诗俊”之称的陈与义。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河南洛阳人。南宋初年精彩墨客,其诗语意超绝,疏朗明快,人称“简斋体”,被 “江西诗派”尊为“三宗”之一。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在北宋、南宋之交,大概要算他是最精彩的墨客。” “陈与义在世时,就有人学习他的诗歌,比如表侄张嵲、朱熹父亲朱松。”
难怪陈与义写了那么多“均房诗”,原来是因表侄张嵲之缘故。
熊焜:堵河漂流
二
张嵲(nie)(1096—1148年),字巨山,襄阳光化阴城(今湖北老河口西北)人。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上舍中第,后官至秘书省正字、中书舍人、著作郎等,南宋文坛主要墨客,平生业绩见于《宋史•文苑传》,《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录有其《紫微集》。
张嵲的人生,与大多数传统文士并无二致。其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入襄阳郡学,且从表叔陈与义学诗,长入太学,二十五岁被天子选录为进士,后调任唐州方城尉,二十八岁调任房州司刑曹。也就在这年秋,他的诗友“房陵丞”夏致宏调任竹山知县,开始与竹山建立起联系。
宣和七年(1125年)秋,张嵲应夏致宏之邀,沿房竹古道,自东而西首入竹山。站在莲花峰上俯瞰山城,陡见山势开阔,满目苍翠。萧瑟秋风中鸡犬相闻,恍若置身桃源,不禁在心中默问割草老人:野老啊,你可意识到,你的生平都生活在这满山苍翠之中。他在《竹山道中》写道:“青山忽断开平陆,鸡犬人烟邃古风。野老诛茅宁故意?生平身在翠微中。”淳厚宁静的竹山,给墨客留下难忘印象。
闻友夏致宏管理竹山政成,建“岁寒堂”,欣然命笔作记。《岁寒堂记》云:“未期年而政成,讼庭廓无事矣。……堂下有双桧,其大连抱,其高参天,因榜曰‘岁寒堂’。”桧,古柏木,取《论语》“岁寒而知松柏后凋”之意,故其文有句:“嘉树之与恶木并生于天地间,初若无别也,至于凌厉以秋霜,回薄于严风,而能不凋落,然后松柏之节见矣;君子与小人并居于世,初亦若无别也,至临短长,遇事变,然后君子之守见矣。”
夜宿紧邻县衙东侧的大梵寺。
大梵寺,竹山最古老的寺庙,有古碑文记其兴建于隋唐。听说有人曾觅得大梵寺古砖,刻有 “尉迟敬德”字样。故意思的是,寺中山僧多“佛印式”的老衲人,《竹山县志》即录有大梵寺山僧所作“偈子”诗。县衙里的官人与庙堂里的僧人关系协洽,不仅有诗书往来,且常在寺中阁楼觞咏雅集、酬谢来宾。其后七十年的宋宁宗庆元年间,县令郑延年又在寺东建“喜丰亭”,后更名 “登爽亭”。名传古今,代有诗文。至元代至正五年,塔失落公为县宰,复将登爽亭修葺一新。元人周仁在《登爽亭记》中云:“亭成,俾寺住山僧守愚住之。”且常“领僚属、父老觞咏于中”,“凭栏槛以徘徊,纳江山于指顾。”此乃后世佳话。
张嵲此行,留有五言古风《次韵王倅大梵寺山亭夜雨》记其环境:“溪山含变态,可玩不可说。西岭澹斜晖,前山明积雪。潭空游鳞出,景晏飞鸟绝。远屿上孤烟,平沙散疏樾。天涯一尊酒,草草堂上设。觞咏寄高爽,对此清夜月。但使息营营,宁论醉兀兀。寓兴合一篇,亡书谢三箧。”
斜晖西落,潭鱼空游。一阵夜雨后,云开雨霁,一轮明净清凉的玉轮东升于莲峰之上,大梵寺阁楼里正 “觞咏寄高爽”,但北方金、辽纷乱已初现端倪,令民气忧。
王倅,剑南人氏,能诗,与张孝祥、蔡珪、郑刚中等南宋诗家均有酬和,不知因何游于竹山。
三
张嵲选择来此避乱,很大缘故原由是好友夏致宏在竹山主政。
关于墨客避乱竹山的韶光,有研究者认为是建炎三年(1129年)秋,依据是《入峡诗序》,笔者认为是在建炎二年(1128年)夏秋之际,在与陈与义、孙信道从房州分别后,即与夏致宏来到竹山。其作于次年的《修房州大成殿记》中,有笔墨“公乃命故吏张某记之”,可见建炎三年时,墨客已是房州“故吏”。
时局混乱,老母多病,张嵲决意“致仕养母”。
再至竹山,墨客见到的景象已迥异于前时,金人掳掠过的山城,一片散乱,惨不忍目。他在《再到竹山》中写道:“衰草连云鸦乱飞,荒城寂历澹寒曦。屋庐烧尽民居少,只有青山似当年。”
初来还在大梵寺寄居。集中另有两首诗,分别为《余所寓僧舍,蜂筒忽散去,仅留其半。僧云分蜂时每如此,寻复追求再得之,贮以别龛,感而成诗》、《登寺阁见月上率然成咏》,第一首中有“余所寓僧舍”笔墨,第二首有 “绝世非吾意,幽栖寄暂闲”句,应是这个期间所作。
市价金人大举南下,中原大地一派刀光剑影。翌年,金军一起破扬州、建康、临安,新君高宗亡命于海上。地处南北交界的金(陕西安康)、均(湖北丹江口)、房(湖北房县)三州,正是抗金一线,双方数易其手。《宋史·王彦传》记惨象:“无问郡县与村落,纵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城市村落庄,搜索殆尽。”
最有效的逃命办法便是躲进大山里。宋叶梦德《避暑录话》云:“盗贼戎狄,所及无瞧类。有先期奔避伏匿林莽间者,或幸以免。”堵河上游的莽莽大山,自然成为最空想的避乱所。故而大多数韶光里,张嵲带着母亲奔逃于竹山南部的高山深谷间。其五言长诗《避贼》写道:
避贼入深谷,乘桴复悠悠。
四顾江上山,群峰如荠稠。
是时雪霜霁,林壑氛雾收。
茂树荫石壁,澄潭深不流。
蓧荡拥荒岗,冲飚忽飕飗。
山深水更佳,溪喧鸟啼幽。
诗的前半部分写得优雅从容,逍遥清闲,似非逃难,而是纵情山水,但很快,墨客便愧意心生:
平昔慕寻胜,所见良未俦。
全球逢祸枢,我独成兹游。
暂赏兴复阑,自誷宽百忧。
舍棹陟绝巘,林光与云浮。
却不雅观来时江,碧线萦长洲。
一室苟自安,两饭无余求。
彼苍未厌乱,平生易近何时休。
传闻仇敌营,近在濒汉州。
尚恐复飘转,讵敢辞淹留。
进而又起“退种田亩”动机,以为“桃花源中可种田”:
已与农父言,傭耕事田畴。
耘耔纾井田,蚕绩充衣裘。
尚享黄发期,庶几谐首丘。
此诗前段写峡中之景,中段写时局之忧,后段写退耕之思,可谓百感交集,在其避乱诗中颇具代表性,总为论者言及。
在寓居竹山的四五年里,张嵲来回庸南山中不下数十次,由此留下了一大批描写峡江山色之佳作,竹山、堵河、白河口、宋坪、峪(余)口、深(生)河口等当地盘名,逐一入其笔下。
熊焜:驴头峡放排
驴头山下的官渡镇蒲溪村落,是堵河岸边主要的驿站。依山分布着两排瓦屋,人称“前街”、“后街”。古往今来,关于堵河的大事要案总与此关联。张嵲在诗文中亦数次写到“蒲溪”这个地名。既有“蒲草绿如发”的清逸,更有“经由涕垂领”的忧伤。在《再经蒲溪往年避地处》诗中,他写道:“淹流既失落策,贼至甘远屏。往岁忆曾游,迳路犹可省。今来冬向除,昔至夏方永。山寒竹树疏,岁阴云雾冷。破屋今已无,荒筠蔓枯颖。前人安在哉?经由涕垂领。”
另有二首《登石门山,山侧有不雅观基,在荒筠中不可到。山相对即新安县也,今谓之新安平》,有“石门山下微江水,依旧东流昼夜声”等句。新安县,南北朝时上庸郡下辖六县之一,今不知其址。张氏诗中所写,疑为“老田家八景”中“石门对石鼓”的石门山,只是不知“新安平”这个地名,至今还有流传否?
(王素冰,现供职于竹山县文联)
——转自竹山县文艺刊物
《堵河》2021年第3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