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去世。
——[唐]李绅《悯农》(其一)
《悯农》(其一),是中唐墨客李绅(772—846)两首同题诗中的第一首,其二为家喻户晓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劳?”此作关照现实、直面抵牾,虚实相衬、比拟强烈,简朴厚重、不拘平仄,是戳穿封建社会不平、同情农人疾苦的代表性诗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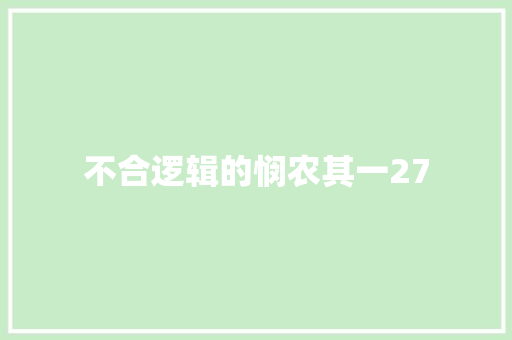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史,同时也是一部剥削史。生活在个中的墨客有着比一样平常群众更亮的眼睛和文人特有的文化担当,几近大家都有诗作在叙事、在讽刺也是在记录那血泪斑斑的人间剥削——早期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唐代有“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韦应物《杂体五首》)、“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劳为谁甜。”(罗隐《蜂》)、“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敷归卖屋。”(元稹《田家词》);北宋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田家语》)……比较之下,《悯农》(其一)更加普通与深刻。
《悯农》(其一)中,只有这几个字词略有阐明的必要:“粟”,即谷子,诗中指代所有的粮食作物;“子”,是指植物的籽实;“四海”,有“普天之下、全中国”的意思;“闲田”,意为“荒废闲置不种的地皮”。诗可直译为:农人在春播时令种下一些种子,秋日时节便能收成到很多粮食;普天之下险些没有荒废不种的地皮,但劳苦的农人却仍旧被饿去世。但作为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一、日常却不平常。诗作以“春种”和“秋收”,揽括了时令之下日常农事的一样平常规律,也将农人一年四季的劳作进行了奥妙而精准地刻画,但从“一粒粟”化为“万颗子”的丰收景象的大超过中,又展现了非凡的艺术力量;二、是理却不在理。只管诗中彷佛没有在说理,但含有道理,即“四海无闲田”,解释了农人的勤恳,解释了丰收的在望,这是个明理,随之该当是农人谷高仓满、丰衣足食才是,但诗歌却破了理——此“农夫”比“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的彼“农夫”更加悲惨,却“犹饿去世”,飞长了诗的美学高度。三、点破却不说破。由“四海无闲田”到“农夫犹饿去世”,道出了这种触目惊心的残酷,但到底是谁剥夺了农人的劳动成果,陷其于去世亡之地呢?墨客没有回答,可见答案在现场、答案在民气。
如果用人性的或关于人性的钥匙来开启《悯农》(其一),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光芒呢?
只要“春种一粒粟”,自然会“秋收万颗子”,这是客不雅观规律。然而,“四海无闲田”时,“农夫犹饿去世”了,明显违背了基本的思维规律。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论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实在也是在用“规律”来讲解“剥削”的存在与现实。
因此,《悯农》(其一)通报的人性之光,即:人们普遍认为,客不雅观规律和思维规律便是广义上的逻辑。人类从生存到生活、从科学到哲学、从道德到法律,还有文化、宗教等等,无不是合乎逻辑的范围中蹒跚而来并终将远行,而不合逻辑的事物也是一种常态,不可弃、不可避,它便是那坎、它便是那坷,如何踏平成大道?心在远方、路在脚下!
(阮德胜)